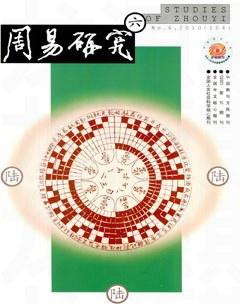《繆和》《昭力》與孔子易教
宋立林
摘要:馬王堆帛書《繆和》《昭力》中的“子”即是孔子,其中蘊涵著大量孔子易教思想,這些思想可以和其他古籍中所見孔子思想相互印證而又富新意。孔子晚而好《易》,不僅出于個人宗教情感之需要,更主要的是他對易之教化作用的闡揚。挖掘這兩篇中的孔子易教思想不僅可以推動帛書《易傳》的進一步研究,更可以深化對孔子思想的認識。
關鍵詞:帛書;《繆和》;《昭力》;孔子;易教
中圖分類號:B2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3882(2010)06-0028-08
孔子思想是一種以王道為理想的倫理一政治思想,其王道教化思想是通過對“六經”的傳授、闡釋來完成的。然而,在疑古思潮影響下,孔子與六經的關系受到質疑,孔子與《易》的關系更是遭到近乎全面否定。孔子六經之教與大量孔子遺說遭遇極端忽略,這無疑極大影響了對孔子思想的整體認識。帛書《周易》經傳的出土和釋文的公布,為我們重新認識孔子與《周易》的關系,研究孔子的易學與易教思想,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在帛書《易傳》中,《繆和》《昭力》為最末兩篇,其中《繆和》篇幅最巨,可是這兩篇所受到的關注度要遠遜于其他諸篇。然而,如細加繹讀,便會發現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價值,是絕不容忽視的寶貴文獻。它們不僅對于探究孔門易學傳承具有重要價值,而且對孔子易教思想的深入抉發,亦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一、帛書《繆和》《昭力》與孔門易學傳承
《繆和》、《昭力》為我們深入探究孔門易學傳承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線索。孔子好《易》發生在晚年,故孔子與《周易》真正確立關系亦在其晚年。正因如此,孔子易教、孔門易學傳承等問題才會若隱若現、糾葛不清。《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呂思勉說:“以設教言,謂之六藝。自其書言之,謂之六經。”六經之中,《詩》《書》《禮》《樂》屬傳統、普通科目,于此之外,又兼通《易》與《春秋》者,只七十余人。此可佐證《易》、《春秋》乃孔子晚年所贊所作的說法,又說明《易》與《春秋》涉及“性與天道”,非一般弟子所得聞,乃孔門精義所在。所謂《易》為“孔門精義”,是指與《詩》《書》《禮》《樂》等相比,更具哲學性和神秘性,職是之故,孔子才感慨:“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
孔門傳《易》者,據史書記載,僅寥寥數人而已。
其一為商瞿。《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傳《易》於瞿。”《漢書·儒林傳》對此亦有記載,《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亦載:“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然而,史志未見其著作著錄。
其二為子夏。子夏與孔子談論易學見于《孔子家語》的《六本》、《執轡》篇,《說苑·敬慎》亦有記載。關于子夏的易學著作,史志亦有記載。盡管關于《子夏易傳》作者有不同說法,但經劉大鈞、劉彬等先生考證,其為孔子弟子子夏無疑。
其三為子貢。子貢與孔子談《易》見于帛書《要》篇,這與《論語》所記子貢“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正相符合。關于子貢之嘆,朱熹早已指出,此乃“嘆美之詞”。李學勤先生也認為:“他說的是孔子關于性與天道的議論高深微妙,連他自己也難于知解。”而且《漢志》錄有子貢的《子贛雜子候歲》,我們可以據此推測子貢極有可能傳《易》。
其四為子張。他與孔子談《易》見于《孔子家語·好生》和《說苑·反質》,而《呂氏春秋·壹行》則記為子貢。其是否傳《易》在疑似之間。以上數人與《易》之關系為明確見于記載者。
另外,顏子與曾子也可能精于易學。在《系辭》中,有孔子稱贊“顏氏之子”的話,歷來作為顏子曾習《易》的證據。在《家語·顏淵》篇有這樣一段話:“顏回問于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日:‘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盛也。”由此可見顏子是曾深得孔子易教的。《論語·憲問》載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顯系引《周易·艮·大象傳》:“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以對孔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補充詮釋。除此之外,我們再很難見到孔子弟子傳《易》的相關記載。
而這兩篇文獻所記與孔子論《易》的弟子竟有七人之多,如繆和、呂昌、吳孟、莊但、張射、李羊、昭力。李學勤先生推測,他們當為楚人。昭力之氏“昭”,為楚氏;繆通穆,也可能是楚氏,有出土楚器燕客銅量銘文為證。其他呂、吳、張、李亦為戰國中期以下漸多的姓氏。由此,進一步推測這兩篇以及其他帛書《易傳》皆為楚人所傳。這與帛書出土于長沙楚墓相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李先生亦由此認為其中的“先生”及“子”乃后世經師,并推測為“鼾臂子弓”,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
人們將這兩篇中的“先生”及“子”認定為孔子之后的經師,根據之一即《史記》《漢書》所載的孔門易學傳承系譜的單線性。其實此乃司馬遷追溯其父易學淵源時之逆向描述而化約形成,故不能據此否定孔門易學的多元復雜性。以上提到的子夏、子貢等孔子高弟傳《易》,可見孔子易學絕非單線傳播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漢書·儒林傳》則將子弓(弘)列為第三代,則孔門易學傳至楚地在孔子身后數十年間。那么,孔子有沒有可能親自將其思想學說傳給楚人呢?據統計,孔子弟子當中明確為楚人者有三人,若將為楚所滅的陳蔡等地一并計算則有八九人之數。另外,澹臺滅明雖非楚人,但“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漢書·儒林傳》亦載“澹臺子羽居楚”。從近年來問世的郭店、上博楚竹書等來看,孔子儒學在戰國時期已在楚地影響十分廣泛。加之我們曾從多個方面去考察《繆和》《昭力》中的“子”即為孔子,可以相信,孔子易學之南傳人楚,恐不必待到孔門之二三傳。孔子易教雖有《易傳》傳世,然自歐陽修以來人們多疑而未信,致使孔子易教漸至湮沒無聞。幸帛書《易傳》出土,孔子易學及其傳承才再次得以確認。我們看到,孔子晚年講《易》,有眾多后進弟子向其請益。盡管這些名字早已湮沒無聞,不如七十子之顯赫,但吾人有理由相信,孔子易學易教之南傳人楚,擴大影響,恐多賴繆和、昭力諸人之力。
孔子之后,儒分為八。表面看來,這是孔子儒學之分化乃至分裂,其實在另一角度來看,正說明孔子思想之博大,儒學發展之多元。之所以會出現這一狀況,除了孔子自身思想的多元發展的可能之外,亦是孔子弟子群體的復雜性所致。史書說孔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在這眾多的弟子之中,有來自不同地域,不同地位和身份,不同稟賦和氣質的學生,而且他們求學處于孔子思想發展的不同階段,至少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甚至更多。這種極端復雜的情況,就造成了對孔子思想的接受和理解的多元可能性。我們通過《繆和》、《昭力》篇,可以發現,這些孔子晚年的弟子,所關心的問題不一,所提問題的角度不同,孔子的“因材施教”必然導致他們對孔子易學易教思想的領會出現差異。我們不清楚這些差異在后來的孔子易學傳流發展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但我們卻可以推測這些差異一定影響
了此后的孔門易學的發展。《繆和》、《昭力》等帛書文獻,只不過為我們揭開了久已失傳的海量文獻的冰山一角,使我們得以反思長期以來對孔子思想的認識的偏失。
二、孔子易教:教化與宗教之間
黑格爾曾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這一看法在西方有一定代表性,除了西哲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作祟之外,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學者自宋代始漸漸剝離了孔子與《易傳》的關系。當大量出土文獻一次次推翻疑古學者的“辨偽成果”,我們也可平和地去審視古代文獻的記載,重新梳理孔子與《易傳》的關系了。
孔子思想確乎很多“道德的教訓”,但卻并非沒有形上思考。孔子思想有一個逐步發展、提升的過程。晚年的孔子對具有哲學意味的《周易》發生濃厚興趣,甚至癡迷到“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瀆《易》韋編三絕”之程度。由于帛書《易傳》出土,使孔子是否曾經習《易》傳《易》這一學術公案得到了解決。《易傳》是否孔子所作雖仍存爭議,但文獻中有大量孔子“易說”已成共識。我們可通過這些“易說”來探討晚年孔子思想的變化和深化,他對《易》的理解以及以《易》為依托的教化思想。在《家語·問玉》和《禮記-經解》都記有孔子對“六經之教”的論述,云:“人其國,其教可知也。……絮凈精微,《易》教也。……其為人也,絮凈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矣。”孔子對《易》的性質功用,理解準確而深刻,這得益于他晚年對《易》有極深入的研究。
不過,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新認可孔子與《周易》的密切關系的情況下,關于孔子對《易》的看法也仍有巨大差異。如陳堅教授提出:孔子之好《易》只是他個人的一種宗教訴求,其中并不含有社會關懷的期許。這與孔子對于《詩》《書》《禮》《樂》的出于“修一教”實踐以完善社會的目的截然異趣。陳氏此說,可謂新見,他以宗教學的視角,對于孔子與《易》的這層“個人宗教”的關系之揭示,有助于吾人深化孔子與《易》關系的認識,很有啟迪意義,不容忽視。
杜維明對于儒家宗教性的定義為:“終極的自我轉化”。這自可表示孔子可能出于“終極的自我轉化”的“宗教需要”而好《易》。但杜氏“終極的自我轉化”所指絕非僅僅限于個人自身,而是不斷向外擴展和深化的。作為哲理書的《易》之所以會蘊含“宗教性”,能滿足人之宗教情感需要,這與其所展現和詮釋的天道思想有關。牟宗三對此有深刻論述:“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義。天道貫注于人身之時,又內在于人而為人的性,這時天道又是內在的。……天道既超越又內在,此時可謂兼具宗教與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義,而道德重內在義。”孔子重《易》,一個重要原因,恐怕在于《易》所具有的天道的超越意義、神圣性和宗教性。杜維明說:“儒家的性命天道雖不代表一種特定的宗教信仰,卻含有濃厚的宗教意義。不過儒家的宗教性并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氣氛中,而表現在個人人格發展的莊嚴性、超越性與無限性上。”@在孔子“易教”思想中,這種帶有形上超越性的思想也有突出的表達。比如,天人合德、與時偕行、極深研幾等,無不是“精微”之思,是窺天道而來。在其晚年,孔子思想形上色彩愈加濃厚。
然而,對于陳堅先生的論斷我們又有所保留。試問: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是否僅僅出于自己的“宗教訴求”?是否還有教化社會的意圖?是否如宗教那樣“神秘單傳”的只有商瞿一人傳《易》?如何理解孔子與宗教的關系?如何區別教化與宗教?這些疑問,我們通過對帛書《繆和》《昭力》的分析可以得到一個答案。
陳先生對其看法提供了很多解釋,但其詮釋可能存在“先人之見”的誤導。陳氏以文獻中只言孔子修“《詩》《書》《禮》《樂》”,而未言“修《易》”,從而提出孔子為何愿意對《易》作全新的詮釋而不愿意改動其中一個字的疑問,進而推測這緣于孔子對《易》所抱有的宗教徒對于宗教經典的崇敬態度。但如此推斷似嫌草率。孔子之所以不曾“修”《易》,恐怕與《易》的特點有關。我們知道,《詩》《書》《禮》《樂》都是古代文獻的資料集,并非成體系的“書”,而《易》卻具有一套“符號一文字”系統,故孔子只能“贊”而不必“修”了。這可以引《要》篇“《尚書》多於也,《周易》未失也”之語為證。
對于孔子“絮靜精微而不賊”的易教觀,陳氏認為:“很顯然,《易經》的這種能使人‘潔凈精微而不賊的作用完全是一種宗教性的作用。”我們認為,他對此語的解釋基本可信,結論卻可商榷。很顯然,即使出于“宗教性”訴求來看待《易》,但其立足點還在于教化,而并非僅出于個人宗教情感的需求,這從“人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的表述是可以清楚知道的。
我們以為,孔子之對于《易》學極為重視,甚至發出“后世之土疑丘者,或以《易》乎”的感慨,其中肯定含有宗教意蘊。然而,這只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孔子所強調的“社會教化”。因此,我們說,孔子之易教,既不是完全的世俗道德,也并非完全出于個人宗教情感之需要,正是介于教化與宗教之間的。
三、帛書《繆和》《昭力》與孔子易教思想
在對《周易》性質有了新認識,進而繼承古代易教傳統的基礎上,孔子形成了自己的易教思想。除今本《易傳》“子曰”部分,我們通過對帛書《易傳》的分析從中亦發現孔子易教思想之廣大精微。茲僅就《繆和》《昭力》這兩篇在學者看來與孔子無關者予以討論。
我們推測,此兩篇當為孔子晚年弟子繆和、昭力等根據聽課筆記整理而來。盡管其中可能經由整理者之潤色,但當基本可信為孔子易教資料。在《昭力》中,孔子明確指出,《易》有“卿大夫之義”、“有國君之義”,著重闡釋《易》的政治思想。在《繆和》中,孔子之答弟子問幾乎無不在闡發政治思想,尤其是為君者應具有的政治智能。
此兩篇文獻所反映的孔子易教思想與其他文獻中所反映的孔子教化思想基本一致,但又有新的論述和闡釋,值得注意。茲分幾個方面試予分析論述。
第一,人道效法天道。正如《四庫總目提要》“易類”小序說:“圣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易》則寓于卜筮。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孔子認為作為統治者的君子、大人應當仿效圣人,上明天道,下察民故,以天道推衍人道,用天道指導人道。在《繆和》中,這一思想有明確闡述。孔子說:“凡天之道,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壹晦壹明。夫人道仇之。”仇字之釋,從趙建偉,可訓“合”。此句言天道有其對立轉換的規律,如陰陽、短長、晦明的互相轉換正是天道的體現。而人道當合天道,故有“利達顯榮”與“困”之轉換。而古之“伯王之君”皆深諳此道,因“困”而得“達”。在講到《謙》卦時,孔子從天道、地道、鬼神之道與人道四個層面總結了“謙”之四益與“盈”之四損,進而提出“謙之為道也,君子貴之”的主張。這同樣體現著人道效法天道的觀念。
第二,憂患與謙讓。孔子“易教”的這一思想主要是針對統治階層而言的。其實,孔子本人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他對此闡述也所在多見。如《系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二三子》:“為上而驕下,驕下而不佁(殆)者,未之有也。圣人之立正(政)也,若遁(循)木,愈高愈畏下。”《衷》篇:“君子窮不忘達,安不忘亡。”無不是憂患意識之流露和闡揚。
其實,憂患意識在《繆和》也十分突出。孔子引用了詩句“女弄不敝衣裳,士弄不敝車輛”,指出“無千歲之國,無百歲之家,無十歲之能”,強調的正是一種憂患意識。該篇中孔子對“困”卦的解讀,更集中展示了這一思想。他強調“困”對人尤其對為政者的意義。孔子一生的遭際,使他對《困》卦有更深刻的理解。繆和問《困》卦,孔子解答道:“是故湯□□王,文王拘牖里,[秦繆公困]于殽,齊桓公辱于長勺,越王勾賤(踐)困于(會稽],晉文君困[于]驪氏,古古至今,伯王之君,未嘗憂困而能□□日美惡不□□□也。”以古來王霸之君為例,闡述了《困》卦深義,表達了自己對“困”(窮)與“達”的辯證看法。《說苑·雜言》、《孔子家語·困誓》亦略載此事。
與憂患意識緊密相關的是對“謙德”的推崇。在《繆和》中,弟子幾次問及《謙》卦,孔子皆借題發揮,闡述為政者要重視謙德的思想。他認為君主若能像古君子那樣“處尊思卑,處貴思賤,處富思貧,處樂思勞”,就能“長有其利而名與天地俱”,古代“圣人不敢有位也,以有知為無知也,以有能為無能也,以有見為無見也,憧焉無敢設也”,“夫圣君卑體屈貌以舒遜以下其人”,才能“致天下之人而有之”。其實在其他文獻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孔子對謙德的論述。如《家語·賢君》篇記孔子說:“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其中所表現的孔子重謙下的思想與此如出一轍。這種思想所體現的并不是一種消極的無為,而是一種政治的智慧。孔子從天地之道推衍人道,他說:“天之道,崇高神明而好下,故萬物歸命焉;地之道,精博以尚而安卑,故萬物得生焉;圣君之道,尊嚴復知而弗以驕人,嗛然比德而好后,故[天下歸心焉。]”(《繆和》)孔子重視謙德,恐怕與周公有關系。《韓詩外傳》卷三記周公誡伯禽的一段話,那里的記載與《繆和》有雷同之處,我們可以推測當是孔子襲用了周公之說。不管如何,它反映了孔子重視謙德的思想是淵源有自的。
實際上。重視謙德又與孔子重視《損》《益》兩卦分不開。在帛書《要》篇、《孔子家語》、《韓詩外傳》、《說苑》等文獻中都記載了孔子占卦得《損》《益》二卦之事,文辭大體相同。孔子強調“損益之道,不可不察”,認為其中蘊涵著天地人“三才”之道。而對損益之道的深刻理解在《家語·三恕》“孔子觀欹器”的記載中有著深刻的體現:“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韓詩外傳》卷三亦載此事而略異。通過對比,我們發現這兩處記載都涉及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等一段,雖文辭有異,但思想相通,而在《繆和》“子”也說了基本相同的話。這些材料當視為“同源材料”。由此可見孔子重視謙德之其來有自與一以貫之。
第三,“重言”與“慎言”。基于對社會人生的深刻體悟,孔子十分強調慎言。在《繆和》中,孔子提出“重言”的主張。他認為,《困》卦所謂“有言不信”,實際是說明“圣人之所重言”的道理。《困》卦孔疏曰:“處困求濟,在于正身修德。若巧言能辭,人所不信,則其道彌窮,故誡之以‘有言不信也。”這一解釋應該是符合孔子思想的。然而,對此有學者卻徑指為黃老道家思想,恐有武斷之嫌。只要我們對比一下《論語》、《家語》、《韓詩外傳》、《說苑》等的記載,就可見孔子的慎言思想是在繼承古圣賢基礎上的發展。在《家語·觀周》篇,記載了孔子觀《金人銘》,有“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之語,孔子命弟子記住這“實而中,情而信”的“古之遺言”,并引“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教導弟子慎言才能免禍。看來孔子的慎言思想也是傳承有自,和古圣賢如周文王、周公的思想一脈相承的。關于《金人銘》的可信度,已有學者作出了新的考證。其中同于《老子》的語句和思想,只能理解為《老子》繼承吸納了前人的思想。孔老思想有著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有許多相通之處,這也得到越來越多的文獻證明。今本《系辭上》就有孔子論慎言的話:“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論語》中,孔子對慎言的強調更可謂比比皆是,無需縷舉。在《家語》中,孔子也曾反復強調慎言。如《屈節》篇,孔子感慨:“美言傷信,慎言哉。”《說苑·政理》篇載孔子對子貢說,“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后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雜言》篇載孔予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這些記載說明將“重言”、“慎言”等思想狹隘地理解為道家的專利是不妥當的。
第四,“重時”與“察幾”。孔子被孟子贊為“圣之時者”。孔子之所以對“時”有極深刻的理解,是和他對《周易》的深入鉆研分不開的。我們在今、帛《易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對“時”的闡述是何等精妙。如《坤文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系辭下》:“待時而動。”孔子在《周易》古經中更深切理解了天道、地道、人道,他觀天道察民故,將“時”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時”有兩層含義,一是要善于把握時機,防微杜漸;二是“與時偕行”的“變通”思想。在《繆和》中,孔子時的思想主要體現為第一層意思。孔子強調君主對各種態勢發展要做到“其始夢兆而亟見之”,要“物未萌兆而先知之”,認為這是“圣人之志”、“三代所以治其國”的“法寶”。他還提出“古之君子,時福至則進取,時亡則以讓”。這一見解,同樣正與《家語·五儀》所載孔子對哀公所說相通:“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為禍”。
第五,“德政”與“刑辟”。孔子的政治思想,一言以蔽之曰:“德主刑輔”。即為政者要對臣民為政以德,同時不廢棄刑罰。《論語·為政》記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邢疏》:“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為政者使百姓有所“得”即是為政者之“德”,即是“善政”。“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這是孔子經常引用的一句話。在《繆和》中孔子同樣說:“君者,人之父母也;人者,君之子也。”孔子對政治關系的理想設計就是“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昭力》篇云:理想的君主應當“調愛其百姓而敬其±臣,強爭其時而讓其成利。”其實,這里所體現的思想和《家語·哀公問政》、《禮記·中庸》所記孔子所闡述的“治天下國家有九經”一致。盡管《中庸》為子思所“作”,但其中的“子曰”部分,顯系其整理保存的乃祖之言,應看作孔子思想資料。綜合這些材料來看,這些思想確乎應屬于孔子,并不像很多學者所認為的屬于子思或更后期的儒家。
《昭力》篇則對“卿大夫之義”即“臣道”思想進行了闡述:“昔之善為大夫者,必敬其百姓之順德,忠信以先之,修其兵甲而衛之,長賢而勸之,不乘勝名以教其人,不美卑喻以安社稷。”在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治國之道是“垂衣裳以來遠人”、“上政衛國以德”,其次是“衛國以力”,最差的是“衛國以兵”。要實現“衛國以德”,“必和其君臣之節,不[以]耳之所聞,敗目之所見,故權臣不作,同父子之欲,以固其親,賞百姓之勸,以禁違教,察人所疾,不作苛心,是故大國屬力焉,而小國歸德焉。城郭弗修,五兵弗實,而天下皆服焉。”雖然如此,如果要維護和諧的統治秩序,就要求君臣都要守禮,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遵循自己的禮,“君能令臣”,君主就能“動則有功,靜則有名”,君主要以爵祿勸勉臣下盡忠效力,“[明君之]口(使)其人也,欣焉而欲利之;忠臣之事其君也,歡然而欲明之,歡欣交通,此圣王之所以君天下也”(《繆和》)。“孰列爵位之尊,明厚賞慶之名”,是先王勸勉臣下的方法和途徑。這樣“賢君之為列執爵位也,與實俱,群臣榮其死,樂其實,夫人盡忠于上”。如果君主做不到這一點,而是“處上位厚自利而不自恤下”,“厚斂致正以自封也,而不顧其人”,則會導致禍亂。像“貪亂之君”那樣,“群臣虛位,皆有外志,君無賞祿以勸之。其于小人也,賦斂無限,嗜欲無厭,征求無時,財盡而人力屈,不勝上求,眾有離志”,則結果只能是“亡其國以及其身也”(《繆和》)。《昭力》篇云:“君之自大而亡國者,其臣厲以聚謀。君臣不相知,則遠人無勸矣,亂之所生于忘者也。是故君以愛人為德,則大夫恭德,將軍禁戰;君以武為德,則大夫薄人,[將軍凌上]。慳君以資財為德,則大夫賤人,而將軍趨利。是故失國之罪必在君之行不知決也。”君主是愛人還是愛財,決定著政治的方向以及成敗。
孔子雖然強調“為政以德”、“君惠臣忠”的為政之道,但也幾次談到“立為刑辟”的問題。“昔[之圣君垂]人以憲,教之以‘義,付之以刑,殺當罪而人服。……夫失之前將戒諸后,此之謂教而戒之。”(《昭力》)他認為臣下“朋黨比周”,“以奪君明”,是“古亡國敗家之法也”。因此,君主要善于明察秋毫,防患于未然;同時應“立為刑辟,以散其群黨”,唯如此方能避免“亡國敗家”(《繆和》),實現長治久安。
乍讀此文,不免有一種法家或黃老的感覺。故研究者多據此將《繆和》等判定為法家或至少是受法家或黃老思想影響的作品。即使承認為儒家作品,也多否認其為孔子思想的體現。陳來曾以帛書這兩篇為中心考察帛書《易傳》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從這個思想來看,雖然是戰國儒家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但……并不像孔子本人的思想,可能是戰國中后期儒家在政治上的發揮。”“包含了比較全面的君道思想,也反映了戰國中后期儒家在諸侯國政治實踐的主張。”王化平同樣認為:“從思想上說,帛書以儒為主干,糅雜了一些法家、黃老學說的內容,而且有些內容又與荀子的思想相通。所以,帛書應當成于戰國晚期”,他否認“先生”為孔子。之所以出現這種認識,正是對孔子為政思想的片面認識所致。
其實,孔子一向主張的“德主刑輔”為政之道。孔子闡述刑與政之關系時說:“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且曾以御馬為喻:“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方能達至千里。御民也一樣,“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這樣就可以達到“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緇衣》篇亦有“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的說法,所體現的正是孔子“德主刑輔”的君道為政思想。這與《繆和》《昭力》所論十分相像。《家語·始誅》所載孔子誅少正卯的故事,從中我們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孔子為政思想中德刑并用的主張。其實,《左傳·昭公二十年》所載孔子所推崇的“寬猛相濟”,《孔子家語·觀鄉射》所記“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都可以看作這一思想的不同表述。
綜上所述,《繆和》《昭力》篇所蘊涵的孔子《易》教思想可謂十分豐富。孔子利用《周易》這部獨特的古代經典,挖掘其中的“德義”,闡發其自己的王道教化主張,涉及到了其政治教化思想的各個方面,與他書所記孔子思想可以相互發明、相互印證。
責任編輯:李尚信劉保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