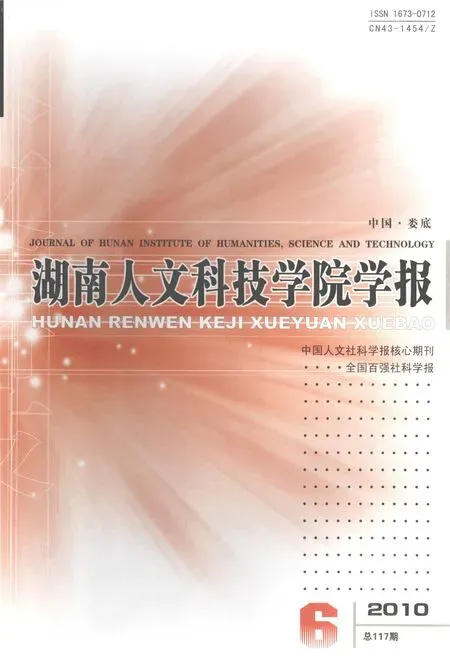朦朧詩命名的意義及其限度
鄭加菊,粘招鳳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南充637000)
朦朧詩命名的意義及其限度
鄭加菊,粘招鳳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四川南充637000)
1970年代末,朦朧詩以異端的吶喊給那個時代帶來了難得的思想沖擊力。朦朧詩的命名表達了當時詩歌的外在美學特征,暗示了當時詩歌創作環境的艱難,而且展示詩歌內容揭示了人內心的隱秘、直接指向心靈的品讀的特質,命名在這些意義上很好地傳達了它自身的涵義。但是當時代過往,朦朧本身的含混意指使得其之后的詩歌在某些方面難以逃越它的美學牢籠,成為新詩歌發展的桎梏。回到朦朧詩命名的現場,考察朦朧詩命名的內涵、直擊命名活動本身,可以清晰地觸摸詩歌發展的脈搏,有益于對當代詩歌發展的困境進行更好的思索和考量。
朦朧詩;命名;意義;限度
朦朧詩以異端的吶喊給那個“萬馬齊喑”的時代帶去了難以想象的思想沖擊力,北島、舒婷、顧城、江河等等作為詩歌的一代表形象屹立在詩文化的長河里。朦朧詩這個概念
也在讀者和批評家的話語實踐中,不斷地更新自己的涵義。“三崛起”、章明的《令人氣悶的“朦朧”》等等話語不斷地出現在許多評論文章里,漸次形成了對朦朧詩這個概念的基本敘述和評價方式。然而,由于時代風尚和人們閱讀經驗的變
化,以至于文學研究者也感嘆“對某種文學現象所作的概括,提出的概念,它的有效性是很有限的。”[1]65進入當代,許多文學研究者開始對一些習焉不察的現象和概念進行質疑,比如關于“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這樣的命名是否合理,“左翼文學”、“自由主義文學”的概念指涉等等。當我們在為朦朧詩后詩歌的不振扼腕痛惜時,除了歸罪于市場經濟這個客觀因素和詩歌本身的發展之外,筆者也在思考朦朧詩這樣的命名是否對其之后的詩歌形成一種牢籠,一種限制,也由此相信這樣的考察對當代詩歌的探索會帶來一些幫助。
一
回到命名的現場,直擊命名活動的歷史狀況,更能讓我們清晰地觸摸到那涌動的詩壇的脈搏。從而來考量這一命名活動的意義所在。1979年,詩人公劉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新的課題——從顧城同志的幾首詩談起》,文章里說到顧城的幾首詩讓他大為驚駭,認為應該對這樣的年輕詩人進行正確的引導,隨即掀起了關于這時候的詩歌的論爭。第二年,章明刊發了《令人氣悶的“朦朧”》,對那些“寫得十分晦澀、怪癖,叫人讀了幾遍也得不到一個明確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的詩,只用“朦朧”二字。這種詩體便稱之為“朦朧體”。同時,顧工也氣憤地指出“我越來越讀不懂我孩子顧城的詩,我越來越氣忿……”[2],可見,老一輩的許多詩人都在詩歌的“不懂”上表現出自己的不解和焦慮。隨后,朦朧詩這個概念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許多評論文章里被引用,它意外地適應了在其初創時期,只是朦朧覺察到的一個時代的關切和焦慮。如方冰《我對于朦朧詩的看法》,臧克家《關于朦朧詩》,周良沛《說“朦朧”》,艾青《從朦朧詩談起》等等。在這些評論文章里,他們認為詩意是清楚的,就不能算作”朦朧詩”,總之,還是在“不懂”上發感慨。臧克家甚至嚴厲批評“現在出現的所謂‘朦朧詩’,是詩歌創作的一股不正之風,也是我們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3]把詩歌功能上升到社會功用上。連備受年輕詩人所期待的老詩人艾青也認為寫詩“首先得讓人能看懂”。即使到了1984年,公劉依然重申《詩要讓人讀得懂——兼評<三原色>》。透視1980年代初對朦朧詩的批評的景象,不得不注意,朦朧詩之所以遭質疑和批判,歸根而言,罪魁禍首在于它的晦澀難懂。
與此同時,朦朧詩的支持者謝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中認為:“我們不必為此不安,我們應當學會適應這一情況,并把它引向促進新詩健康發展的路上去。”孫紹振先生堅信這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后起之秀徐敬亞認為“一首詩重要的不是聯貫的情節,而是詩人的心靈曲線,一首詩只要給讀者一種情緒的感染,這首詩的作用就宣告完成。”[4]當事人顧城在回答關于“懂”與“不懂”的認識時,也談到“對于詩和人的理解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是由作者和讀者兩方面來決定的。”[5]并且提到每個人都有審美的階段性,它是隨著人類進步,個人成長而不斷發展的意識。側面地回擊了反對者。198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副教授鄭樹森遙說“在西方,意象派的試驗早已被吸收為現代詩的常規而不再引起注意了;就是曾極力借鑒西方的臺灣現代詩中,這種集中的色彩意象也已被認為過時了;而顧城的詩在中國大陸卻正在引起某種‘不熟悉’的感覺和種種否定的評論。這就是朦朧詩派現象的反諷意義。”[6]海外學者從外部環境來考察中國當時的詩壇狀況,更多指明在詩與讀者之間,大多是讀者的問題,而非詩的全部過錯。當時的批評家所設定的“衡文”標尺,更多的來自于他們的閱讀經驗。
朦朧詩這個命名的由來大致如此,人們常常只是記住了誰第一次提出了這個稱謂,而實際上,命名的活動本身是一個不斷地折中和累積的過程。來自全國各地的詩人及詩評家都無不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話語表達。不難看出,命名表面上的簡單、明確,給許多讀者一種先入為主的印象。這個名稱對當時的詩歌而言首先是一種貶低。詩論者大多以詩意是否清晰來品評一首詩歌的好壞。梁小斌的《雪白的墻》一詩,不但寫得不朦朧,而且還很新穎。“顧城同志的《遠和近》,怎么讀也讀不懂,不知道作者為什么寫這樣的詩。”[7]他們大凡只是單純地從詩歌表面上的晦澀難懂這一點來進行解讀,拘囿于詩歌難懂背后的社會意義,而較少分析詩歌在美學上的意義。這種評價上的分裂,說明了我們生活的社會的“分化”。而朦朧詩本身的社會批判性正好適應了當時的社會風尚。后來對朦朧詩的指責消失了,舒婷的詩歌被選入了課本。朦朧詩在最大程度上使讀者的審美意識和閱讀視野發生了很大的改觀,在相繼地論爭中不斷地確立自己的價值和地位。朦朧詩在一開始作為權威批評家眼中的異端,但是在相繼地論爭中也確立了自己的價值和地位,從另一方面來說,可以窺見當時的權威性已經有所旁落,先前的文學評價機制也已經有所坍塌。朦朧詩成為打破國家話語方式的一個開始,同時也開始了一個追尋個人話語表達和選擇的過程。
二
在當前的學界,有持續的“評價”的沖動,命名活動更是頻繁。本雅明說“人在語言之中傳達著他自己的精神存在,而人的語言是通過語詞來言說的。因此,人是通過對其他事物的命名來傳達其精神存在。”[8]命名的名稱如何向我們傳送,決定了我們對事物的感受和理解。因為命名同時包含著一種精神存在。可見命名對于人們理解世界的重要性。反過來,人也只有通過命名這一活動,才能更好的向他人表達自身。
朦朧詩這樣的命名首先最直接地表現了它的外在特征,其次也暗示了當時詩歌的語言環境的艱難。按照朦朧詩的支持者的理解,他們認為朦朧詩最直接呈現了它的美,朦朧美。孫紹振說這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從傳統和審美習慣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內核”,他一再強調習慣問題,認為新的習慣必須向舊的習慣借用酵母。朦朧,在傳統上的意思是具有朦朧美,“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云無覓處。”諸如這首詩表現的就是讀者所理解的朦朧意境,美不勝收。孫紹振先生的用意或者正是借用傳統的這些合理的內核,順勢推出了朦朧詩這種美學原則。命名的直接性,易懂性顯示了這個命名更好的向他人傳達自身,給人們更加深刻的印象。朦朧詩這個名稱首先符合人們的接受心理。時過境遷,當人們提到何為朦朧詩,便可以從這個名稱本身闡發詩歌的應有之義,也可以由此推及詩歌當時的社會環境,從而更好地理解詩歌的本質內涵。
同時,朦朧詩的命名也展示了詩歌內容揭示了人內心的隱秘、直接指向心靈的品讀的特質。朦朧詩的難懂性關鍵也就在于其內容上的模糊、晦澀。因為朦朧詩是指向詩人自我心靈的獨白,非得有類似的人生體驗不能理解,非得靜下心去體會不能理解,非得有必要的知識水平不能理解,非得在朦朧中體會出清晰不可。
正如朦朧二字本身的含義一樣,模糊、含混,包含著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它的最大的藝術特點就是因為朦朧而具有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如果在解讀上把它單純化或單一化,就勢必會削弱朦朧詩的藝術本性,朦朧詩也就不再是朦朧詩。如果說,“當代文學”老讓人覺得是“當前”的文學,這導致了語義上的含混,那么朦朧詩這個概念也總讓人覺得只要是朦朧的詩歌,都可以歸為朦朧詩,而含混了這個名稱應確切表示的內涵。因而,這個命名實際上過于寬泛了。當時評論者把大量的具有僭越傳統的異質性詩歌統統納入了討論的范疇,而且直到現在,關于朦朧詩的許多作品,詩人以及概念仍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這種敘述方式、敘述體系,沒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就直接進入我們的當代文學史,這也反映了命名的有限性和研究與思考的局限性。而這種有限性在朦朧詩一開始就顯現出來了。
在人性剛剛得到舒解的時候,朦朧詩以叛逆性的姿態宣告一個質疑時代的到來。他們自覺承擔起歷史和現實苦難的雙重書寫,追求宏大的敘事和主體上的真實,多采用意識流,蒙太奇,象征等手法并擅用鮮活的意象群,所有這些皆增加了語言的所指性難度系數,大肆地沖擊了當時詩歌閱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感受心理。同時也造成在當時的許多詩人看來這些詩歌晦澀難懂。甚至謝冕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對朦朧詩進行總結時,曾從“看不懂”的角度對朦朧詩的某些方面有所批評:“例如某些詩篇過于夸大破碎形象的偶然拼湊,甚至浮表地滿足于淺層次的象征和繁榮的裝飾,相當數量的詞語不合常規,無節制地使空茫的意象充斥詩中,而作品的可感性達于低點。”[9]這個特點是朦朧詩的特質,也是它在一開始為人所詬病的地方。有趣的是,第三代詩歌,有些寫得十分直白,有些卻把這一缺點放大到極點,很多出現了“看不懂”的現象。第三代詩人們試圖通過打破習慣性詞語的組合模式,追求詞義的幽秘和多義,從而顛覆一體化的詞語霸權,達到心靈的自由抒寫。以鐘鳴的《樹巢》為例:風吹過草原,我們兩眼茫茫,血,在碑額上停止無用的奔流。羊群在最后一線燭光中遭到女巫熾熱的語言放逐。光明,無畏黑暗者最初的光明。樹巔上神秘的葉子在頭頂消失,牙在陰影里恢復,石麒麟和玉蟾蜍,優美的亂倫,人類的俗氣?魚鳥各有各的卵,各自的統治,各有各的巢,無論是庭前的玉樹,還是在死者身上找到的沒有光澤的徽章,或者以仁義為劍,或道德為胄,這些都無法使他擺脫死者,一根碩長的金指甲,以雞鳴樹巔上,在火苗里,在采采服飾上為他徒勞地講授庸俗的地理學。
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繁雜密集的詞語展覽,毫無規律可言的縱橫散亂的扭結組合,互相碰撞覆蓋,激起一片奇異怪誕的喧響。很難找出貫串一致的內在含義,詞語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聯被徹底切斷。不能不說,第三代詩歌在選擇了以朦朧詩為反叛目標,雖然在命名上與朦朧詩廓清了關系,但是詩歌所表現出來的美學特質卻實實在在地因襲了朦朧詩美學特征的一方面。本雅明還說:“人給予語言的名稱取決于語言是如何向他傳送的。”[8]8那么,第三代詩歌這樣的命名應該取決于詩歌給人的美學感受是如何向他傳送的。反過來說,第三代詩歌給我們的美學感受也是多義性,含混性,可否說屬于它的命名應該也是朦朧詩。問題到這里就出現了先后的關系。朦朧詩在先,而第三代詩歌在后。朦朧詩是一個具有多種解讀性的命名,借用本雅明先生的一個說法“過度命名”,用在朦朧詩這個命名上是很自洽的。所謂“過度”指超越適當的限度。朦朧詩的過度命名使它的適用性范圍大大的擴大了,在時間和空間上均超越了命名所該有的指向性。時過境遷,它的超時代性的命名仍一直籠罩著第三代詩歌。第三代詩歌必須為自己命名才能劃清與反叛目標的界限,走上一個新的高度。而朦朧詩的出現是時代使然。但是這種朦朧詩寬泛式的命名最終使這個命名帶來的涵義走出了一個時代,又走進了另一個時代。很顯然,它也一同包括了第三代詩歌的難懂性。這種過度性的命名使得其之后的詩歌一直很難擺脫它的美學圈套,那么,其之后的詩歌就更加無法形成自己命名下的美學原則,從而也就難以具有不絕的生命力。當一種命名涵蓋了另一種命名下的創作,命名本身便失去了一定的意義。后一種命名可以為前一種命名所取代,其中所蘊含的精神存在或者說美學原則卻有部分重合。當試圖徹底反叛的結果造成是精神上因襲的壓力,作為對一種美學原則的反撥時,卻出現了相同的價值取向。不能不說,這種命名的有效性是很有限的。
三
在對一些文學現象和文學事件、潮流的研究和評述中,文學研究者常常喜歡用一些概念來攏括復雜的互有差異的體驗和具體性,用概括來替代具體分析。洪子誠在編寫《中國當代新詩史》時,把牛漢詩人1980年代的詩歌編在章節“七月派”的詩群里面。牛漢發言說:“我根本就不是‘七月派’,‘七月派’早就不存在了;50年代‘七月派’就不存在了,我就是我,為什么還把我放在‘七月派’里頭?”[1]45我們看到了,概括自身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而這壓力不僅是對自身,更是概括以后對后來者產生的影響和壓力。對一些思潮的命名也是如此,隨著時間的流動,有些命名顯示出了影響的尷尬,同時不可避免的出現重復命名的現象。諸如對一個詩潮的命名,單對朦朧詩后的詩歌就有各式各樣的命名,目前看到影響較大的就有“新詩潮”“后新詩潮”朦朧詩“后朦朧詩”“前崛起”“后崛起”“第三代”“新生代”“實驗詩”“現代詩群”“現代主義詩群”等等。這看似喧鬧的命名活動,實際上也體現出研究和評述本身的些許無奈。
“朦朧”詩,“朦朧詩”?實際上當朦朧詩成為一個確切的命名時,它也就擠壓和掩蓋了之后同征詩歌的命名空間,甚至是生存空間。縱觀我們史學上的朦朧詩后的詩歌,其最明確的特征,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仍然是“朦朧”。或者說,朦朧詩后的詩歌仍然是“朦朧”詩,其美學內涵和精神存在在讀者的第一印象中仍然是“朦朧”,至于其他的特質,就被掩蓋在這背后。另外,細致思考如“第三代詩歌”等的命名本身,實際上是一種無力突破的妥協,第三代詩歌的特質是“第三代”?這顯然無法給讀者以直接美感的牽引,而成為一種無奈的提示。
命名本身就意味著研究者的獨到發現,獨特的命名正是體現研究者研究實踐的價值核心,其內在包含研究主體的創造性思考、艱辛性求索和特殊性見解。其一,一個獨特的命名往往指向一種獨特的研究思路、觀察視角。其二,一個獨特的命名往往包括研究主體艱辛的探究的過程,是對其艱辛勞動的科學總結。其三,一個獨特的命名就是研究成果的展示,是對研究的獨到發現的合理概括。然而,歷史不斷發展,新舊更替是一種必然的趨勢。當一個命名越過了它命名的時代,它便常常成為一個舊物,甚至成為一種新事物誕生和發展的桎梏。
當然,對這些已經為人們所習焉不察的名稱,我們不能無視也不能輕易拋棄。輕易拋棄的話,會使很多具有體系性的概念和敘述消失,而一些重要問題也因此而消失,這是不可取的。我們要做的就是重新找尋這些名稱、主張和“語境”之間的關聯,辨析它們特定的內涵。同時,對一種新的文學現象的產生,不要過于著急為它命名。缺乏時空的一定距離,研究者獲得超眼界會比較困難,容易就事論事。身處其中,情感、經驗上的一些因素,也會成為一種束縛。而一旦一種名稱已在不斷地被論述中成為一種既定的表達方式,那么它自身的限度也就開始顯露出來了。
因此,在還沒有特別看清楚事物的發展狀況的時候,不妨先讓時間來“蕩凈”一些假象,從而更好地為文學把脈。在朦朧詩發生后的20多年,我們繼續對這段歷史進行探討,不是就歷史而談歷史,相信對今天和明天的文學研究的建設和發展會有啟示性意義。
[1]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65.
[2]顧工.兩代人:從詩的“不懂”談起[J].詩刊,1980(10):28.
[3]臧克家.關于朦朧詩[J].河北師院學報,1981(1):56.
[4]徐敬亞.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J].當代文藝思潮,1983(1):78.
[5]顧城.朦朧詩回答[J].文學報,1983:82.
[6]鄭樹森.論《“朦朧”詩》[J].藝術爭鳴,1987(4):47.
[7]方冰.我對于朦朧詩的看法[N].光明日報,1980總匯.
[8]瓦爾特.本雅明.寫作與救贖:本雅明文選[M].李茂增,蘇仲樂,譯.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2):5.
[9]謝冕.斷裂與傾斜:蛻變期的投影:論新詩潮[J].文學評論,1985(5):108.
(責任編校:光明)
Significance of Naming Misty Poetry and Its Limitation
ZHENG Jia-ju,NIAN Zhao-feng
(Literature Institute,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Nanchong 637000,China)
In the late 1970s,misty poetry exerted great impact on people’s ideas of the age with unusual cry.The naming of misty poetry displayed the external esthetic features,and implied the hard environment of creation at that time.What’s more,it also showed the traits that the contents of poetry could be directed at the mind to reflect the secret inner world of people.In these senses,the naming expressed itself well.However,as the time passed by,due to the ambiguous implication of the misty poetry,it is hard for the later poetry to break the bonds of the esthetic conventions in some aspects,which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creation.Back to the scene of naming misty poetry,inspecting the meaning of the naming and the naming activity itself,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poetry development clearly,which is beneficial to better consider and speculate on the plight of contemporary poetry development.
misty poetry;naming;significance;limitation
I206.7
A
1673-0712(2010)06-0053-04
2010-10-26.
鄭加菊(1985—),女,福建漳州人,南充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