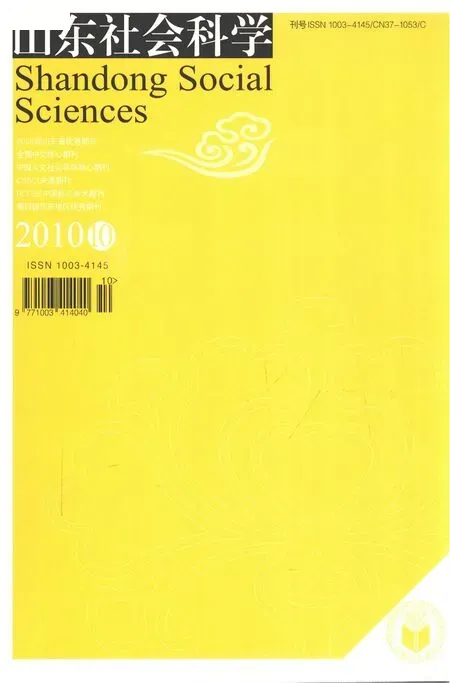新時期鄉土散文的美學精神*
王景科 顏水生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新時期鄉土散文的美學精神*
王景科 顏水生
(山東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新時期鄉土散文的美學精神是復雜多樣的。以陳白塵、汪曾祺和陸文夫等人為代表的鄉土散文具有江南水鄉氣息,表現的是婉轉悠揚的尋根與鄉戀之曲;以劉成章、周濤等人為代表的西部散文表現的是西部風情高亢雄渾的贊歌;賈平凹的鄉土散文是鄉村文化的惋歌,賈平凹與韓少功從不同角度實現了對現代性的批判;以劉亮程、謝宗玉等人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的鄉土散文表現了“大地悲歌”的美學精神。
鄉土散文;懷鄉;西部散文;反思現代性;大地悲歌
新時期三十年,鄉土散文創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其美學精神呈現出豐富多樣的局面。以陳白塵、汪曾祺和陸文夫等人為代表的鄉土散文具有江南水鄉氣息,表現的是婉轉悠揚的尋根與鄉戀之曲;以劉成章、周濤等人為代表的西部散文表現的是對西部風情高亢雄渾的贊歌;賈平凹的鄉土散文是鄉村文化的惋歌,賈平凹與韓少功從不同角度實現了對現代性的批判;以劉亮程、謝宗玉等人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的鄉土散文表現了“大地悲歌”的美學精神。
一、婉轉悠揚的戀歌
進入新時期以來,無論老一輩作家,還是中青年作家,他們的鄉土散文都表現了強烈的對故土家園的思念之情。在老一輩作家的鄉土散文中,如孫犁《老家》、茹志娟《故鄉情》、劉紹棠《榆錢飯》、菡子《看戲》、田野《掛在樹稍上的風箏》、吳泰昌《紅紅的小辣椒》等都表達了對故鄉的深沉掛念;畫家郁風著有散文集《我的故鄉》,其中《最可懷念的地方》、《我的故鄉》、《還鄉雜記》等散文以對鄉村生活的描繪表達了作者對故鄉的深沉眷念。也有些作家沉浸于對故鄉風土人情的描繪,如陳白塵《龍舟競渡話端陽》回憶了童年時代的端陽風俗,思鄉之情溢于言表;楊羽儀《水鄉茶居》繪聲繪色地介紹了廣東茶居的特色。在中年作家中,“尋根與鄉戀”仍然是重要的主題,如鐵凝《洗桃花水的時節》、和谷《石磨憶》、蘇葉《夢斷瀟湘》等表達了強烈的思鄉之情。賈寶泉有散文集《當時明月今在否》等,“像許多愛家鄉、寫家鄉的作家一樣,賈寶泉的許多作品都深深扎根在家鄉的土地上。……在他的作品中,故土已不僅僅是一個個具象的實體,在生命的漂流中,它幻化成時間長河中的一個個港灣,帶著特有的情調和意味,載入詩性的審美人生的追尋中”。①李曉虹:《中國當代散文的審美建構》,海天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47頁。徐治平的《故園》、《捕虎》等散文追思了難以忘懷的童年生活。周同賓著有《鄉間小路》、《葫蘆引》等散文集,以對鄉村生活的描述表現了對鄉土的守望與歌哭。郭保林著有《青春的橄欖樹》、《五彩樹》等散文集,郭保林是農民之子,他對故鄉魯西平原有著“純潔高尚的愛”,如《八月,成熟的故鄉》、《家鄉的白楊林喲》等。
與中年作家相比,老一輩作家在時間和空間距離故鄉都更加久遠,因此,他們的“懷鄉”情結更加沉重,其中陳白塵、汪曾祺、陸文夫等人的鄉土散文具有代表性。陳白塵在新時期著有散文集《寂寞的童年》,表達了對故鄉的愛與相思。《我的故鄉》描寫了故鄉的歷史人物、山川風光、名勝古跡,《元宵憶親》表達了對父親和母親的深厚感情,《我的三位老師》追思了自己的啟蒙老師。陳白塵還追憶了童年時代的生活,如《風箏之戀》、《話說毽子》、《金鈴子》、《“岸束穿流怒”》等散文回憶了童年放風箏、踢毽子、逮金鈴子、大閘口看過船的趣事;《升官發財過新年》、《龍舟競渡話端陽》、《迎神》、《賽會》等散文回憶了鄉村習俗。陳白塵的童年生活是寂寞的,但他仍然對童年生活記憶猶新,滿懷相思和懷念,“我并不是對童年時代感到悔恨。相反,倒很留戀:要不然,哪能在小小年紀能懂得如許生活?況且,回憶總是甜蜜的,即使那段生活充滿了痛苦。特別是對一個到了垂暮之年的人來說”。①陳白塵:《寂寞的童年》,三聯書店 1985年版,第 158頁,第 1頁。陳白塵在散文中流露的感情是不加掩飾的,他對故鄉的感情是厚重的、奔放的,他能開門見山地暴露自己對故鄉的愛,正如他在《我的故鄉》的開頭寫道:“人,愛自己的母親;也都愛自己的故鄉。故鄉,這個詞是多么具有迷人的魅力!”②陳白塵:《寂寞的童年》,三聯書店 1985年版,第 158頁,第 1頁。
汪曾祺的鄉土散文奏響的也是鄉戀之曲,但他在情感表達上不同于陳白塵。汪曾祺繼承了中國現代鄉土散文的寫作傳統。中國現代鄉土散文的一個重要特色在于作者把對故土家園的深情藏于對人、景與物的精雕細刻中,體現的是一種平和沖淡的藝術風格,如周作人的《烏篷船》詳細介紹了烏篷船的構造特色,沈從文的《湘行散記》及《湘西》對景與物的刻畫也是細致入微,汪曾祺繼承了現代鄉土散文的這種寫法。作為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不僅仰慕沈從文的人品:“他是我見到的真正淡泊的作家,這種‘淡泊’不僅是一種‘人’的品德,而且是一種‘人’的境界,”③汪曾祺:《沈從文的寂寞》,載《汪曾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6年版。而且繼承了沈從文的風格:“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④汪曾祺:《蒲橋集·自序》,載汪曾祺:《蒲橋集》,作家出版社 1991年版。如汪曾祺在《故鄉的食物》中對家鄉的食物如數家珍、流連忘返,他不厭其煩地敘述了家鄉的炒米、焦屑、咸蛋、咸菜,平淡、自然,像拉家常一樣。周作人和沈從文并不過度夸飾自己對家鄉的深情,而是把這種深情一語帶過。他們對家鄉的景與物早已了然于心,通過委婉的敘述和精細的刻畫,以一種平淡的心境構造平和的意境,款款深情盡在不言中,因此,中國現代鄉土散文重在寫意是有道理的。汪曾祺《故鄉的食物》把對故鄉食物的喜愛和眷念滲入字里行間,《我的家鄉》中寫道:“我的家鄉是一個水鄉,我是在水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⑤汪曾祺:《我的家鄉》,載汪曾祺:《草木春秋》,作家出版社 2005年版。這樣的語句與周作人“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把自己的深情以委婉的語句表達出來,卻句句是情,字字是真。
陸文夫的鄉土散文也是在一種平實的敘述中表達深厚的感情。陸文夫的鄉土情感是深厚的,如《故鄉情》中寫到:“一個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總要想起自己的故鄉,”⑥陸文夫:《故鄉情》,《夢中的天地》,《綠色的夢》,載陸文夫:《陸文夫散文:插圖珍藏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年版。《夢中的天地》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也曾到過許多地方,可那夢中的天地卻往往是蘇州的小巷。”⑦陸文夫:《故鄉情》,《夢中的天地》,《綠色的夢》,載陸文夫:《陸文夫散文:插圖珍藏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年版。陸文夫的情感表達是委婉適中的,字里行間沒有浪漫的抒情,更沒有情感的噴發,他的鄉土散文記述的往往是已經過去的人與事,通過回憶的方式、行云流水的描述表達對鄉土永久的懷念,如《綠色的夢》中寫道:“所有的夢幾乎都是些既模糊,又清晰,大都十分遙遠的記憶,”“竹園是小小蒙童的迪尼斯樂園”,⑧陸文夫:《故鄉情》,《夢中的天地》,《綠色的夢》,載陸文夫:《陸文夫散文:插圖珍藏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7年版。這篇散文回憶的是作者在童年樂園中發生的趣事。《鄉曲儒生》回憶的是秦老師的故事,秦奉泰是作者的啟蒙老師,引導作者走上了文學道路。
以陳白塵、汪曾祺、陸文夫等為代表的鄉土散文作家,積淀了深厚的藝術功底,歷練了豐富的人情世故,以各自獨特的敘述風格,蘊藏著真摯深厚的鄉土情感,奏響了一曲曲婉轉悠揚的鄉戀之歌,為鄉土散文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為新時期鄉土散文創作樹立了一座難以逾越的豐碑。
二、高亢雄渾的贊歌
鄉土散文因為地方性的限制使其具有非常鮮明的地方色彩。陳白塵、汪曾祺、陸文夫等人的鄉土散文具有明顯的江南水鄉氣息,而劉成章、周濤、馬麗華、張承志等人的鄉土散文具有鮮明的西部風情。關于“西部文學”的美學精神,李曉虹認為:“西部文學是‘力’的文學,豪壯、粗獷、蒼涼、奔放、渾厚遼闊。人生的艱難和環境的困苦給生活的理解蒙上一層充滿奮斗精神的憂患色彩、悲壯情調。陽剛之氣鑄就了西部風骨。”⑨李曉虹:《中國當代散文的審美建構》,海天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35頁。這種美學精神在西部散文中表現得更為突出;江南水鄉釀造了一曲曲婉轉悠揚的戀歌,而西部風情造就的是一首首高亢雄渾的贊歌。
在老一輩作家中,劉成章和楊聞宇是西部散文的代表。楊聞宇的散文集《灞橋煙柳》描繪了獨特的秦中風情,劉成章的《劉成章散文集》和《羊想云彩》中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表現黃土高原和陜北風情的,其中的《轉九曲》、《安塞腰鼓》、《臨潼的光環》、《壓轎》等散文表達了對高原由衷的贊美和熱烈的歌頌;劉成章“對高原生命有著深刻的體認,他的骨子里有著高原地域特有的詩意的浪漫情懷,而成為陜北高原上的一位‘歌手’,一位著名的浪漫詩人”。①厚夫:《高原生命的火烈頌歌 民族魂魄的詩性禮贊》,《名作欣賞》2001年第 5期。《安塞腰鼓》的美學精神得到了高度的評價,李曉虹認為它是“一篇突出表現西部風格的作品,作者以激越的語言、明快的節奏,寫出黃土高原上獨有的舞蹈安塞腰鼓的壯闊、豪放、火熱,更寫出只有黃土高原才能孕育出來的這些元氣淋漓的后生,和從他們那‘消化著紅豆角老南瓜的軀體’里釋放出來的‘那么奇偉磅礴的能量’,這是一曲力與美的贊歌,西部風情在作品中得以詩意的體現”。②李曉虹:《中國當代散文的審美建構》,海天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51頁,第 240頁。另有人認為:“《安塞腰鼓》既是高原生命的火烈頌歌,也是民族魂魄的詩性禮贊。它以詩一般凝練而又富有動感的語言,譜寫了一曲慷慨昂奮、氣壯山河的時代之歌。”③厚夫:《高原生命的火烈頌歌 民族魂魄的詩性禮贊》,《名作欣賞》2001年第 5期。
在中年作家中,周濤、馬麗華、張承志等人的散文具有鮮明的西部風情。李曉虹曾稱周濤的散文具有一種“西部風骨”,其實在美學精神方面,周濤、馬麗華、張承志等人的描寫西部風情的散文都可稱之為“西部風骨”,“蘊含著奪人的氣勢和獷悍勁健的風骨”④李曉虹:《中國當代散文的審美建構》,海天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51頁,第 240頁。,他們的散文完全沒有江南水鄉的特色。周濤對新疆獨特風情的描寫使他的散文表現出了一種西部精神,這是一種開拓進取的精神,表現出一種強悍粗獷的美。在周濤的哲學中,“邊緣不是世界結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闡明自身的地方”。他走向邊遠地區,扎根西部,他對中國西部有一種獨特的認識和特殊的親近感。周濤認為“中國西部的故事一點兒也不比美國西部少,其粗獷的力度和多種文化沖撞的光芒,如能表達,則更精彩。歷史曾在這里大開大闔,時間在大摧毀和大空曠中期待著大物質與大精神的新構架”。⑤周濤:《周濤散文:插圖珍藏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33頁,第 21頁,第 22頁。因此,周濤致力于對西部獨特風情的表現,在《二十四片犁鏵》中,周濤首先描寫了犁鏵的巨大能量,它可以剖開草原的肌膚,劈斬無數種生命,切斷草根、土地和頑石,但是哈薩克老婦人根本瞧不起這種現代化工具,周濤就是在老婦人的沉默中表現了游牧者的高貴。在周濤的散文中,西部游牧者是如此的高貴,西部動物也是強悍的、威武的,在《鞏乃斯的馬》中,周濤再現了鞏乃斯馬驚心動魄的氣勢與波瀾壯闊的場面:“我見到了最壯闊的馬群奔跑的場面。仿佛分散在所有山谷里的馬都被趕到這兒來了,好家伙,被暴雨的長鞭抽打著,被低沉的怒雷恐嚇著,被刺進大地倏忽消逝的閃電激奮著,馬,這不肯安分的牲靈從無數谷口、山坡涌出來,山洪奔瀉似的在這原野上匯聚了,小群匯成大群,大群在運動中擴展,成為一片喧叫、紛亂、快速移動的集團沖鋒!爭先恐后,前呼后應,披頭散發,淋漓盡致!”⑥周濤:《周濤散文:插圖珍藏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33頁,第 21頁,第 22頁。作者被這種氣勢和場面所震驚,久久地站在那里,發愣、發癡、發呆。在《猛禽》中,作者描寫了鷹與狼的搏斗場面,再現了一只威武強悍的鷹。周濤認為馬、鷹等動物是“進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與美的巧妙結合”,⑦周濤:《周濤散文:插圖珍藏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33頁,第 21頁,第 22頁。所以他把它們推向力的極致、美的極致。
馬麗華的散文是她多年西藏生活的思考與記錄,散文集《走過西藏》包括《藏北游歷》、《西行阿里》、《靈魂像風》等三部長篇紀實散文,描寫了西藏的風光、人物、歷史、文化,表現了西藏的神奇與瑰麗、夢幻與莊嚴,成為“西藏大地的歌者”。⑧劉俐俐:《構筑當代精英文化烏托邦的歌者》,《西藏文學》2000年第 6期。張承志對內蒙古草原、天山南北、黃土高原的風情描寫也獨具特色,他在《音樂履歷》中表達了對草原的忠愛:“無論如何,感激草原,它使我遠離了另一種——我想是可怕的生存方式。”張承志描寫了西部的生存境況,無論是在內蒙古大草原,還是在天山南北,純美的自然景觀和頑強的精神生態都令人振奮不已。與周濤的相比,張承志更加注重對人的歌頌,他筆下的“額吉”富有崇高的母愛,是完美無缺的,是圣潔的化身。張承志與馬麗華一樣,喜歡表現人在困境中的苦難掙扎,人物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和不斷進取的精神,以表現西部人超越苦難、樂觀生活的精神,正如“‘苦難美’主義使她實實在在地真誠面對生命歷程中的一切,并與之共生共榮”。⑨邵長纓等:《藏北原風景與西藏的馬麗華》,《臨沂師專學報》1998年第 5期。
“西部散文作家在表現描寫西部時,持的是仰視的立場,他們虔誠地把西部的高貴相勾勒出來,作為重建精神家園的參照系”。⑩范培松:《西部散文:世紀末最后一個散文流派》,《中國文學研究》2004年第 2期。“在西部散文的字里行間,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屬于西部的奧博與靈性,深厚與偉岸,粗礪與曠達,悲愴與神圣,使西部散文帶給人以強烈審美感受的同時,顯示了磅礴厚重的精神格調和思想魅力”。①賈艷艷:《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西部散文》,《河北學刊》2004年第 1期。因此,綜觀劉成章、周濤等人的西部散文,其美學精神的核心在于歌頌西部的高貴與圣潔,表現的是一種陽剛之氣和偉力之美。
三、惆悵無奈的惋歌
賈平凹鄉土散文的美學精神是復雜多樣的。賈平凹一方面繼承了現代鄉土散文的寫作風格,重視對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的表現,強調對鄉土人性與人情美的謳歌;另一方面,賈平凹與韓少功一樣,在鄉土散文創作中表現了鮮明的反思現代性的意識,對鄉土文化的漸漸逝去表達了沉重的感傷和無限的惋惜。
賈平凹《商州三錄》、《秦腔》、《靜虛村記》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鄉土散文。《商州三錄》描述了商州的山川河谷和風土人情,正如賈平凹所說:“商州實在是一個神奇的土地呢。它偏遠,卻并不荒涼;它貧瘠,但異常美麗。”②賈平凹:《在商州天地——〈小月前本〉跋》,載賈平凹:《小月前本》,花城出版社 1984年版。他對生我養我的商州懷著深厚的感情,商州已經融入到賈平凹的血液里;同時“商州成全著賈平凹‘作為一個作家的存在’。當如‘魯鎮’于魯迅,‘湘西’于沈從文,‘白洋淀’于孫犁,‘商州’已成了對賈平凹的另一種描述甚至指稱”。③曾令存:《賈平凹散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7頁,第 99頁。商州作為賈平凹的故鄉,已不僅僅作為游子感情寄托的家園,而且“已具有思想文化與藝術審美的意義”。④曾令存:《賈平凹散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7頁,第 99頁。賈平凹繼承了沈從文和孫犁對鄉土人性和人情美的贊揚,正如他寫:“棣花就是這樣的地方,山美,水美,人美。”⑤賈平凹:《商州初錄》,載賈平凹:《鄰家少婦》,作家出版社 2005年版。一語中的,賈平凹描寫商州也就是表現鄉土的人性和人情美,在這方面,賈平凹也承認深受沈從文的影響,他說“沈從文之所以影響我,我覺得一是湘西和商州差不多,二是沈從文名氣大,他是天才作家”。⑥賈平凹:《如語堂·關于小說創作的問答》,中國工人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5頁。在藝術表現方面,賈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與汪曾祺的鄉土散文風格基本相似,繼承了現代鄉土散文重在寫意、力求平淡的風格,如程光煒所說:“他的語言獨具神韻,文字簡約、傳神,就像是一幅寫意畫,往往三言兩語,即把一種含蘊的思想、意趣傳達給了讀者。”⑦程光煒:《說“文”還從之“道”來——代序》,載曾令存:《賈平凹散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版。《秦腔》介紹了秦腔戲曲,秦腔在八百里秦川有著神圣不可動搖的基礎,其歷史悠久、文武正經、是非洶洶。賈平凹挖掘了秦腔的歷史文化內涵,以及秦腔與秦川百姓喜怒哀樂的密切關聯。《秦腔》以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意義,與汪曾祺的鄉土散文如出一轍,為鄉土散文的歷史化、文化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靜虛村記》中,賈平凹把靜虛村作為清靜拙樸的棲身之地,描寫了靜虛村的人、水、花、樹,村人怡然自樂,作者也樂在其中。
綜觀賈平凹的鄉土散文,他的故土赤子情懷是深厚的,他作為鄉下人對鄉土人性和人情熱情地贊美,同時他以農民的眼光和立場對時代發展保持清醒的認識。《商州初錄》有一段話:“外面的世界愈是城市興起,交通發達,工業躍進,市面繁華,旅游一日興似一日,商州便愈是顯得古老,落后,攆不上時代的步伐。”⑧賈平凹:《商州初錄》,載賈平凹:《鄰家少婦》,作家出版社 2005年版。賈平凹看到了在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日漸落后,他本人也經歷了由鄉下人到城市人的轉變,然而城市生活并沒有給賈平凹帶來快樂和幸福,“我回過頭來,望了望我生活了 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顆顆淚。這一去,結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結束了我的農民生活。我滿懷著從此踏入幸福之門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 20年后我才明白,憂傷和煩惱在我離開棣花的那一時起就就伴隨我了,我沒有擺脫……”⑨賈平凹:《我是農民》,陜西旅游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74頁。賈平凹始終認同自己的鄉下人身份,2000年,賈平凹寫了《我是農民》的長篇散文,回憶了自己在商州鄉下 19年的農民生活,指認了自己的農民身份。在《〈秦腔〉后記》里,賈平凹也念念不忘自己的農民身份:“做起了城里人,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上的。”⑩賈平凹:《〈秦腔 〉后記 》,載賈平凹:《鄰家少婦 》,作家出版社 2005年版。《〈秦腔〉后記》在鄉土散文中非常具有代表性,賈平凹不再像《商州三錄》那樣對家鄉的山川草木、風土人情表達純真的熱愛,在經歷歲月的斑駁后,賈平凹看到了鄉村的貧困和由此生發了對故鄉的恨,這種愛恨交織使他對故鄉的感情更加真切。在經歷現代化的洗禮后,城市化的進程使鄉村日漸受到擠壓,鄉村的日漸破敗和凋零,鄉村文化的日漸萎靡和消逝,觸動了賈平凹的神經,“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盤前,想,難道棣花街上我的親人、熟人就這么很快地要消失嗎,這條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嗎,土地從此也要消失嗎,真的是在城市化,而農村真的要消失嗎”??賈平凹:《〈秦腔 〉后記 》,載賈平凹:《鄰家少婦 》,作家出版社 2005年版。賈平凹的困惑是必然的,作為一個以“鄉下人”自居和堅持農民立場的知識分子,他對農民懷有深切的同情,他憐憫農民在現代化擠壓之下的困境,他反思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被拋”狀態。賈平凹思想上的變化,必然影響了他的散文風格,在《<秦腔 >后記》中,他對鄉村困境的描寫字字見情,句句含淚,他似乎要迫不及待地躍出紙面表達對農民的同情和憐憫,過去那種恬淡委婉,那種怡然自樂消逝殆盡。從早期的《商州初錄》到現在的《〈秦腔〉后記》,雖然賈平凹對鄉村文化有著謳歌與贊美,但賈平凹對鄉村文化的歷史與未來都有著清醒的認識,早期散文對鄉村文化的歌頌更多地象征著對鄉村文化的拯救,但歷史趨勢不可移易,鄉村文化的消逝在現代化進程中成為必然。正如“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這句話所隱含的內容,《〈秦腔〉后記》是鄉村文化的惋歌,是賈平凹鄉土美學的終結。
在反思現代性方面,與賈平凹重視現代性對鄉村的擠壓不同,韓少功的鄉土散文側面表現了現代性對城市的擠壓。1992年,張煒在《上海文學》發表散文《融入野地》,表達了作者對故土家園的向往和對城市化的反思與告別。從某種意義上說,張煒的《融入野地》是在表達對鄉土的一種回歸,一種理念,一種向往,在賈平凹與韓少功之間形成了一定的承繼關系,這篇散文在新時期鄉土散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2006年,韓少功長篇筆記散文《山南水北》的出版是鄉土散文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在《山南水北》中,韓少功描寫了八溪峒的山光水色、飛禽走獸、風情民俗、神話傳說等,表現了鄉村生活的和諧與安寧。“撲進畫框”、“地圖上的微點”、“窗前一軸山水”等章節描摹了八溪峒如詩如畫的風景,宛如一幅優美的山水畫。“開荒第一天”、“治蟲要點”、“養雞”、“憶飛飛”等章節描寫了勞動的快樂。韓少功筆下的鄉村如詩如畫,居于山南水北則是心靈的陶冶和靈魂的凈化,他把鄉村建構成理想的家園以實現對城市化的反思和批判:“融入山水的生活,經常流汗勞動的生活,難道不是一種最自由和最清潔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難道不是一種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樓所擠壓,不愿被城市的噪聲所燒灼,不愿被城市的電梯和沙發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車交織如梭的鋼鐵鼠流,還有樓墻上布滿空調機盒子鋼鐵肉斑,如同現代的鼠疫和麻風,更讓我一次次驚悚,差點以為古代災疫又一次次入城。”①韓少功:《山南水北》,作家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頁。在《山南水北》中,城市是作為鄉村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鄉村生活的自在與和諧襯托了城市生活的陌生與孤獨,表達了韓少功返樸歸真、回歸自然的人生追求。韓少功散文對鄉土的描寫始終體現的是知識分子視角,他歸隱農村是為了逃避城市生活的擠壓,為了享受田園生活的樂趣,這與農民的真實心理是有隔膜的,如賈平凹對鄉下的體驗更多的是苦難:“人生的苦難是永遠和生命相關的,回想起在鄉下的日子,日子就變得透明和快樂。真正的苦難在鄉下,真正的快樂在苦難中。你能到鄉下去嗎?作為人,既要享受快樂,也要享受苦難。”②賈平凹:《我是農民》,陜西旅游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05頁。1987年,韓少功寫過《布珠寨一日》,這篇散文表現了湘西保靖縣的一個小山寨的封閉與落后,可見韓少功的知識分子立場是一貫的,韓少功與賈平凹的區別就在這里。賈平凹始終堅持的是農民立場,他對鄉土既愛且恨,他愛鄉土的血緣之情、養育之恩,他恨鄉土的貧困與落后,他以對鄉村文化的謳歌試圖拯救鄉村文化的未來,但結果卻是令人失望與無奈,“謳歌”轉變成為“惋歌”也就理所當然了。
四、悲愴凄惋的哀歌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加速發展,中國農村遭受了巨大的沖擊,農民的身份與心理也隨之變動,新生代鄉土散文作家記錄了這種變遷。新生代鄉土散文作家雖然有不少側重對鄉村風景的贊美和對歷史文化的謳歌,如周鐵鈞散文集《我是東北人》描繪了東北的風土人情,又如少數民族作家阿拉旦·淖爾的散文集《薩日朗》描繪草原風光和游牧風俗,但是以劉亮程、謝宗玉等為代表的鄉土散文作家對鄉村生活的消逝表達了深切的哀痛,其哀痛之情更甚于賈平凹的惆悵與無奈,更多的是悲哀與凄惋,正如楊獻平所說:“驀然覺得了悲涼、疼痛和憂傷,丟失的,遠去的,再也找不回來了。”③楊獻平:《有一種憂傷,比路途綿長》,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
劉亮程、謝宗玉等一批 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散文作家,也就是所謂的“新生代作家”,他們以大地之子、農民之子的身份,悲憫大地,悲憫農民的災難與痛苦,其中摩羅的《我是農民的兒子》非常具有典型性,其情感表達與美學追求都突出了“悲哀”二字。新生代鄉土散文作家在思想和情感上具有很多相似特征,他們更多地是追求一種“大地悲歌”的美學精神。首先,新生代鄉土散文作家大都是農民之子,他們都不約而同地以農民自居,如摩羅一再宣稱:“我是農民的兒子,而且是世世代代的農民的兒子。”④摩羅:《我是農民的兒子》,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他們對土地有著固執的深愛,叛逃土地給他們帶來了強烈的原罪感;無論身在何處,他們的精神都永久地跪倒在故鄉的土地上。其次,新生代鄉土散文作家筆下的鄉土是一片苦難深重的土地,在這塊土地上積累了世世代代的痛苦。如摩羅說:“在這些繁華而又缺乏人氣的地方,我無意間窺見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頭、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的痛苦。”①摩羅:《我是農民的兒子》,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又如江子在《永遠的暗疾》中描寫因下地勞動而感染瘟疫,生病二十二人,死亡兩人致使兩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以土為命的人,哪一個身體上沒有一兩個未愈合的傷口”?②江子:《永遠的暗疾》,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朝陽在《喪亂》中寫到:“我鄙視一切把農村視作田園的人們,他們不能理解勞動給予身體的痛苦和重壓。”③朝陽:《喪亂》,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再次,鄉村經歷和苦難決定了這些作家與城市的隔膜。摩羅承認“強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農民烙印仍然非常明顯。我至今沒有融入城市之中,我想以后也永遠不會”。④摩羅:《我是農民的兒子》,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這一特點在劉亮程和謝宗玉等人的散文中也有著鮮明體現。最后,新生代鄉土散文作家對當今農村遭受的現代化的擠壓懷有深切的痛苦,如程寶林在《民如鳥獸》中描繪了“青壯打工去,婦孺留村莊”的農村現實,農民為了生存而背棄土地,使田園荒蕪、長滿青青的野草。劉鴻伏在《父老鄉親哪里去了》表達了一種深深地哀痛:“我不知道這世代播種著汗水和淚水,收獲了貧窮也收獲了快樂的田園為什么要被人厭棄。田園,美麗且蒼茫的田園啊,你到底怎么了?為什么人沒有了眷戀,為什么人要逃離你的庇護,寧愿去漂泊?”⑤劉鴻伏:《父老鄉親哪里去了》,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小山在《關于鄉村》中寫道:“中國鄉村,留守的人都是無奈,走出去的孩子幾乎沒有返回的。城市人口,有多少來自鄉村亦永別于鄉村 ?”⑥小山:《關于鄉村》,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
劉亮程與謝宗玉的鄉土散文代表了新生代鄉土散文的成就。劉亮程著有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風中的院門》、《人畜共居的村莊》等。《一個人的村莊》分為三輯:人畜共居的村莊,荒蕪家園,扛著鐵锨進城。在“人畜共居的村莊”中,有一個叫“黃沙梁”的村莊,村莊里驢牛狗馬、花木蟲蟻和諧相生,自然成趣;村民生活簡樸,思想單純,自得其樂。在“荒蕪家園”里,作者寫到了家園荒涼、田地荒蕪的景象。“在扛著鐵锨進城”中,作者生活在城市中卻仍是城市的過客,他無法改變自己鄉下人的生活習慣。從“人畜共居的村莊”到“荒蕪家園”再到“扛著鐵锨進城”,這三個名字具有寓言化的內涵,人畜共居的村莊是和諧安寧的,現代化和城市化不僅打破了這種和諧與安寧,而且帶來了家園的荒蕪與被拋,然而進城的鄉下人生活浮躁不安,仍然懷戀著過去的鄉村生活。在散文集《風中的院門》中,“黃沙梁”在作者心中是永恒的,是無法舍棄的。劉亮程在散文中建構的“黃沙梁”小村莊,是他生命的起點和終點:“我的故鄉母親啊,當我在生命的遠方消失,我沒有別的去處,只有回到你這里——黃沙梁啊。”⑦劉亮程:《只有故土》,載劉亮程:《風中的院門》,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1年版。“黃沙梁”也是他思想、感情的棲居地和精神故鄉,“這是一個被‘現代’,也被‘傳統’遺忘了的村莊。這是一個被‘革命’,也被‘發展’遺忘了的村莊。這是一個被‘城市’,也被‘田園’遺忘了的村莊。這是一個被‘畫家的調色板’,也被‘學者的田野札記’遺忘了的村莊。這是一個真實的村莊,又是一個虛擬的村莊。這是作者自己一個人的村莊”。⑧牛布衣:《自己的村莊》,載《鄉村哲學的神話》,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63頁。劉亮程對鄉村的態度是雙重的,他一方面以詩意的筆觸描寫了寧靜和諧的鄉村生活,他對土地有著一種固執的熱愛,如《家園荒蕪》寫全家兄弟因為遷住城市而荒廢了自家的土地而感到茫然無措、備受折磨。另一方面他也體悟到了鄉村的愚昧與落后,農民生活的艱辛與困難,如《做閑懶人,過沒錢的生活》描寫了農村父老鄉親辛苦無奈的生活,《人畜共居的村莊》描寫農民活得艱難、過得艱辛。在劉亮程的散文中,鄉村與城市是對立的兩極,他出身農村,以農民立場觀察時代的變遷和現代化的進程,散文中的農民意識是強烈的,也是真摯的,他對鄉村有著難以磨滅的愛,對城市有著深深的隔膜,如《城市牛哞》:“這個城市正一天天長高,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蒼白的。”⑨劉亮程:《城市牛哞》,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劉亮程感受到了現代化、城市化給鄉村生活帶來的沖擊,表現了鄉村生活正在漸漸消逝的悲劇,林賢治談到劉亮程散文中的悲劇時,認為:“鄉村的悲劇不同于城市的悲劇,農人的悲劇不同于市人的悲劇,前者不僅是精神的,也是物質的,因此更為慘苦。”⑩林賢治:《九十年代最后一位散文家》,載《鄉村哲學的神話》,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6頁。由此可見,劉亮程的散文更多地是鄉村的哀歌。
謝宗玉著有散文集《田垅上的嬰兒》、《村莊在南方之南》等,他在散文中建構了一個叫“窯村”的世界,“‘窯村’是他的生命之源,也是他的藝術之源”、“沉浸在他的窯村世界中,我們會觸摸到一種真誠的隱痛,一種美麗的憂傷,一種徹骨的悲涼,當然還有超然的寧靜與曠達”。①吳玉杰:《謝宗玉鄉土散文的雙重敘述》,《文藝爭鳴》2008年第 4期。謝宗玉對農村生活的苦難與死亡有著特殊的敏感,如《一個夏天的死亡》、《活多久才能接受死》、《誰是最后記得我的那個人?》、《剩下的日子我還能做些啥?》、《麥田中央的墳》、《該輪誰離去了》、《家族的隱痛》等散文對死亡的追問;在《一個夏天的死亡》中,農民的非正常死亡成為司空見慣的事實;在《活多久才能接受死》中,爺爺認為住房是旅館,棺材才是永久的家。謝宗玉以赤子之心悲憫大地,悲憫農民,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危機,如他在《鄉村四季》中寫到:“即便是簡單的農事,有時也會暗藏某種兇機。”②謝宗玉:《鄉村四季》,載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花城出版社 2005年版。謝宗玉對城市也有著心理隔膜:“在城里生活,我有一種被包扎的感覺。”在情感表達方面,謝宗玉比劉亮程更加直白,劉亮程追求的是一種緩慢的節奏,哀歌侵人心脾,余音繞梁;謝宗玉更多的是徹骨的悲涼,立刻給人以心靈震憾。
綜觀新生代作家的鄉土散文,“他們的作品抒發了一種強烈的情感,躍然紙上、攝人心魄,正是由于這種獨特的情感使他們與老一輩散文作家在藝術風格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他們拋開平淡的敘述,走出了精致的描寫,情感的迸發成為他們執著的藝術追求”。③顏水生:《新時期鄉土散文史論》,《名作欣賞》2009年第 5期。如果說現代散文家對鄉土有著獨到的眷戀情懷,那么,到了新生代散文家,鄉土則變得陌生和困惑。這其中有社會的因素,時代的變遷,更有著美學意義的差異。
I26
A
1003—4145[2010]10—0040—06
2010-09-01
王景科 (1949-),女,山東滕州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顏水生(1980-),男,湖南衡陽人,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山東省社科基金項目《多維視野中的中國新散文研究》,批準號:05BYJ11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艷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