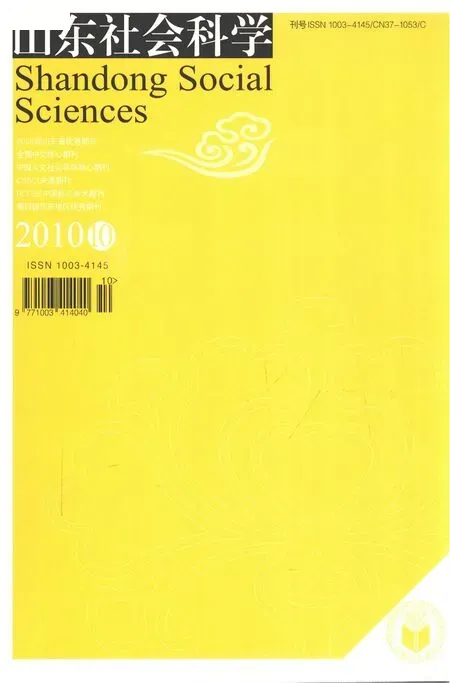學術偶像的另一個側面
——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學術政治活動述評*
鄧慶坦
(山東建筑大學,山東濟南 250101)
學術偶像的另一個側面
——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學術政治活動述評*
鄧慶坦
(山東建筑大學,山東濟南 250101)
梁思成不僅是中國著名的建筑史學家和建筑遺產保護事業的先驅者,而且也是 1949年新中國后長期主宰建筑文化界的建筑創作主旋律的奠基人。1950年代初,他扮演了新政權建筑藝術政策“立法者”的角色:將政治話語引入建筑理論,對“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建筑創作主旋律進行了理論闡述。他的學術政治活動為新中國成立后近 30年的主流建筑文化設立了鮮明的意識形態坐標。
梁思成;折衷主義;建筑藝術;政治化
梁思成 (1901~1972年)是中國近代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梁啟超的長子,作為中國古代建筑歷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傳統建筑文化遺產保護的先驅者,梁思成蜚聲海內外,并成為中國建筑學界的一代學術偶像。他的形象似乎永遠這樣定格在世人的腦海中:在內憂外患、烽火連天的舊中國,為考察和研究古代建筑而跋山涉水;在政治風云變幻的新中國,為保護和搶救北京舊城和文物建筑而奔走呼號。然而,作為一位歷史人物,他的一生是多側面的,上述只是他廣為人知的一面,也許是為長者諱為尊者諱的傳統使然,他的另一個側面——新中國成立后近 20年的學術政治活動雖有論及卻鮮有深入的探討。
梁思成一生的建筑夢想有兩個,一個是中國古老的建筑文化遺產能夠得到妥善保護,另一個則是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在新時代能夠得到發揚光大。傳統建筑文化的保護和復興情結貫穿了他整個一生,并且屢屢與官方倡導的中國傳統復興運動相糾纏。1927年成立的國民政府曾經給他實現自己夢想的第一次機遇:1928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大興土木作為新政權的象征,并掀起了一場傳統建筑文化復興浪潮。為了迎合民族主義思潮,同時出于國內意識形態斗爭的需要,南京國民政府積極倡導傳統文化復興,留學歸國的梁思成可以說是生逢其時:回顧梁思成 1920、30年代的學術生涯,基本上是一手“整理國故”,一手發揚國故。他編輯出版了《建筑設計參考圖集》——為“中國固有形式”設計提供傳統樣式參考,他還親自指導了南京中央博物院的建設 (徐敬直、李惠伯設計)。雖然梁思成對中國傳統建筑有著深厚的感情,但是面對時代潮流還是保持了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智和清醒。他是中國引進現代主義建筑理論的先驅,早在 1930年代初,他對現代主義建筑思想的理解已經達到了時代的高度。1940年代,在國際現代建筑運動浪潮沖擊下,他對“中國固有形式”進行了反思,承認中國傳統建筑復興運動是一種“逆時代的潮流”,“在最清醒的建筑理論立場上看來,‘宮殿式’的結構已不合于近代科學及藝術的理想。”“世界建筑工程對于鋼鐵及化學材料之結構愈有徹底的了解,近來應用愈趨簡潔。形式為部署邏輯,部署又為實際問題最美最善的答案,已為建筑藝術的抽象理想。今后我們自不能同這理想背道而馳。”①梁思成:《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凝動的音樂》,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8年版。
1930年代,胡適曾經告誡學者們要恪守學術立場的中立,反對學術為政治服務。他指出:“我不認為中國學術與民族主義有密切關系。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夸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工夫,所謂實事求是也。”①宋劍華:《胡適與中國文化轉型》,黑龍江教育出版社。綜觀梁思成的早期建筑思想,雖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主義的印記,但是還是與國民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保持了應有的距離,保持了學術思想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如果說在南京國民政府倡導的中國傳統建筑復興浪潮中,梁思成還基本上游離于政治之外;那么,在新中國成立后以“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為口號的更大規模的傳統建筑復興運動中,梁思成已經深深地陷入建筑政治化的急流與漩渦之中。
一、為新政權建筑藝術“立法”——建筑理論的政治論證
新中國成立伊始,梁思成如同文學界的周揚、美術界的徐悲鴻一樣,扮演了新政權建筑藝術政策“立法者”的角色。與文學、繪畫相比,建筑藝術是長于文化與意識形態戰線斗爭的中國共產黨人所陌生的空白地帶,因此,梁思成的作用就顯得至關重要、不可或缺。早在 1950年 4月,他躊躇滿志地寫信給一位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在建筑理論中闡發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觀點。他宣稱,“今后中國的建筑必須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建筑;而‘民族的’的則必須發揚我們數千年傳統的優點。……二十余年來,我在參加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中,同若干位建筑師曾經在國內作過普遍的調查。……其目的就在尋求實現一種‘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建筑的途徑。”②梁思成:《致朱總司令信——關于中南海新建宿舍問題》,《凝動的音樂》,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8年版。在其后的論文中,他做了進一步的闡述:“我們將來的建筑應該向哪個方向走呢?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新民主主義論》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一節就是我們行動的指南。那也就是斯大林同志為全世界文藝工作者,包括建筑工作者,所指出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總方向。蘇聯各民族的建筑師們在斯大林時代的創作,就是以民族形式來表達社會主義內容的最好的范本。”③梁思成:《祖國的建筑》,《梁思成文集 (四)》,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86年版。
1953年 2至 5月,梁思成隨中國科學院訪蘇代表團訪問蘇聯,對蘇聯“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建筑文化政策深表贊同。同年 10月,在中國建筑工程學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為主任委員的梁思成作了《建筑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的報告,他引述清華大學建筑系蘇聯專家阿謝甫可夫教授的話說:“藝術本身的發展和美學的觀點與見解的發展是由殘酷的階級斗爭中產生出來的。并且還正在由殘酷的階級斗爭中產生著。在藝術中的各種學派的斗爭中,不能看不見黨派的斗爭,先進的階級與反動階級的斗爭。”在報告中,他正式把階級斗爭理論引入建筑理論,使建筑理論上升到一個新的政治高度,他宣稱,“毛主席給我們指出:‘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在建筑工作的領域中,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建筑思想和歐美資產階級的建筑思想還在進行著斗爭,而這斗爭是和我們建筑的民族性的問題結合在一起的。這就是說,要充滿了我們民族的特性而適合于今天生活的新建筑的創造必然會和那些充滿了資產階級意識的、宣傳世界主義的絲毫沒有民族性的美國式玻璃方匣子的建筑展開斗爭。”④鄒德儂:《中國現代建筑史》,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1年版。通過他的報告,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建筑藝術具有階級性,而階級斗爭常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因此,在建筑中搞不搞民族形式,是個階級立場問題。
1950年代初,梁思成把政治話語引入建筑理論,完成了對官方建筑藝術政策的理論闡述,從而為新中國成立后近 30年的主流建筑文化設立了鮮明的意識形態坐標。
二、建筑理論的退卻——對現代建筑運動的徹底否定
作為對舊政權和舊中國建筑歷史通盤否定的一部分,梁思成把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建筑體系傳播歸結為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譴責指出,“這一百年中蔑視祖國傳統,割斷歷史,硬搬進來的西洋各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筑形式對于祖國建筑是摧殘而不是發展。……殖民地建筑在精神上則起過摧殘民族自信心的作用,阻礙了我們自己建筑的發展;在物質上曾是破壞摧毀我們可珍貴的建筑遺產的兇猛勢力。”他對歐洲現代建筑運動和曾置身其中的中國現代建筑實踐進行了全面否定,指出,“以‘革命’姿態出現于歐洲的這個反動的藝術理論猖狂地攻擊歐洲古典建筑傳統,在美國繁殖起來,迷惑了許許多多歐美建筑師,以‘符合現代要求’為名,到處建造光禿禿的玻璃方盒子。中國的建筑界也曾墮入這個漩渦中。……‘五四’以后很短的一個時期曾作過恢復中國傳統和新的工程技術相結合的嘗試,但在殖民地性質的反動政府支離破碎的統治下和經濟基礎上沒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發展;反倒是宣傳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的各種建筑理論和流派逐漸盛行起來。”①梁思成:《中國建筑發展的歷史階段》,《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69-470頁。
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氣候,對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演變軌跡產生了重要影響。早在 1930年代,他就對現代主義的理性建筑觀表現出充分的認同,他把建筑的實用性放在首位,把美觀視為實用和堅固的派生物,認為“一個好建筑必須含有實用、堅固、美觀三要素,美觀,則即是綜合實用、堅穩兩點之自然結果。”1950年代初,他全面接受了蘇聯斯大林時期強調建筑藝術性的學院派建筑思想,放棄了自己的現代建筑價值觀,對其曾經心儀不已并深得其精髓的現代主義建筑大加撻伐。1951年,他在《城市計劃大綱·序》中指出,“所謂‘國際式’建筑本質上就是世界主義的具體表現;認識到它的資產階級性;認識到它基本上是與墮落的、唯心的資產階級藝術分不開的;是機械唯物的;是反動的;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教政策基本上是不能相容的。”②梁思成:《城市大綱·序》,《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9年版。他宣稱,“洋房、玻璃盒子似乎給我們帶來新的工程技術,有許多房子是可以滿足一定的物質需要的。但是,建筑是一個社會生活中最高度綜合性的藝術。作為能滿足物質和精神雙重要求的建筑物來衡量這些洋式和半洋式建筑,他們是沒有藝術上價值的。”他進一步指出,“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無所留戀地揚棄那些資本主義的,割斷歷史的世界主義的各種流派建筑和各流派的反動理論;必須徹底批判對世界文化遺產的虛無主義態度以及忽視民族藝術遺產的態度。”1954年,他在《祖國的建筑》一文中宣稱,“我們的建筑也要走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的路,而揚棄那些世界主義的光禿禿的玻璃盒子。”③梁思成:《祖國的建筑傳統與當前的建設問題》,《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98頁。梁思成把對現代主義建筑的批判上升到政治高度,從而給“民族形式”和現代主義建筑風格貼上了不容混淆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政治標簽。
梁思成從 1930、40年代現代主義建筑思想立場上的倒退和對現代建筑運動的政治性批判,可以看作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現代建筑悲劇性命運的縮影。
三、建筑可譯論——理論創新還是折衷主義?
1954年,梁思成在發表于《建筑學報》的《中國建筑的特征》一文中,提出了建筑的“可譯性”理論。首先,他把“我們建筑上二、三千年沿用并發展下來的慣例法式”稱為“文法”,他指出,“無論每種具體的實物怎樣地千變萬化,它們都遵循著那些法式。構件與構件之間,構件和它們的加工處理裝飾,個別建筑物與個別建筑物之間,都有一定的處理方法和相互關系,所以我們說它是一種建筑上的‘文法’。”至于“詞匯”,他是這樣定義的 ,“梁、柱、枋、檁、門、窗、墻、瓦、檻、階、欄桿、隔扇、斗拱、正脊、垂脊、正吻、戧獸、正房 ,廂房、游廊、庭院、夾道等等。那就是我們建筑上的‘詞匯’,是構成一座或一組建筑的不可少的構件和因素。”
在對中國傳統建筑的典型形式要素進行了語言學類比后,他提出,“運用這‘文法’的規則,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極不相同的‘詞匯’構成極不相同的體形,表達極不相同的情感,解決極不相同的問題,創造極不相同的類型。”④梁思成:《中國建筑的特征》,《梁思成文集 (四)》,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86年版。1953年梁思成在一次演講中,對運用可譯性理論進行了形式生成與轉化的示范。張镈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他草畫了圣彼得大教堂的輪廓圖,先把中間圓頂 (dome)改成祈年殿的三重檐。第二步,把四角小圓頂改成方形、重檐、鉆尖亭子。第三步,把入口山墻 (ped iment)朝前的西洋傳統作法徹底鏟除,因為中國傳統建筑從來不用硬山、懸山或歇山作為正門。把它改成重檐歇山橫擺,使小山花朝向兩側。第四步,把上主門廊高臺上的西式女兒墻的酒瓶子欄桿,改為漢白玉石欄板,上有望柱,下有須彌座。甚至把上平臺的大石階,也按兩側走人,中留御路的形式。第五步,把環抱前庭廣場的回廊和端亭也按頤和園長廊式改裝,端頭用重檐方亭加以結束。”最后,梁思成得出結論,“用中國話,說中國式的建筑詞匯,用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法和形象風格,加以改頭換面,就是高大到超尺度的圣彼得大教堂上去運用,同樣可以把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杰作,改成適合中華民族的藝術愛好的作品。”⑤張镈:《我的建筑創作道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1997年版。
在不久后的另一篇論文《祖國的建筑》中,梁思成還繪制了兩幅民族形式建筑的想象圖,從多層建筑和高層建筑兩個類型出發,對其帶有西方學院派色彩的形式生成與轉化理論進行了具體的詮釋。梁思成的可譯性理論使張镈“感受極深”,在他設計的北京民族文化宮中,把這一理論演繹得淋漓盡致:高 13層的中央塔樓覆蓋著綠色琉璃瓦重檐攢尖屋頂,四角為小重檐攢尖頂,這種集中式構圖顯然來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
至此可以得出結論:剝除繁雜的概念與理論,梁思成的可譯性理論本質上就是西方建筑歷史上前現代時期的集仿式折衷主義,具體手法就是運用西洋古典構圖與傳統官式大屋頂和細部的結合;他的兩幅民族形式建筑想象圖也并無多少新意,無論是多層建筑還是高層建筑,都沒有超越 1920、30年代的“中國固有形式”實踐。
四、結語:梁思成晚年學術悲劇的反思
梁思成出生于晚清,青少年時代是在清末民初度過的。這一時期,從上層社會到市民階層,中國社會普遍崇尚西洋建筑文化,傳統建筑文化受到世人的鄙視。他曾經為這一時期傳統建筑文化的空前衰落而痛心疾首:“自清末季,外侮凌夷,民氣沮喪,國人鄙視國粹,萬事以洋式為尚,其影響遂立即反映于建筑。凡公私營造,莫不趨向洋式。”①梁思成:《中國建筑史》,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53頁。客觀地講,“外侮凌夷,民氣沮喪”的國勢頹唐,并非傳統建筑體系衰落的主因,真正的原因還得從中國傳統木構建筑技術層面的先天不足中尋找,在適應現代社會需要方面,即使與西方傳統磚(石)木建筑體系相比都處于明顯劣勢 (如清末民初的洋風盛行),被以鋼筋混凝土和鋼結構為技術基礎的現代建筑體系取代更是歷史的必然。而用現代結構、現代材料模仿中國傳統建筑特征的所謂傳統復興,必然嚴重違背建筑功能、結構與經濟的合理性和文化的時代性,這是中國傳統建筑復興運動始終無法逾越的時代困局,也是梁思成的傳統建筑復興之夢所無法走出的時代困局。他對傳統的衰敗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無奈與惋惜,他一方面清醒地認識到“世界建筑工程對于鋼鐵及化學材料之結構愈有徹底的了解,近來應用愈趨簡潔。形式為部署邏輯,部署又為實際問題最美最善的答案,已為建筑藝術的抽象理想。今后我們自不能同這理想背道而馳。”另一方面他又痛心于傳統的失落,“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這事實明顯的代表著我們文化衰落,至于消滅的現象。”②梁思成:《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凝動的音樂》,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09頁。這種矛盾與困惑似乎注定了梁思成在建國后歲月中的悲劇性角色。
建筑文化的道路是走復興傳統還是全面現代化,從 1920、30年代開始成為中國建筑界一個綿延不斷的爭論話題,而官方態度始終是明確倡導民族化,而且這種官方建筑文化政策的牽引力量非常強大。然而,如果認為在官方幫助下傳統大屋頂能夠起死回生乃至再度復興,則未免過于一相情愿,官方文化導向具有強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官方寧可按照自己的意愿仿造出無數的大屋頂贗品,也不愿意修復身邊歷史承傳下來的真正古跡,甚至不惜去破壞、毀滅它們。當梁思成倡導的北京舊城保護與官方追求的工業化、現代化目標相沖突時,他的保護規劃被毫不猶豫的無情拋棄,北京城墻被拆除的命運已經注定;當他大力倡導并得到官方推動的大屋頂的“民族形式”陷入功能、經濟的困局時,他又成為“反浪費”運動的替罪羊而受到批判。1970年代初,當梁思成在落寞中死去時,各地的傳統建筑文化遺產正在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驟雨式破壞,而他曾經熱切地進行理論闡釋和演繹的建筑政治化也已經墮落為“極左”的文化怪胎,我們已經無法臆測此時他的心情是悲哀抑或是麻木?
梁思成希望傳統建筑遺產得到保護,更渴望在新的時代發揚光大,他希望通過政治和官方意識形態的力量實現自己的夢想,卻打開了建筑文化政治化的潘多拉之盒。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經寫道,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卻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斗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人們還想象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梁思成的悲劇不也是如此嗎?
梁思成是在寂寞和悲涼中逝去的,今天卻又在莫名的喧囂中被各式各樣的理由“懷念”著。浮躁的喧囂只是歷史長河中水面的浮萍,惟有真誠才是支撐歷史進步的堅實支點,從他的學術悲劇、文化悲劇和政治悲劇中汲取歷史教訓,也許是對梁思成最好的紀念!
T U-8
A
1003—4145[2010]10—0164—04
2010-09-01
鄧慶坦,山東建筑大學建筑城規學院副教授,建筑設計及其理論專業博士,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