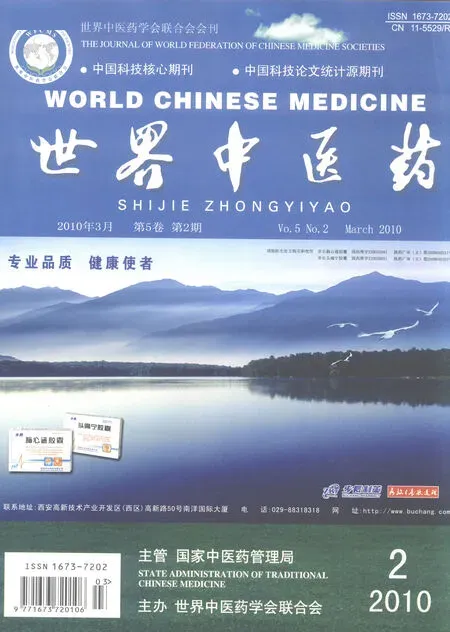中醫(yī)中藥治療惡性腫瘤的一些策略和對若干問題的思考
蔡霄月 徐振曄
(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yī)院腫瘤科,上海市宛平南路 725號,200032)
近年來,對惡性腫瘤的治療越來越強調根據不同疾病分期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治療。隨著治療藥物的不斷更新,治療方案的不斷改進,個體化治療理念的逐步形成,中醫(yī)藥如何尋找與現代治療手段適合的切入點,完善中西醫(yī)結合的模式,在抗腫瘤術后復發(fā)轉移,改善患者生活質量、延長生存期等方面發(fā)揮中醫(yī)藥獨特的優(yōu)勢。現僅就非小細胞肺癌(NSCLC)現代治療過程中的若干問題以及中醫(yī)藥在整個綜合治療過程中的定位和發(fā)展談幾點思考。
1 中醫(yī)藥治療介入的時機:中藥介入要趁早,分階段貫穿全程
目前臨床對中醫(yī)藥介入肺癌綜合治療的時機,沒有一個明確的認定。甚至存在這樣的誤區(qū),認為中醫(yī)藥是現代醫(yī)學無效情況下的一種補充手段,早期無需中藥干預。而筆者一直認為,中醫(yī)藥應貫穿于整個腫瘤治療的過程中,中藥介入要趁早。以早中期 NSCLC為例,具體可分三步走[1]:
第一階段:術后 1周即可行中醫(yī)藥扶正治療。手術是早中期 NSCLC的主要治療手段。但手術在清除局部腫瘤的同時,也打破了機體內環(huán)境的整體平衡狀態(tài)。1)手術具有創(chuàng)傷性,使患者正氣受損,氣血耗傷,陰陽失衡,免疫力下降,令癌細胞“乘虛而入”,能夠逃避機體的免疫監(jiān)視,導致轉移相關基因活化,介導癌癥復發(fā)轉移的發(fā)生。2)手術存在局限性,無法徹底根除隱匿的病灶。殘余癌旁組織及亞臨床癌灶細胞一旦解除休眠狀態(tài),進入增殖期,便可成為癌癥復發(fā)轉移的原因。3)手術客觀上在一定時期內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對肺癌患者手術前后生活質量動態(tài)的評估結果顯示,術后半年內患者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心肺功能受損,呼吸受限,慢性疼痛,生活質量功能評分下降等[2]。尤其部分術后死亡高危人群及術后生存質量明顯降低的患者,有明確的藥物干預指征[3]。故在治療上,應盡早介入中醫(yī)藥,一般持續(xù)扶正治療 2~3周。
第二階段:與術后輔助治療同步,增效減毒。輔助化療能減少早中期肺癌術后遠道轉移的發(fā)生率,5年生存可提高 5%左右。故術后扶正治療后,需行輔助化療,這是現代醫(yī)學“祛邪”的階段。但放、化療易傷陰耗氣,損傷脾胃,患者在“祛邪”階段多見神疲乏力、腰膝酸軟、胃脘嘈雜、惡心納呆等腎精虧損,濕熱內蘊之證。此時同步配合中醫(yī)藥,投以益氣養(yǎng)精,清熱化濕和胃之劑,可奏減毒抗瘤增效之功[4-5]。
第三階段:抗復發(fā)轉移,扶正與祛邪并重。西醫(yī)一般認為,手術和化療周期完成后,基本上已完成了整個治療方案。但事實上,這種“被動”“靜止”的思維方式并不能有效降低腫瘤的術后復發(fā)轉移率。手術和放、化療雖然可以清除局部的瘤體,但卻無法改變患者機體致癌的內環(huán)境。從理論上講,現代醫(yī)學對瘤體的控制較好,而中醫(yī)則對腫瘤的環(huán)境(人)起作用,也就是對患者易感體質的調整,對患者機體內環(huán)境陰陽運行的平衡。
臨床上,我們對辨證為氣虛型和陰陽兩虛型的患者,擬扶正與祛邪并重,予參芪扶正注射液合華蟾素注射液靜脈給藥。辨證為脾虛濕阻和氣陰兩虛型的患者則選用康萊特注射液。一般化療結束后,每 3個月治療 1次,4個療程為宜。在靜脈滴注用藥期間,通過辨證論治,結合口服扶正抗癌的中藥湯劑依然是一個重要的治療手段。
2 老年晚期NSCLC:中醫(yī)藥治療具有更大的優(yōu)勢和特色
晚期老年患者通常免疫力低下,多伴有慢性疾患,骨髓儲備功能減退,放化療耐受性差,導致治療受限,影響了其生存期和生活質量[6]。筆者認為,解決的途徑有三條:一是采取中西醫(yī)結合治療,以前對年齡 >70的老年患者不主張進行化療,新的觀點認為,年齡并非限制化療的唯一因素[7]。中醫(yī)藥增效減毒的作用能保證化療周期的完成;國內多項臨床試驗表明:中醫(yī)藥治療與化療聯(lián)合,可延長晚期 NSCLC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質量[8-12]。二是針對一般狀況差、或因故不能耐受或不能接受化、放療的患者,中醫(yī)藥治療則是最佳的選擇。肺癌系整體屬虛,局部屬實,虛實夾雜的全身性疾病。此類患者若見脾胃受損,運化不全者,當治擬扶正培土,固護胃氣;若見年事已高,腎氣虧虛,或久病及腎,陰陽偏衰者,當治擬益氣養(yǎng)精,平衡陰陽;若久病入絡,兼有痰瘀互結之證,則當酌加清熱化痰,散結消瘀之品,蓋臨證當分清正虛邪實,輕重緩急,及時糾正機體內環(huán)境的陰陽失調,靈活立法施治。三是靶向治療與中醫(yī)藥的切入。靶向治療由于其特殊的作用機制和低毒副作用的特點而廣受關注,臨床上多作為晚期NSCLC的二線或三線治療。中醫(yī)藥切入靶向治療的模式和中醫(yī)藥與化療聯(lián)合治療不同。因為化療藥物的選擇性弱,殺傷力強,故中醫(yī)藥的介入首先以減毒為目的,一般不主張在化療的同時施加祛邪藥。而靶向藥物的作用途徑與化療藥物不同,并不是對腫瘤細胞的直接殺傷,而是著眼于控制和改變腫瘤賴以生存的微環(huán)境,其毒副作用較輕。中藥的介入除了減毒外,更注重以辨證施治,扶正與祛邪并舉,使中醫(yī)藥與靶向治療聯(lián)合協(xié)同抗癌。
3 腫瘤中醫(yī)辨證分型過于復雜:證候的客觀化研究不妨著眼于舌診
證候是中醫(yī)學特有的診斷概念,是疾病發(fā)生和演變過程中某階段本質的反映。目前中醫(yī)證候的規(guī)范缺乏統(tǒng)一的標準,中醫(yī)證候的深入研究缺乏統(tǒng)一的客觀基礎,這些問題直接影響了中醫(yī)治療惡性腫瘤規(guī)范化治療方案的推進,以及客觀化療效評價的確立。
雖然近年來對肺癌中醫(yī)證候分型和某些細胞因子等蛋白質多肽、各種腫瘤標志物、免疫學改變以及微循環(huán)相關等指標之間的聯(lián)系探討較多,力求通過觀察所選指標在不同中醫(yī)證候的差異表達,探求“證”的本質,尋找判別不同證候的客觀化指標。然而,這些指標過分傾向于現代醫(yī)學,不能體現中醫(yī)認識疾病的整體觀。根據我們長期的臨床經驗,腫瘤辨證分型研究應著眼于舌診。將中醫(yī)辨證與現代舌象信息采集及舌苔組織分子生物學相結合,打開中醫(yī)證候分型客觀化的新思路。理由如下:1)舌象客觀化識別方法的發(fā)展:傳統(tǒng)的舌診依賴于主觀經驗,客觀性和一致性較差。而現代基于數字圖像技術的中醫(yī)舌診現代化研究實現了舌象信息的采集,舌色、苔質、裂紋、舌動態(tài)特征等指標的探索分析,為舌象客觀化奠定了技術基礎[13]。2)臨床常有舍癥舍脈重舌而論治:清代吳坤安曰:“病之經絡 、臟腑 、營衛(wèi) 、表里 、陰陽 、寒熱 、虛實,畢形于舌,故辨證以舌為主,而以脈癥兼參之,此要法也。”而在當代對 4400例醫(yī)案統(tǒng)計發(fā)現:有舌診記載的醫(yī)案占所有醫(yī)案總數的 91.86%[14]。由此可見,舌診在臨床辨證論治的地位相當高。3)舌診,中醫(yī)與現代醫(yī)學的結合點:舌診,是中醫(yī)“四診”之一。《臨證驗舌法》有云:“凡內外雜證,亦無一不呈其形,著其色于舌……據舌以分虛實,而虛實不爽焉;據舌以分陰陽,面陰陽不謬焉;據舌以分臟腑,配主方,而臟腑不差,主方不誤焉。”舌象是病證本質的局部反映。通過辨識舌體、舌質、舌苔、絡脈,可以分清陰陽、虛實、病位,據此處方有的放矢,故“不誤焉”。足見舌診在中醫(yī)辨證論治中的重要性。
4 中醫(yī)藥療效評價的現狀:有趨勢,少證據
目前在肺癌的綜合治療中,使用中醫(yī)藥治療尚未在大范圍內得到廣泛應用。主要原因如下:1)缺乏循證醫(yī)學的證據:目前中醫(yī)個案、專家經驗或觀點的評價居多,缺少多中心、雙盲、隨機、大樣本的臨床觀察資料,缺乏循證醫(yī)學的證據;由于治法方藥的不同導致臨床療效參差不齊,缺乏系統(tǒng)的操作規(guī)程,重復性差,尚未形成規(guī)范化的治療方案。2)中醫(yī)療效評價體系不完備,尤其缺乏能體現中醫(yī)特色的生活質量量表:現在國內公認比較完善的中醫(yī)臨床療效評價體系主要從以下3個板塊構建[15]:a.對于“病”的公認的常規(guī)療效評價指標;b.構成“證”變化的評價指標;c.生活質量的評價量表。除上文提及的證候客觀化問題外,采用體積生活質量量表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惡性腫瘤治療方案日益注重個體化的趨勢下,中醫(yī)藥固有的辨證統(tǒng)一的思維觀和方法論所帶來的優(yōu)勢和特點也日趨凸現。隨著中醫(yī)藥與現代科技的緊密結合,多學科的交叉滲透,包括中醫(yī)藥在內的惡性腫瘤的綜合治療必將走得更遠。
[1]徐振曄,鄭展.中醫(yī)藥分階段防治惡性腫瘤術后復發(fā)轉移優(yōu)化方案探討.中西醫(yī)結合學報,2007,1(5):5-10.
[2]Balduyck B,Hendriks J,Lauwers P,Van Schil P.Quality of life evolution after lung cancer surgery:a prospective study in 100 patients.Lung Cancer.2007 Nov;58(2):302.
[3]Cannon J,Win T.Long-term quality of life after lung resection.Thorac Surg Clin.2008 Feb;18(1):81-91.
[4]嚴桂英,徐振曄,王中奇,等.中藥抗瘤增效方對非小細胞肺癌化療增效減毒作用的臨床研究.中華實用中西醫(yī)雜志,2005,18(6):873-876.
[5]周衛(wèi)東,徐振曄,王中奇,等.抗瘤增效方對 NSCLC化療患者免疫功能及血清 VEGF、CYFRA21-1的影響.上海中醫(yī)藥雜志,2005,39(3):6-8.
[6]Asmis TR,Ding K,Seymour L,et al.Age and comorbidity 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in treatment of non small-cell lung cancer:a review of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Canada Clinical Trials Group trials.J Clin Oncol.2008 Jan 1;26(1)54-59.
[7]Pepe C,Hasan B,Winton TL,et al.Adjuvant vinorelbine and cisplatin in elderly patients: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Canada and Intergroup Study JBR.10.JClin Oncol.2007 Apr 20;25(12):1553-15561.
[8]周岱翰,林麗珠,周宜強,等.益氣除痰法延長非小細胞肺癌中位生存期的作用.中醫(yī)雜志,2005,46(8):600-602.
[9]楊宇飛,鄔冬華.癌癥惡病質患者 84例生存期、生活質量與中醫(yī)辨證論治關系的回顧性調查.中國臨床康復,2004,8(2):286-287.
[10]徐振曄,金長娟,沈德義,等.中醫(yī)藥分階段結合化療治療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臨床研究.中國中西醫(yī)結合雜志,2007,27(10):874-878.
[11]林麗珠,周岱翰,鄭心婷.中醫(yī)藥提高晚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生存質量的臨床觀察.中國中西醫(yī)結合雜志,2006,26(5):389-393.
[12]周岱翰,林麗珠,周宜強,等.中醫(yī)藥治療Ⅲ -Ⅳ期非小細胞肺癌的預后因素分析.癌癥,2005,24(10):1252-1256.
[13]沈蘭蓀,劉長江,張新峰,等.中醫(yī)舌象信息采集與分析新進展.世界科學技術,2007,9(5):97-101.
[14]陳濤,李克乾,陳茂華.4400例當代名醫(yī)醫(yī)案的舌象分布頻數分析.遼寧中醫(yī)雜志,2007,34(9):1217-1220.
[15]賴世隆.中醫(yī)藥臨床療效評價若干關鍵環(huán)節(jié)的思考.廣州中醫(yī)藥大學學報,2002,19(4):245-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