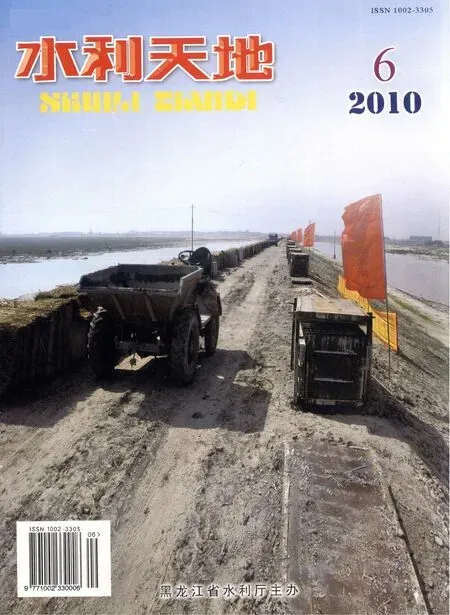農業(yè)水價改革的路徑選擇
□ 宋海鷗 母成波 馮建維
農業(yè)水價指的是農業(yè)灌溉用水價格。農業(yè)水價之所以由政府定價,主要考慮到農業(yè)是弱質產業(yè)和供水單位的唯一性,如完全放開可能會損害農民利益。但為農業(yè)服務的農業(yè)供水單位所處的困境,長期以來卻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由于長期低成本供水,致使供水設施老化失修,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骨干因工資低于稻農的收入而紛紛另行高就,農業(yè)供水單位難以為繼的矛盾日益凸顯。現階段,化解這些矛盾的途徑,可能就剩下對農業(yè)水價的進一步改革了。
單兵突進的水管體制改革
筆者認為,目前影響農業(yè)水價改革的最大難題是單兵突進的水管單位體制改革,它甚至是制約農業(yè)水價改革的第一難題。
據調查,在經濟欠發(fā)達的農業(yè)地區(qū),由于就業(yè)問題,幾十年來國有體制下的農業(yè)供水管理單位人滿為患。按照國務院《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中的定崗定編標準,絕大部分水管單位超編,最多的超編5倍以上。即使部分已經進行了水管體制改革的單位,還要承擔已減人員的各項養(yǎng)老、醫(yī)療費用甚至部分生活費,這一方面使農業(yè)供水管理單位不堪重負,另一方面是農民不肯接受成本價,在目前實收水價普遍低于成本價30%左右收費的情況下,部分農民也以各種理由拒交,甚至出現暴力拒交、打傷警察的現象。
哈爾濱市農田水利管理總站站長張云弟指出,十幾年的實踐已經證明:造成農業(yè)水價改革長期蹣跚前行的根本原因,是農業(yè)水價改革缺少水管單位體制改革這個前置條件和基礎。今天農業(yè)水價改革所有亂像的根源,是水管單位體制改革長期難以到位,而水管單位體制改革陷于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從國家層面上就缺少人事編制部門的支持和全社會各項改革的齊頭并進,單兵突進的水管單位體制改革已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中。
關于水管體制改革,綏化市水務局副局長李海波對此深有感觸:按照國務院《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水管單位體制改革已進行了多年,具體的定崗定編標準也已頒布,但在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水管單位存在著大量的富余人員,就是把水管單位的人員定額定得很高,仍需普遍的大批裁員。減人,則是對基層政權的一大考驗,尤其是同一單位工作的人,一批人進入吃“皇糧”了,另一批被減下崗,這將十分殘酷。由于矛盾太大,和缺少人事編制部門的配套安置措施,致使黑龍江省大多數水管單位無法進行裁員,因此水管體制改革在基層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這使很多基層水管單位內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事業(yè)單位改革是全國的事,水利行業(yè)的單兵突進必然困難重重。
除了減員的難題外,另一難題是水管單位改革后,編制內在職人員經費、離退休人員經費、辦公經費等支出由同級財政負擔。五常市水務局局長李國安說,由于1994年國稅、地稅分開后,80%左右的稅收收入被中央財政拿走,縣級一般僅剩百分之十幾,造成了縣級事多錢少,目前在黑龍江省的65個縣中,有56個靠上級財政轉移支付維持。因此縣級政府在水管單位體制改革中普遍強調:我們現有的開支還靠財政轉移支付呢,省政府如要給水利職工劃入財政開支的編制,那就給我們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的金額好了,開空頭支票式的督辦沒有用。什么時候省財政轉移支付的錢調整時包含了水管體制改革的,才能把水管體制改革從“文件”化為現實。
我們看到,作為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的縣級財力十分有限,現有的財政收入就無法滿足本級財政支出,更遑論再增加吃財政飯的人了。據了解,就是財力好的縣,目前每個縣每年至多能增加幾個吃財政飯的編制。而依照水管體制改革的要求,很多縣一次要增加上百個甚至更多吃財政飯的人。
為此,業(yè)內的有識之士指出:水管體制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即把水管單位劃分為純公益、準公益等,然后定崗定編,最后該由公共財政負擔的由公共財政埋單,該推向市場的就讓他們去市場上自謀生路。
但目前縣級財政稅收的現狀是:1994年國稅、地稅分家后,縣級分到的事權多、財權少,這在經濟欠發(fā)達省份尤其突出。即便按市場經濟要求,很多屬于提供公共產品的人員,仍舊不能吃上財政飯。更何況嚴格、準確地落實《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后,水管單位還要大批裁人呢?
綜上分析,完全落實《水利工程管理體制改革實施意見》還很遙遠,因為當時發(fā)文的國務院辦公廳,就僅僅把這個文件叫做《實施意見》而沒叫做規(guī)定。這說明,發(fā)文之初有關部門就知道,完全實現水管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多年以后的事。問題的原因是改革措施與現實缺乏有機關聯,即政令不通的原因,在于這項涉及到全國47萬多水管單位職工切身利益的改革,在基層是不具可操作性的。
以上是農業(yè)供水單位難以為繼且短期內無法解決的硬傷,是制約農業(yè)水價改革的第一難題。
為了跳出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境,南方極個別有經濟實力的縣為了回避矛盾,簡單采取了取消農業(yè)水費,農業(yè)供水單位由縣財政出錢全額供養(yǎng),但其后果是農民不再節(jié)水,用有限的水資源去澆更多地以造福更多農民的目標付之東流。
改革的路徑
通過對上述眾多矛盾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單靠水利行業(yè)一家來推動農業(yè)水價改革幾乎是不可能,但我國農業(yè)的基礎——灌區(qū)又普遍難以維持,在這個兩難的夾縫中,現階段如想繼續(xù)維持農業(yè)灌溉,除了加大水利工程供水是商品的宣傳,努力推動系統性的相關改革之外,由公共財政給農業(yè)水價以補貼,是解決難題的最佳選項。
多年從事農業(yè)水價工作的慶安縣水務局副局長白建學指出,灌溉農業(yè)作為我國糧食安全的基礎,正面臨著單兵突進的水利工程管理單位體制改革無法實現,農民不接受物價和水利部門算出的成本價,地方政府不肯按成本價批準農業(yè)水價,這就造成了農業(yè)供水單位的癱瘓甚至破產。在國家重視農業(yè),投入不斷加大,粳稻收購價連年提高使水田單位面積效益是旱田2~3倍的大環(huán)境下,保守估計,黑龍江省每年仍有幾十萬畝水田因設施老化、淤積嚴重而被迫水改旱。這足以說明:作為中國商品糧第一調出大省,其灌溉農業(yè)正在呈現出一邊是各級財政出資增加面積,一邊是因水價和體制改革問題在減少面積的矛盾。
既然上述體制機制的問題目前無法解決,農民和地方政府都不能接受成本水價,那就只有由公共財政給農業(yè)水價以補貼了。
我們建議的具體路徑是:首先引入第三方,測算出農民、水利工程管理單位和政府都認可的成本水價,然后由地方政府與農民協商后,確定一個各方可以接受的價格,由縣級政府批準后,從農民手中收取。從目前的情況看,這個價格通常是成本水價的70%。縣級政府所批水價與成本水價的差額部分,由中央財政承擔。既然種糧是為了國家的糧食安全,相關改革的推動也在高層,那國家理應負起部分責任。
五常市水務局副局長單景芳告訴記者,按照國家的事業(yè)單位改革方案,農業(yè)灌溉管理單位被定位為準公益事業(yè)單位。準公益的農業(yè)灌溉管理單位是什么概念?就是灌溉管理單位所提供的灌溉水是半公共品,半公共品灌溉水的成本構成,應是一部分從用水戶收取,一部分由公共財政出。為了避免扯皮和縣級政府不負責任,這項補貼的另一個前置條件是各方首先明確具體的灌溉面積,然后中央政府確定每畝補貼標準,更合理的是按產量補貼,但計算復雜。如果縣級政府批準的從農民手中收取的農業(yè)水價加上中央財政補貼,尚達不到成本水價的,其差額由縣級政府補足。否則,縣級政府就提價并負責確保足額收費,提價的幅度應以加上中央財政補貼后不超過成本價為準。
以上建議的本質,是找到一個政府財力能承受,農民能接受和灌溉站能保本運行的平衡點。
既然用占總耕地面積48%的灌區(qū)生產了占我國總產量75%的糧食,那就應該像其他農業(yè)直補一樣,給農業(yè)水價補貼。
這里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多年來各界一直在呼吁關注農業(yè)供水單位難以為繼,長期虧損運行,缺少維修養(yǎng)護和更新改造資金,水利工程普遍嚴重老化失修,灌區(qū)職工長期不能足額開支的現狀。事實上,發(fā)展至今天,很多農民已經因灌區(qū)渠道淤積和田間設施損壞,而被迫將效益高的水田改成旱田。更為可怕的是:長期低工資甚至是低于稻農收入的結果,是技術骨干的大量另尋高就,留下繼續(xù)“混”的,大多是沒有業(yè)務專長的人。在很多灌區(qū),連一個懂養(yǎng)護工程、清淤時放線的技術人員都找不到。
可見,大多數農業(yè)灌溉設施普遍存在著工程老化失修和渠道淤積后灌溉面積達不到設計能力,灌溉管理單位人員普遍超編,灌溉水費(價)普遍達不到成本,農民和政府普遍不接受進一步提高水費(價);政府對灌溉管理單位這種準公益事業(yè)單位的財政支持普遍缺位,但在強制灌溉管理單位必須供水上又普遍越位。這諸多的“普遍”,直接造成了灌溉管理單位的難以為繼,進而威脅到我國的糧食安全。
因此,只有政府首先樹立起水利工程供水與電一樣是商品,改變強迫灌區(qū)在農民拖欠水費時仍要供水,解決政府越位向灌區(qū)安置人員,根據國情和各方博弈結果適當給農業(yè)水價補貼之后,才能扭轉已有灌區(qū)的繼續(xù)棄灌,以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