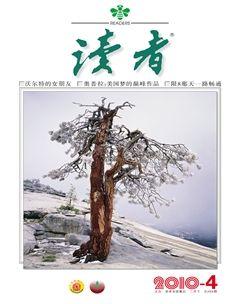誰念西風獨自涼
1931年4月29日,清華的校慶。早就聽說在那天的校慶上將要上演易卜生的《娜拉》,自小酷愛音樂的鄭秀不由分說拉了同學去看。那次,她深深地被臺上女主角從容、熟練又富有情感的表演吸引住了。
演出結束后,演員卸了妝從后臺走出來。身邊的一位同學指著那位圓臉、戴一副近視鏡、身穿長布衫的男青年向她介紹:“喏,他就是剛才臺上演娜拉的那一位,名字叫萬家寶。”
那是他們的初遇。那一年,鄭秀還是一名快樂單純的高中女生,曹禺已是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的學生。那次匆匆相遇,又匆匆道別,他只覺她清麗可愛,她只慕他才華橫溢,彼此之間卻并未作深的交談——不過一面之緣。
彼此熟識,是兩年后。1933年春天,一年一度的清華校慶戲劇排練又開始了。那一次,熱愛話劇的幾個同學決定排演英國杰出劇作家高爾斯華綏的話劇《最前的與最后的》。劇本很快由曹禺譯成了中文,全劇只有哥哥、弟弟、女孩三個角色。劇中的哥哥和弟弟很快找到了人選,曹禺建議讓孫毓棠演哥哥,他演弟弟。談到女孩汪達的角色時,大家一時犯了難。最后,還是由曹禺敲定:“讓法律系的鄭秀來演吧!聽說她在中學演過戲。”
那一場戲,拉開了曹禺與鄭秀相戀的大幕。近一個月的彩排,他們朝夕相處,共同切磋。每次排練完畢,曹禺還要送鄭秀回到她的宿舍。那一場傾注了他們共同心血的戲劇,演出非常成功,竟然接連公演了七八場之多。戲劇演出結束時,他和她的愛情也已如火如荼。只是那時她還年少,面對如此火熱的愛情,她還有些手足無措。她開始刻意地躲著曹禺,可躲開的是人,躲不開的是情。聽說曹禺為她大病,她再也顧不得許多,跑到曹禺床前,與他緊緊相擁。就此,鄭秀把自己的幸福,輕輕地交到了那個多才亦多情的男子曹禺手上。
那年暑假,曹禺留在校園沒有回天津的家,他要求鄭秀也不要回南京。在清華園圖書館的西洋文學系閱覽大廳的東北一隅,靠近借書臺的一張長條桌的一端,他和她相對而坐,除了低聲交談一兩句之外,便分別做著自己的事。曹禺埋頭創作劇本《雷雨》,鄭秀用工整娟秀的字跡謄寫出來。1933年8月初,初稿完成。深秋,《雷雨》在清華園誕生了。當時曹禺只有二十三歲,是清華大學研究院的研究生。而鄭秀,是《雷雨》的第一位忠實的讀者。
1936年11月26日,經過三年的戀愛之后,他們在南京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典禮。1938年春,曹禺和鄭秀同赴已撤到長沙的國立劇校。他們在長沙舉行了簡單的婚禮。他們的婚姻曾被眾多文化界名人看好與祝福,只可惜世事難料,情路難猜。婚后僅兩年,他們便發現彼此在性格、志趣、生活習慣上有著諸多的矛盾。在曹禺的眼里,戲劇就是他的神圣殿堂,在日常生活中,他一向不修邊幅,有時還顯得心不在焉。與他恰恰相反,鄭秀卻是一個特別注重儀表又愛干凈的女子,再加上曹禺一心撲在工作上,對鄭秀越來越冷落,兩個人的小爭小吵就不斷出現。在鄭秀生了兩個女兒后,由于另一個女子的介入,他們的感情已走向破裂的邊緣。只是那時她心有不甘,明知那段愛情已死,還在死死地守護。為此,她甚至不惜放棄自己的血脈親情。
1948年底,上海龍華機場,鄭秀站在機場上焦急地等待著曹禺出現,可直到她身后的飛機即將起飛,她等的那個人都沒有來。頭發花白的老父親在她身后焦灼地大喊:“他不會來了,快隨我走吧!”“不!他不去,我們也不去!”任身后老父親的呼喚再焦灼,她還是拉著孩子決絕地走上了回程的路。飛機起飛,從此海天相隔,她與父親就此永訣。只是那樣的訣別,仍沒有換來愛情的回轉。1950年,在他們分居了近十年之后,她終于含淚答應了他離婚的請求。
“過去我愛曹禺,嫁給了他,現在我還是愛他。我同意離婚,因為我希望他幸福。”面對前去勸說她的朋友,她如是說。
此后,曹禺與第二任妻子方瑞結婚。后來方瑞去世,他又與著名戲劇表演藝術家李玉茹演繹了一段中國版的《金色池塘》,在中國戲劇界留下了一段愛情佳話。曹禺年事漸高,身體不好,在醫院躺了八年。那八年里,一直都有李玉茹的悉心照料與陪伴。
相比之下,鄭秀的生命就單調灰暗了許多。與曹禺離婚后,她沒有再嫁。1989年,她在去世前夕表示想見曹禺最后一面,但那個愿望終究成空。
在談及那段不美滿的婚姻時,曹禺曾說:“在這件事上,她有錯,我也有錯。”可她愛了他一生,也為他孤苦伶仃地守了一生,卻是誰也抹殺不了的事實。
“文革”期間,曹禺被審查,每天早晨要掃大街。鄭秀看在眼里卻無力相助,只能在每個早晨他出門來掃大街時,默默地站在遠處看著他。誰說那種無聲的陪伴不是一種無聲的愛呢?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納蘭性德的《浣溪沙》將那種人生的孤獨和凄涼勾勒得讓人觸目驚心。鄭秀,這位出身官宦之家又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曾同曹禺幸福地牽手又無奈地別離,如若也讀這首詞,是否該有特別的涼意從心底升起?
(孟憲忠摘自梅寒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