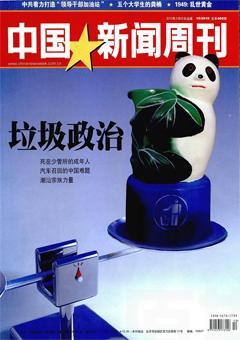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善堂
龐清輝


“即使建立了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很難無微不至地照顧到每一個孤兒與老人。”而善堂,就填補了這其中的空白。
2010年1月14日,汕頭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湖南來汕頭打工的李湘軍身受重傷,躺在醫院一層一個四人間的簡陋病房里。
進行了簡單急救的李湘軍,無奈地躺著,沒有進行進一步的治療。
1月12日一大早,李湘軍制止了一個正在偷車的偷車賊,卻被其手持一米長的砍刀砍了30多刀。
110隨后趕來,把李湘軍送進汕頭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警察認可李湘軍的見義勇為,但是對于醫治的醫藥費則不能墊付,“要層層報批”。
汕頭市的存心善堂,在看到有關李湘軍的電視報道后,派副會長范進樂給李湘軍送來3萬塊錢。
范進樂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等政府批下來什么都晚了。善堂有非常靈活的應急機制,只要認為扶持李湘軍這種社會正氣值得,就能迅速啟動應急機制。”
潮汕地區十分發達的善堂,是一種帶有宗教色彩般的民間慈善機構。自明清時起,善堂就開始施醫贈藥、施殮施棺、救貧濟困、養老育嬰、發埋孤骨、敬惜紙字及興辦義學。建國后,善堂一度蕭條。改革開放后,善堂重新發揮作用,也從比較單純的傳統慈善救濟,逐漸向社會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務轉型。
善堂所提供的服務涵蓋了很多范圍,甚至是社會基本保障的范圍,如“養老院”“樂齡護理中心”等。而其興辦的“義塾”“特殊學校”,則屬于義務教育范圍。“修橋造路、建學校、建醫院、建消防隊。他們甚至把救火都當做是他們的本分。”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顧問、汕頭大學原黨委書記黃贊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善堂肩負著很多并不屬于慈善救濟事業的多種職能,已經覆蓋了民眾社會生活保障的方方面面。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善堂。”據統計,在近1萬多平方公里、1300多萬人口的潮汕地區,有近1000家大大小小的民間善堂。差不多每一個村,就有一個善堂。
最早用來收養被棄的女嬰
存心善堂是汕頭市最大的一家善堂,建于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善堂位于汕頭市外馬路57號,由一組三座并列相連的廟堂式古建筑組成。
存心善堂會長蔡木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存心善堂最早是一座用來收養女嬰的棄嬰堂。在建國前,潮汕地區重男輕女的風氣嚴重,很多人基于家族或者貧困的原因,把女嬰拋棄在被認為是內陸盡頭、省尾國角的汕頭海邊。
在清末、民國以及汕頭淪陷日偽時期,政府基本處于癱瘓的狀態。“當時社會的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都是由民間承擔。”于是,存心兒童教養院、存心醫院、存心學校、存心施粥局、存心掩埋隊、存心救護隊、存心義山等一系列救助機構相繼成立,扶貧救困、賑濟饑民。“在戰亂時,存心掩埋隊曾一天收埋1200具尸骸,收尸的數量以百萬計。”
1927年,在海內外華僑資金的支持下,存心善堂還修建了用于消防的存心水龍局。存心水龍局擁有汕頭歷史上第一輛消防車。蔡木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當時購買了三輛消防車,都是從西德進口,用了兩年的時間才運到中國。”
如今的存心善堂,還有粵東第一家公益慈善診所“存心善堂診所”,免費為窮困的民眾治療和取藥;類似的則還有“存心慈善園”,為孤寡殘疾老人免費提供衣、食、住、醫、送終服務;“存心特教學校”,免費為殘疾智障兒童提供特殊教育;“存心快餐廳”,全年免費向社會殘疾人供應每日三餐。而《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餐廳門口看到,領餐的還有社會低保特困戶、空巢老人、單親戶及周邊困難群眾。
“免費也是有條件的,善堂有自己的救助制度。”蔡木通對記者說,需要幫助者要填申請表,低保特困戶要有居委會或街道辦事處的證明,生病的則要有醫院的證明。
不久前,存心善堂還啟動了民間慈善交通救濟金,按照交警部門的有效證明,對交通肇事、交通傷害、交通死亡、交通逃逸等4類需緊急救助者提供及時的資金幫助。如果救助者發生交通事故后家庭非常困難,還會按月向救助者家里發放大米和食油等用品。
“宗教、姓氏、國別都不計較,只看你值不值得幫助。”蔡木通說,善堂的救助和保障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補充,“錢要用對地方”。
經費從何而來
善堂收入的固定來源,是善堂會員繳納的類似于會費的款項。蔡木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有近兩萬會員,這些會員中有汕頭市居民、有外來打工人員、有商人、也有普通工薪階層的成員,具有草根慈善的性質。
另外,潮汕地區海外華僑很多,偶爾也會有華僑把行善的款項捐在善堂。
善堂內也設有功德箱,有人進來會捐贈一些錢物。一位趙姓家庭主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她和姐妹們經常會湊錢買一兩包米捐贈到善堂,“捐多少不拘,哪怕是捐一塊錢在這也不會受到歧視。”
存心善堂收到的捐贈物品五花八門。舊衣服、舊家具、護理工具、輪椅等皆有。
善堂的財務支出非常公開。善堂的支出每三個月都要上報當地審計部門一次。除了審計部門的財務審計,善堂內部還設有監事會和耆老會共同監督理事會。每年正月初九,善堂開會員大會之時,善堂的會計人員則會把所有開支都掛在墻上,受所有捐款者監督。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汕頭慈善總會存心善堂福利會(2008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樂捐善款及實物的財務收支情況的專項審計報告)》中看到:一年半來,該善堂募集的善款1984多萬元,募集大米63.5多萬斤、食用油1.6多萬斤,伊面4.6多萬件。同時募集南方雪災的賑災物資價值65萬元、募集四川汶川地震賑災物資價值322萬元。
“一年發放1400多萬的善款,相當于一個區縣級的民政局。”蔡木通說。
2008年雪災時,大量返鄉民工滯留汕頭火車站,“政府還沒響應,善堂里150個義工24小時三班倒,堅持了十五天”,為滯留旅客免費提供御寒衣物、棉被以及速食面、麥片、姜湯等。
存心善堂負責救濟救災的76歲老人陳文元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8年雪災,他曾經在冰天雪地中押送善堂籌集的9卡車生活必需品到達湖南郴州;汶川地震時,經過三天三夜近3000公里的長途跋涉,押送了發電機、帳篷等7車物資奔赴四川什邡災區,從四川回到汕頭后,又籌集救災物資從汕頭奔赴甘肅文縣。
“善堂的老人就是想做善事,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們更信任善堂,更愿意把錢捐給善堂。”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顧問、汕頭大學原黨委書記黃贊發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沒有傳統和宗教作為支柱,善堂很難長久”
走在汕頭拐來拐去的大街小巷里,經常可以看到各種小的善堂善會,幾個老人煮各種各樣的中草藥涼茶,擺在路邊,路過的人、三輪車夫、環衛工人都會停下來喝兩口。
汕頭外馬路上的榕香蠔烙飯店,每天提供80份的免費炒飯。每到中午十一點,飯店門口的大榕樹下就會排著長長的隊。乞丐、干苦力的、撿垃圾的、環衛工人、鄰街的老人常在隊伍中。飯店老板蔡乳武為貧困人群提供免費午飯已經有16年,中間也經常會有人拿油米給飯店。“給錢的我都不要,給油米的,都是小時候吃過人家飯的。”
潮汕人的先民多來自中原,有的是征戰士兵,有的是舉家而遷的災民,有的是因家族或村落爭斗而被迫南遷的難民。在長途遷徙中,扶老攜幼,歷經顛簸,方達潮地。但在這個“蠻荒”之地,等待他們的仍是艱辛的生存環境。“重信仰,尋寄托,求庇佑,是絕大多數潮汕人的心理形態。”黃贊發說。
也因此,潮汕人對諸神都很崇拜。記者在汕頭云湖庵就看到有佛、有道、又有地方神擺在一起的祭拜形式,甚至把最早建立善堂行善的大峰大師也作為神來崇拜。存心善堂所在的外馬路上,則既有善堂這樣的地道中式古建筑,也有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的典型西洋樓房。
善堂也經常舉行各種大小傳統宗教儀式和活動,接受各界捐贈。“把傳統活動作為凝聚社會的力量,變為慈善活動。”蔡木通告訴記者,“沒有傳統和宗教作為支柱,善堂很難長久。”
靠海的潮汕人還有怒海討生的風俗習慣。如今,海內海外各有潮人一千多萬,“海內有一個潮州,海外也有一個潮州”。
善堂文化也隨著潮人離鄉背井出洋。他們離鄉時,往往捧著某善堂或神廟香火,一起渡洋,待到事業有成,生活改善,便合建善堂或神廟,作為敬奉處、思鄉所、會聚點,并以善堂為機構組織救困扶危。為后來出洋的潮人提供食宿,幫忙找工作,為當地國家解決了很多移民問題。
現在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以及香港、臺灣等地都先后出現了善堂機構,“在泰國曼谷街頭,如果發生交通事故,很可能公立醫院的救護車還沒到,泰國報德善堂的車已經到了。”蔡木通告訴記者,泰國報德善堂醫院里面的血漿、骨髓比國內醫院的還多。
全國政協副主席李金華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曾告訴記者,如今他很關心中國的慈善事業,慈善是社會保障和緩解貧富差距的一個補充,“更難得的,還有對精神的陶冶”。
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
善堂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
以存心善堂為例,1953年,存心善堂曾經作為封建財產被沒收。1985年,存心善堂等多家善堂集體上書要求正確看待善堂的作用,“行善不是迷信,善堂沒有了很多社會服務都沒有人做了”,終獲批準。
1995年,由于善堂所在地的產權等原因,“社會團體財產歸人民所有”,存心善堂被強制取締。
2003年,經汕頭市民政局、民間組織管理局正式批準,存心善堂為汕頭市慈善總會分支機構,全稱“汕頭慈善總會存心善堂福利會”,但存心善堂不可以再設分支機構,它下面的學校,文武學校、養老院、慈善診所等不能獨立開展活動。直到2009年,存心善堂獨立登記,成為獨立法人,全稱汕頭市存心慈善會。
汕頭市民政局副局長鐘岳峰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現在情況要發生變化,民政局作為業務主管單位,將改為業務指導單位。“作為業務指導單位,善堂要來登記,每年要年檢,財務年檢,人員、會員的變動,開展哪些活動,重大活動等都要備案,主要是敦促善堂遵守法律法規,健康規范發展,出了什么問題民政局要去清算清理。”而據記者了解,汕頭市在民政局登記的善堂,大概有46家左右。
鐘岳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汕頭市民政局也在培育慈善機構,但主要是增加政府指導下的中華慈善總會下的分支機構,“有一些情況必須由汕頭市慈善總會和汕頭市紅十字會來進行,善堂不可以公開募捐,只能依法接受捐贈,大的事情政府統籌會更好一點。”去年汶川地震,存心善堂向社會募捐拿的箱子,都冠名為“中華慈善總會”。“錢的來龍去脈,是需要政府規范的,要不沒有辦法監管。”鐘岳峰說。
上個世紀90年代,日本學者夫馬進教授對中國善會善堂史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最后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社會始終未曾產生獨立于官或超脫于“國家”和“社會”的公共領域和公共組織。而“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也曾感嘆,國際上通行的是政府購買非政府組織的服務,但中國,是非政府組織“購買”政府的服務。
2009年末,廣東省民政廳副廳長王長勝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廣東省民政廳關于進一步促進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發展的若干規定》通過,“東莞試點‘政府購買社會服務,凡是能夠由社會組織解決的事,移交給社會組織解決管理;政府通過采購或特定委托方式,購買公益性社會組織提供的社會工作服務,逐步將政府直接‘養機構、養人、辦事,轉變為向公益社會組織購買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