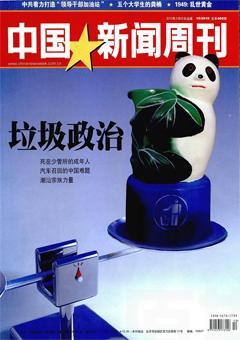好萊塢的心明鏡似的
連清川

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文明,都有主流文化和亞文化;這些亞文化或先鋒文化有可能轉化成為主流文化——端的在于時間、環境和工具的變化。
奧斯卡出來,照例又是議論紛紛。
今年的焦點,尤其是在中國,自然是一部毫無名氣的小制作影片《拆彈專家》,大破名震全球的《阿凡達》,奪得桂冠。詹姆斯·卡麥隆雖然在全球狂掃了25億美元票房,但紅地毯的主角不是他,為什么?
我們當然都知道,奧斯卡從來不是票房的背書,可從來也不是“反好萊塢者”。十余年前,卡麥隆同樣創造票房神話的《泰坦尼克號》就捧走了11項小金人,創造了奧斯卡新紀錄。奧斯卡榜上的小制作、獨立制作實在也不乏其人,比如前幾年的《撞車》和《老無所依》,都是小制作的片子。
如果你在紐約生活的話,會發現,收到的信件之中,除了最多的教會邀約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的邀請是各種各樣的展會和獨立、外國電影的放映信息,在紐約當地著名的城市指南報紙《鄉村之聲》(Village Voice)中,專門有一個版面刊發獨立電影的放映會信息。
所以,其實,我們許多關于美國生活的信息是相當錯誤的。的確,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樣庸俗的是:他們都喜歡大制作,大導演,豪華演員陣容的作品,《阿凡達》的成功自然有賴于這樣的庸俗大多數來支撐。不過,獨立電影、外國電影從來都不乏擁躉。在全美的每個城市里,幾乎都有幾個專門放映獨立制作、小制作和外國電影的影院。
美國的孩子講究個性,Lady Gaga,Adam Lambert,《阿凡達》這樣的主流當然是他們成天討論的重點,可是如果書包里沒有個把Nirvana或者《猜火車》這樣的另類、小眾片子,如何能在眾人之中顯出“酷”來?
當然,擺酷雖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可是文化的多元性早就決定了各種流派風格的藝術,都能夠在美國這個國家找到自己的土壤和生存空間。小眾電影和獨立制作在以往的歲月里由于傳播渠道被主流公司所壓制,所以自然在全世界的聲音微弱,生存狀態地下。
但實話實說,好萊塢是不會排斥小制作和獨立制作的,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金礦要長期開采下去,就必須要設定類似于像圣丹斯獨立電影節那樣的機制,來發現下一個下金蛋的母雞。來自德國的文德斯,在成名之前拍的可都是小制作的文藝片;斯皮爾伯格雖然師從上一代大師斯坦利·庫布里克,但也沒有什么特殊待遇,也是獨立制作出身。
可是這些年來,電影業的游戲規則已經悄然在發生變化了。《連線》雜志的前主編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早在前幾年名噪一時的著作《長尾理論》中指出了電影界必然要發生的巨大變革。由于互聯網的視頻網站、制作工具軟件的普及,那些缺乏資金的天才們,已經在互聯網上沸反盈天了。而以前依賴Blockbuster等這樣租碟店才能尋找到那些有限的獨立制作作品的小眾產品擁躉們,已經完全解放出來。
世界上的任何一種文明,都有主流文化和亞文化;有大眾文化,也有先鋒文化。地域文明如此,種類文明也是如此。比如中國,漢族文化自然是主流文化,但是同樣有苗族文化等亞文化;唐朝有一度曾經是佛教文化為主流,而道教文化為亞文化。這些亞文化或先鋒文化有可能轉化成為主流文化——端的在于時間、環境和工具的變化。獨立制作電影在長期的時間中,由于傳播手段的缺乏,尤其是上映銀幕的限制(他們自然無法像好萊塢的主流片場那樣投入大量的營銷資本),只能隱身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想象一下,美國每年的電影出產量在13000部。而網絡的出現顯然拯救了這些獨立制作和小制作。小眾產品中有大量的垃圾,但是天才總是不會被淹沒的。人們的注意力和時間總是有限的,于是那些意圖制造大熱門產品的電影人,需要投入的營銷費用和制作成本必須上升,才能獲得更多的青睞。小眾產品在網絡口碑去蕪存菁的大浪淘沙中,優秀者自然水落石出;大熱門或意圖大熱門者面對網絡口碑這樣的大眾利器,自然也難隱真身。于是小眾上升大眾,熱門轉成冷門。
好萊塢顯然是這個趨勢的重要“受害者”之一。雖然近些年來也有些影片在票房和藝術性上雙豐收,但是像《辛德勒的名單》《肖申克的救贖》這樣的產品實在已經難得一見。倉促上陣的好萊塢頻頻推出新的技術大作,不過近幾年除了幾部動畫片以外,表現實在差強人意。好萊塢近些年來總體票房慘淡,大公司紛紛轉型。
因此,卡麥隆實在算是好萊塢的救主了。像他這樣對大制作電影的技術革新,讓好萊塢人重燃了對大制作、豪華演員陣容和大票房的信心。3D一時成為風潮,自然拜這個電影之王所賜。因為好萊塢心里跟明鏡似的,獨立制作、小制作雖然長尾效應很大,但那不是他們的那碟腌白菜,他們的金礦還是那些庸俗的大眾們所深深沉陷的聲光電、炮彈+英雄模式。
所以,奧斯卡給了《拆彈專家》,票房給了《阿凡達》。好萊塢找到了自己的新救主,小眾粉絲找到了自己的春天,大家各得其所,還有什么比這個更加花好月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