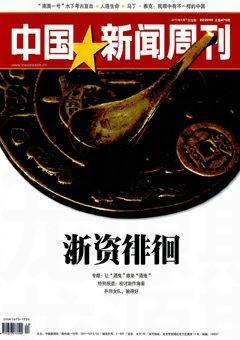檢討趙作海案
劉 剛



趙作海案余熱未消。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規定》首次明確了包括“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等6種不能用于死刑定案的證據。這被視作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巨大創新和突破。
然而回溯趙作海案,不難發現,將趙作海致罪的推手不僅僅是公安取證的刑訊逼供。這其中包括,當地鄉村的道德審判,司法界解決超期羈押的決心以及政法委的協調辦案等等
重獲自由的趙作海回到趙樓,看見圍上來的老鄉,忙不迭地遞煙,但沒有人肯接。
在趙樓村,如今的村民們還是看不起趙作海。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個男人雖說被證實沒有殺人,但至少干了偷雞摸狗的事情。
鄉村的罪人
通奸——在這個中原農村是一輩子抬不起頭的事。
這是一個被麥田包圍的平靜村莊,一條機耕道貫村而過,村民的院子鄰路而建,全村1000人上下,流言飛語從村頭到村尾的傳播用不上10分鐘。
11年前,趙振晌從趙樓村“消失”后,村民們相信他肯定已經不在人世了,“好端端的一個人,怎么就蒸發了。”與此脫不了干系的只有趙作海。
他與趙振晌此前發生過流血沖突,然后趙振晌就“消失”了。
這個簡單的邏輯在趙樓村人們的心里一開始就根深蒂固。民間旁證不斷地增加,二趙因為一個女人爭風吃醋,而且都與這個女人不清不楚,此前糾紛還動了刀子。
不管村里人怎么說,在趙振晌“消失”四個月后,警察帶走了趙作海。
調查了20多天,趙作海被放了出來。因為警方找不到更多的證據,哪怕連趙振晌的尸體都沒有。
但在許多村民心里,趙振晌的“消失”,肯定和趙作海有關。只是證據尚未出現。
趙振晌“消失”快一年半的時候,趙樓村出了一件大事。村西頭的井內,挖出了一具無名尸體。尸體已經高度腐爛,無頭,膝關節以下缺失。尸體上還壓著幾塊巨石。
當天夜里,趙作海又被派出所的民警帶走了,當時他剛從地里忙完農活回家。
那是1999年5月8日,趙47歲。
趙作海被帶走的第二天,就被刑拘,罪名是涉嫌故意殺人。
兩天后,他被帶到商丘柘城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在這里,趙作海遭遇了“生不如死”的刑訊逼供。
他先后做了9次有罪供述。這些口供也成為他日后定罪的重要依據。
在公檢法系統最終為趙作海定罪之前,這個案子在趙樓村已經被視為鐵案。和二趙不清不楚的那個女人,成為村里人眼里的蕩婦。不久趙作海的老婆也改嫁了,撇下兩個無人照看的孩子。
在趙振晌“消失”一年半之后,民間的審判系統已經結案,對于趙作海,“當地人皆曰可殺”。
但警方的取證調查還在持續。在被刑拘40天后,1999年6月19日,柘城縣檢察院對趙作海正式批捕。當時的柘城縣檢察院批捕科科長楊東平,后來成了柘城縣檢察院反瀆職局的局長。
被呈送到柘城縣檢察院批捕科的證據有:趙作海的口供,刑事技術鑒定,證人的證言以及趙振晌的失蹤。
柘城縣檢察院正是依據上述證據,做出了批捕決定。
證據不足的“兇手”
根據司法程序,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刑事案件,歸中級人民法院管轄。1999年10月,趙作海案完成了公安環節的預審后,由柘城縣檢察院公訴科報送至商丘市檢察院公訴處審查起訴。
當年,商丘市檢察院承辦此案的小組共兩人,公訴處副處長王長江牽頭,主訴檢察官是汪繼華。
“趙作海的案子就一個核心問題,尸源問題。”事隔11年,汪繼華對于趙作海案的具體細節已不清晰,但汪繼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當時初步感覺,這個案件無法確認被害人身份,所以案卷一到我手里就退了。”
汪繼華畢業于鄭州大學法學院,1997年到商丘市檢察院工作。他是一個很看重職業聲譽的人。獲得過“人民信得過檢察官”的榮譽稱號。
在當時,村里人都覺得趙作海是殺人兇手的時候,檢察官汪繼華做了退卷的決定。理由是,證據不足。
除了尸源無法確定是趙振晌,另一處疑點是兇器。
隨后,柘城縣公安局補充了一些細節,不久,案卷再次被報送到商丘市檢察院。
“但是尸源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汪繼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法規,檢察機關兩次退卷后,公安機關要么撤案放人,要么變更嫌疑人的強制措施。
1999年12月9日,商丘市檢察院第二次退卷,但趙作海卻依舊羈押在柘城縣看守所。
“如果當時釋放趙作海,社會效果無法估計,放大了講,關著他就是政治需要。”汪繼華分析,社會評判,不是專業評判,“現在趙振晌回來了,村民才知道他沒有死,才知道趙作海沒有殺人,可那時候趙振晌沒有出現,誰知道趙作海有沒有殺人?”
2001年5月,汪繼華辭職離開商丘市檢察院,與人合伙創辦河南華豫律師事務所。
一直到2002年被起訴,趙作海被超期羈押將近3年。
三堂會審
就在趙作海被羈押期間,千里之外的廣西玉林,曝光了一起因超期羈押導致的悲慘事件,掀起了社會上對超期羈押的密集關注。
在廣西玉林,1974年,謝洪武被當地公安機關以“反革命罪”拘留,此后,謝在玉林第二看守所里度過了漫漫28個春秋。
這一案例的曝光引起了司法界的反思。
超期羈押被稱為我國刑事訴訟的三大難題之一。據權威部門的統計,1993年至1999年全國政法機關每年超期羈押人數一直維持在5萬至8萬人之間。
2000年全國九屆三次人大會議上,陜西人大代表劉三陽提交了《關于對司法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實行“拖案”責任追究制的建議》,認為“拖案”數量多、涉及面廣,對社會穩定影響大,所造成的危害絕不亞于錯案。
2001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進一步清理和糾正案件超期羈押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對超期羈押問題進行全面清理,在當年6月底之前要全部糾正。
《通知》還特別提到,“在清理糾正超期羈押案件過程中,要積極爭取地方黨委、人大的領導和支持,特別是對于一些重大疑難、認識不一致而久拖不決的案件,可以專題報告黨委、人大、政法委,促進問題的積極解決。”
在此背景下,趙作海案再次啟動了司法程序。
2001年7月,中共商丘市委政法委召開協調會,政法委和公、檢、法三部門經研究認定,該案尸源問題沒有確定,仍不具備審查起訴條件,不予受理。
商丘市檢察院公訴處副處長王長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在柘城縣檢察院召開,決議要求公安局去做DNA鑒定,確定尸源。”
但DNA鑒定報告最終無法形成結論。趙作海又被持續羈押了1年多。
時間到了2002年,政法系統解決超期羈押的決心越發強烈。
5月31日,在山東省濰坊召開的全國檢察機關糾正超期羈押經驗交流會要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要切實加強對超期羈押案件的督辦力度,檢察環節存在的超期羈押案件,要在2002年6月底前全部糾正。
這一年,河南省人民檢察院、高級人民法院、公安廳等部門,為了解決超期羈押這個“老大難”問題,聯合下發了《河南省刑事訴訟超期羈押責任追究辦法》,要求嚴格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辦案期限。文件細化了案件在各個訴訟環節中的時限和責任劃分,包括檢察院要及時向辦案單位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
據官方數據,到2002年底,河南省共計清理超期羈押5000余人,遺留超期羈押案件20余人,基本實現了無超期羈押現象。
在此期間,趙作海案再度過堂。
2002年,八九月間,商丘市委政法委第二次就趙作海案召開協調會。
最終的結果是:趙作海案具備了起訴條件。
當年,決定趙作海命運的這次協調會,公檢法三家各方的具體意見如何?由于與會者三緘其口,會議紀要無從尋覓,至今仍是一個謎。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曾多次致電中共商丘原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師燦。王師燦表示,他已于協調會后第二年退休,對那次會議的情況已記不清楚。王師燦承認,他不是學法律的,而是學煤礦和礦山機電的。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調查,當時商丘市政府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張士勛,已在2008年因受賄罪被判刑。
時任商丘市公安局局長的崔保連,現已調任三門峽市,出任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時任商丘市檢察院檢察長的吳廷學,現已調任河南省檢察院。
“政法委是黨委的職能部門,代表黨委,其角色非常關鍵和微妙。”一位退休的政法委干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政法委與公檢法部門的關系,簡單概括就八個字:“領導、指導、協調、監督。”在他看來,政法委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位子沒有擺對,就容易適得其反。
據介紹,黨委政法委開協調會,一般會召集公檢法等案件承辦單位參加。會議主要有兩種形式,對于非常重大敏感的疑難案件,全體委員參加,都是各部門一把手,也稱作“大三長”會議;另一種是“小三長”會議,對于一些案件不夠重大,但又需要政法委協調的,由各部門分管副職參加,比如,公安局分管刑偵的副局長,檢察院分管公訴的副檢察長,法院分管刑庭的副院長。
學界這些年對政法委制度的批評聲此起彼伏。主要有兩種聲音。比較溫和的主張改良政法委員會制度。中國法學會郭道暉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認為,政法委員會制度在實踐中會導致地方黨委的非法干預問題。
“政法委實際上是公、檢、法、司的聯合體。往往變成司法機關‘聯合辦公,多屬互相‘配合,而很少或取消了‘互相制約。或者政法委員會的委員制變成政法委書記首長負責制,他個人說了算。重要案件都須給他審批,成了判案的習慣程序。”
另一種主張取消政法委員會協調辦案制度。中國公安大學崔敏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就主張廢止政法委員會協調辦案的制度,取消政法委員會。“過去多年形成的由各級黨委政法委牽頭,公檢法各部門‘聯合辦公、協調定案的制度,缺乏法律依據,由于法院和檢察院都必須貫徹政法委的‘協調意見,實際上他們不可能獨立行使職權”。
庭審定罪
趙作海依舊羈押在柘城縣看守所。
沒有增加新的證據。重大疑點也沒有得到解決。政法委協調會后的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檢察院受理趙作海案。
此時,主訴檢察官汪繼華已離開檢察院,案件由助理檢察員鄭磊承辦。
至今,鄭磊仍記得當時擺在他面前的卷宗上,有上級部門負責人對此案“快審快判”的批示,“當時要求我們必須在20天內起訴到法院”。
“商丘市委政法委把結論都定好了,檢察院、法院只不過是個形式,我們只有服從”。鄭磊1992年畢業于武漢中南政法大學法律系。1998年,經過公務員考試,進入商丘市檢察院。
這已不是鄭磊經手的第一個上級“定調”的案子了。在短暫的檢察系統工作經歷中,鄭磊此前曾接手多次“定調”的案子。
“比如一個貪污受賄案,證據不充分,如果一審在中院,被告人申訴到省高院,還有可能改判,協調會后,就安排一審到基層法院,申訴到中院維持原判結案了。”
雖然有上級的“定調”,審查完卷宗后,鄭磊還是給主管領導匯報了自己的意見,“能夠起訴的證據,和不能起訴的證據,都有匯報。”
能夠起訴的證據共五點:一、趙作海的口供;二、殺人的動機,二趙不但有私人恩怨,還存在債務糾紛;三、被害人趙振晌在一年內沒有出現;四、井里裹尸用的麻袋,經趙作海的媳婦和兒子辨認,是趙作海家的,趙作海對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釋;五、趙作海申訴說警方刑訊逼供,當時認為是狡辯。
但案件疑點也暴露得同樣清晰:尸源問題;壓在尸體上的三個五六百斤的石磙,趙作海不可能一人弄到井里;難以排除逼供、誘供的行為;肢解尸體的刀具沒有找到。
領導當時是這樣答復鄭磊的:案件符合兩個“基本”的原則(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充分”),夠起訴條件。為了解決超期羈押問題,按市委政法委的要求,盡快起訴。
2002年11月11日,鄭磊在規定時限內,作為公訴人,指控趙作海犯故意殺人罪,向商丘市中院提起了公訴。
庭審現場安排在柘城縣。
庭審沒有公開,但當地人長久以來認為趙作海是兇手的想法,依舊牢固。這些年被認為和二趙不清不楚的那個女人,撫養了趙作海前妻遺棄的兩個孩子。他們一家,在趙樓村一直抬不起頭。村民們在他們家門口潑屎潑尿,沒事還數落幾句。
庭審現場波瀾不驚。雖然致罪證據依舊不足,但面對這個疑罪從有的系統,趙作海始終拿不出自己不是兇手的更有力證據。
趙作海的辯護人是當時尚未拿到律師執業證的實習律師胡泓強。“趙作海的辯護律師是法院指定的,當時還沒有法律援助中心。在庭審現場,法官說,這是某某律所的律師。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如果不看新聞,也不知道他原來是個實習律師。”鄭磊說。
庭審持續了僅僅半個小時。鄭磊匆匆念完起訴詞。趙作海依舊在法庭上喊冤,訴說著自己的冤屈和刑訊逼供的事實。實習律師胡泓強為趙作海做了無罪辯護,但辯護也沒有得到法官的采信。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人趙作海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趙作海原本有申訴的機會,但他最終放棄了。錯案曝光后,趙作海說,之前在社會上生活得并不好,入獄后感覺“生活穩定”,就不想再折騰,安心服刑,以求早日出去。
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院復核認為,商丘市中院一審判決,事實成立,證據充分。
11年后, 2010年4月30日,“亡”者歸來。老無所依、向往低保的趙振晌,突然回到了村莊。
他并沒有死,他只不過是躲了起來。他回村后的解釋是,當晚和趙作海沖突后,擔心報復,連夜騎自行車離家出走,隨身帶了400塊錢,還有被子和身份證,以撿廢品為生。
來自警方和法院的錯案追究機制已然啟動,涉事民警和法官初步處理結果已出。
5月9日,趙作海被無罪釋放。5月13日,趙作海領到國家賠償和生活困難補助65萬元。當地政府為趙作海援建的房子即將封頂。
與他被致罪的過程相比,這個認錯的過程顯得簡單、迅速。
目前,商丘中院參與一審的三名法官和河南高院復核的一名法官均已被停職,等待調查。
事后,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受訪時,談到錯案發生的原因,趙立勇說:“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起案件有很多疑點,卻出現了這樣的判決,三家辦案機關都是有責任的,是沒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也沒有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
而在趙作海案余熱未消之際,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要求各級政法機關嚴格執行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依法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確保辦理的每一起案件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兩個規定首次明確了包括“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等6種不能用于死刑定案的證據。這被視作中國刑事證據制度的巨大創新和突破。
眼下,河南全省法院正在開展為期一個月的趙作海案教訓大討論活動。
在網絡上,關于趙作海案的討論還在持續,有調查問,你認為相關責任人會受到應得的追究嗎?
81%的回復說,不會。★
(實習生周瀟梟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