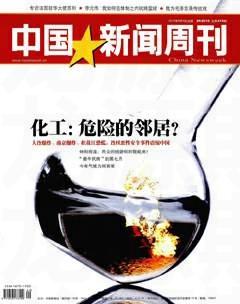財富分配鴻溝深陷
周政華


大雨傾盆而下。21歲的王永松在取款機里,領到了上個月的工資,1520元。正當他把錢揣進荷包時,一輛寶馬車從路邊呼嘯而過,泥水濺濕了他一身。
沖著遠處早已模糊的寶馬車罵了一句后,這個瘦削的青年一貓腰,便飛身跑向馬路對過的宿舍。雨霧里,一切都迅速地模糊掉。亞熱帶的廣東,所有的事情,都和這天氣一樣變化無常。
還沒進屋,褲兜里的手機響了起來。一接通,原來是廣州的堂哥打過來的:下個禮拜天堂哥結婚,請他過去喝喜酒。堂哥在一家證券公司上班,年薪幾十萬,電話里說說笑笑。
對堂哥,王永松只有羨慕。作為廣東南海一家汽車零部件公司的員工,從去年5月進入工廠的第一天起,學生時代的無憂無慮就一去不復返了,“錢掙得太少”成了王永松的一塊心病。
起初,他還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他站在流水線旁辛辛苦苦干活,卻總趕不上物價上漲的幅度快。在沒有原因的被剝奪感驅使下,這個初出校門的年輕人,參加了一場全國矚目的要求加薪的停工運動。
不久,王永松在另外一家民營汽車零部件廠找到了一份新差事,工資多了三百塊錢。漸漸地,一種對現實的無力感取代了最初的憤怒。現在,王永松沒有選擇地成為流水線上一顆有血有肉的螺絲釘。王永松并不知道,一個叫做收入分配改革的計劃,在2010年將要出臺,并旨在促使像他一樣的人收入會出現變化。
那些無法跨越的鴻溝
王永松是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家在廣東湛江郊區,工廠的同事,快餐店里的老板娘,都喊他靚仔。這個18歲的打工仔最討厭別人喊他農民工。
在王永松的印象里,農民工是個帶有污蔑意味的詞兒。出生于廣東湛江農村的王永松,對于城鄉差別的最初感受,源于小時候的一次走親戚。
1999年,10歲的王永松,第一次被父親帶到廣州大伯家走親戚。在大伯家,王永松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電視里見到的電腦,大他6歲的堂哥幫他申請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個QQ號。
十年前的一趟廣州之行,王永松感受到了當公務員的大伯和在老家種田的父親之間巨大差別。城鄉差別的印象深深地烙在了王永松的心頭。
那一年,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全國農村居民收入為城鎮居民的收入的兩倍多。從那時起,王永松開始明白父親為何從小教育他“好好讀書,以后上大學進城坐辦公室”。
“這些年家里三個兄弟姐妹讀書,都是靠父親在廣州打工養著。”王永松說,家中的幾畝水稻只夠得上全家一年的口糧,種田早已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眼下,家里的三個姐姐分別在珠海和中山打工,而50多歲的父親,仍然在廣州一間小餐館的后廚里掂勺,肩膀上搭著的一方毛巾,終日為汗水所浸濕。
城鄉天壤之別,早在王永松父親那一代人中就已經存在。王的父親出生在上世紀50年代,當時正逢三年自然災害,用奶奶的話說,父親的那條命是撿來的。父親讀完初中不久就進入大隊的生產隊,成了一名掙工分的壯勞力。
1949年,當時中國為了發展工業,設立了城鄉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村大量獲取工業發展所需的廉價原材料。僅1960年到1978年這十九年間,據不完全統計,通過統購統銷,農村為城市工業奉獻了3400億元人民幣的價差。
而城鄉差距在改革開放后出現了短暫的縮小之后,到了王永松這一代,又進一步擴大了。
到了2009年,農民三年的收入才趕得上城鎮居民一年的收入。因水稻賣不出好價,家里的水田面積從十多年前的20多畝,到現在只剩下不到5畝,剩下的都撂荒了。在王永松的父親眼里,過去十幾年化肥種子價格都翻了好幾番,可是政府的晚稻收購價還不到一塊錢。
出于糧食安全的考慮,中國的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至今仍處于政府嚴格調控之下。
眼下,王永松一家從土地獲得的收益,主要還是依靠種植業。按照現行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規定,中國農村的絕大部分土地不可作為銀行貸款抵押。農村集體土地只有通過國家征收轉化為國有土地后,才能上市交易,變為資本。不過,中國人民銀行今年7月28日,發布了《關于全面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的指導意見》,嘗試通過小范圍的試點,推動農地抵押。
對于這一點,王永松一家深有體會。在他的家鄉湛江,2009年政府新建東海島新區占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時,每公頃耕地補償45萬元,相當于45元/平方米,而目前湛江的商品住宅均價早已經突破6000元/平方米。國家稅務局統計顯示,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總金額達1.5萬億元,如果把這些錢發放到8億農民手上,每個人可以分得近2000元。
當除種植業以外的土地增值渠道被切斷后,打工就成了農民為數不多的謀生出路之一。
2009年,王永松也走上父親的打工路。由于英語一直跟不上,嚴重偏科的王永松念完初中后,就上了湛江當地的一所職業學校。17歲那年,進入廣東海南的一家汽車零部件廠,成了流水線上的小工。
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夠比湛江多出500元。這種地區間的差距,也導致了大批像王永松一樣的粵西農民,不自覺地流向了珠三角。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政府調整了此前的地區均衡發展思路,轉而優先支持東部沿海發展,在“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路下,政策、資金、人力等各種資源向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唐地區傾斜,這些地區依靠加工出口貿易保持了高速增長,并成為中國的財富聚集地。
南海,也搭上了國家政策的末班車。僅南海區獅山鎮一地,截至去年末,吸引了兩千多家工廠,年產值超過兩千億,相當于中西部數個地級市的經濟總量之和。
地區收入差距開始出現。到了2009年,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在城鎮居民年人均收入方面,最高的上海市已經比最低的青海省高出兩倍多。
這種地區收入差別,也體現在王永松的家鄉湛江和省會廣州之間。
盡管廣東是中國工業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但是珠三角與粵西之間仍然存在巨大落差。2009年,湛江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為13600元,僅相當廣州的60%左右。
城鄉和地區差別擴大的同時,行業收入差距的擴大更為明顯。
2010年,王永松從湛江的一所職高畢業后,和村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學畢業后,去了廣州一家證券公司上班。
在珠三角,王永松所從事的制造業工人的年平均工資不超過3萬元,而王永松堂哥參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證券公司僅年終獎就發了9萬多元,總收入是王永松的6倍多。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各行業間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09年,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以不到8%職工的人數,占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于社會平均工資10倍左右。
消失的基尼系數
不同人群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最終帶來的是社會嚴重的貧富不均。
“我是一個徹底的無產者。”工作才一年多的王永松拍拍口袋說,我一分錢存款也沒有。
王永松只是中國眾多“無產者”的一分子。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根據其2004年進行的一項涉及幾個省市的銀行儲蓄存款分布調查數據推算,前20%的儲戶占有銀行存款的86%,而其余80%的儲戶只占有剩余的14%。
13億中國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早在二十年前,與王永松相隔千里、遠在北京的李實,也產生過類似的疑問。
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彈為什么還不如賣茶葉蛋賺錢”的李實,參加了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課題組,并開始了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民間收入調查。
這也是中國首次全國性的民間調查。經過五年斷斷續續的調查,1993年,課題組公布了1988年中國農村基尼系數是0.325,城市是0.233。這一數據,遠遠超乎當時學界和政府的預料。但據李實回憶,當時社會對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見并不強烈。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重要分析指標,取值在0與1之間,如果超過0.4,便被視為收入差距過大。國際上一般把0.4設定為收入差距的警戒線,認為如超過這一水平上,極易引發社會動蕩。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居民間收入分配的差距一直沒有過大。收入分配的急劇惡化,首先來自于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由于中國政府決定對數量龐大、效率低下的國企實施“減員增效”,近千萬國企職工下崗,低收入階層人數突然激增。而在之前的開放中,迅速致富的個體戶的出現,以及伴隨著國企改革中大批中小國企被出售而涌現出來的收入激增的民營企業家,使得這一貧富對比一時間凸現了出來。
而后,地區發展的不均衡,以及在城市化過程中由于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城市政府拿走等因素,使得國民間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到200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當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5,接近收入懸殊的水平。
對此,時任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對外表示,我國的基尼系數雖然超過0.45的國際警戒線,并不意味著我國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因為我國二元城鄉體制導致基尼系數偏大。如果單獨核算,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都分別低于0.4。
此后,國家統計局再也沒有公布過基尼系數,這個用來衡量收入差距的尺子也從各種政府文件中消失。
但學者的研究卻從未中斷。1988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李實一直關注收入分配和貧困研究。現任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實估算,200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可能超過0.5。李實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收入差距仍在持續擴大中。
誰拿走了大頭?
差距這么大,錢都到哪里去了?
這是王永松一直想不明白的問題。王所在的廣東南海區獅山鎮境內的2600多家企業,2009年生產了總價超過千億元的產品,為當地上繳了近30億元的稅收,但是像王永松這樣的打工仔,一年的收入通常不到3萬元。
中華全國總工會公布的數據表明,從1993年到2007年,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了20%,但同期,資本報酬比重卻上升了20%。與資本回報急速上升相比,政府的財政收入也持續走高。
楊重光的研究,或許能夠解釋王永松的疑惑。
“收入分配差距為什么越來越大?看看這三組數據,答案就在里面。” 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楊重光指著自己手抄的今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數據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大批財富向政府集中是導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王永松的記憶中,政府收入似乎與自己關系并不大。但現實中,政府稅收和民眾收入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關系。
國家統計局新近發布的一組數據引起了長楊重光的注意:2010年上半年,財政收入同比增長27.6%(預計全年將超過8萬億元),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1.1%,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同比增長10.2%。
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的研究發現, 1951年時,我國民間的消費占當年GDP的68%,政府的消費僅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間的消費降到了GDP的37.5%,政府的消費則上升到了GDP的28%。據陳志武的推算,在中國,超過76%的資產屬于政府。
政府收入膨脹不僅表現為稅收和種種預算外收入的激增,更為隱匿的部分還體現在政府官員灰色收入中。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政府官員的灰色收入總額高達5.4萬億元,比2009年中央財政總收入還要多。
王小魯認為,龐大的灰色收入來源主要是圍繞權力對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的分配而產生的腐敗、尋租、侵占公共資金和他人收入、聚斂財富等行為,以及壟斷性收入的不適當分配。
這種權錢結合的情形在房地產領域表現最為突出。國家統計局調查資料表明,2007年,中國居民戶均60%的財產來自房屋。作為中國居民財產的主要構成部分,房地產也成為國內居民投資理財的首選。
2008年位于上海中心區徐家匯名為帝景苑的樓盤售罄數年后,由股東糾紛引發的舉報顯示,約400戶業主中,50余戶曾獲得一成以上的折扣,其中22名買家折扣高達三至五成。折扣買家多出自房地、規劃、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門。
近年來政府查處的官員腐敗案顯示,涉案官員大都是炒房高手:上海浦東新區原副區長康慧軍案發時,這位“炒房局長”擁有27套住宅,市值超過6000萬;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原主任戴國森被“雙規”時,辦案人員從其家中搜查出十多本房產證。
王小魯認為,權力在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的情況下,會自發趨向于追逐經濟利益,導致對社會的侵占和掠奪,并引發日益嚴重的分配不公和社會沖突。
“房地產是觀察中國收入分配一個窗口。”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楊重光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這位64歲的老人說,收入分配問題,從根本上說乃是一個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