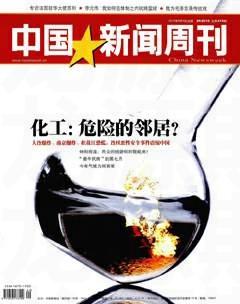圍魏救趙,解北京人口之困
梁小民
最新公布的數據,北京常住人口已經達到1972萬。北京房價之高、交通之堵、環境之差,已使人們難以忍受。你能想象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達到2500萬時,北京會是什么樣子嗎?控制北京的人口規模已成為上下的共識。
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時,政府早已考慮到要控制北京人口規模這個問題。一直以來,北京實施著嚴格的戶籍制度,對沒有戶口的“盲流”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清理。但為什么越控制,人口規模擴大越快呢?
人們愿意進入北京,想成為北京人,是因為北京的吸引力太大了。這種北京的吸引力來自北京的發展思路。
解放后,北京的發展圍繞一明一暗兩個思路。明的思路是北京是首都,所以要把北京建成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就有了政府對北京的大規模投資。民國時期,北京不是首都,成不了政治中心,經濟上遠遠不如天津、上海,文化上有幾所好大學,擁有一批文化人,但當時北京也并非唯一的文化中心,起碼上海的“海派”是可以和北京的“京派”抗衡的。解放后,北京什么都要當中心,各行各業發展迅速,自然需要人,那時許多人不愿意來北京,是“被移民”到北京的。
暗的思路是,北京人是“天子腳下”的居民,應該享有特權。說得好聽點,讓北京居民過得更好一點也有利于維護、提升北京的國際形象。困難時期和文革時期北京的物質供應就比其他地方豐富得多。許多外地生產的東西,當地買不到,只有北京才有的供應,那時,從北京到外地的人,都是大包小包地帶東西,人們出差到北京,都是順帶手采購許多東西帶回去,有幾次把火車行李架都壓塌了。據說,有工作人員請示周恩來總理,要不要采取嚴格的限制措施,總理說,讓他們帶點吧,外地太困難。
在這兩種思路的指導下,北京與外地的差距越來越大。因此盡管有嚴格的戶籍制度,但北京的人口還是越來越多。改革開放后,沒有戶口也可以在北京生活了,而北京的發展思路并沒有變。因此,北京人口規模超速膨脹,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過去控制北京人口規模是用戶籍制度加清理沒有戶口的“盲流”,現在市場經濟時代,公民有流動的權利,過去控制人口的方法都作用有限或不能使用了,因此,控制北京人口規模必須改變思路。新的思路應該是“圍魏救趙”,即加速其他地方的發展,減弱北京的吸引力。“圍魏救趙”不是壓制北京的發展,而是在發展其他地方的同時,調整北京的發展思路。
首先,北京的定位不能再是政治、經濟、文化樣樣中心,要突出北京的特點。北京是首都,政治中心是改變不了的,盡管也有“遷都”的建議,從近期來看,實現的可能性并不大。北京已形成的文化優勢也難以改變,總不能把北大、清華、中科院、社科院遷往外地吧?但是要實現文化上的多中心,讓更多的城市成為文化中心,尤其是發揮本地的特色文化。經濟中心,北京還是不要當的好。北京不必追求GDP,更不用什么產業都發展。不僅不用發展鋼鐵、汽車等傳統行業,甚至連高科技行業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發展,經濟上形成多中心,也才有利于全國的平衡發展。
其次,就北京而言,不能僅僅發展四環之內,還要向郊縣地區,甚至河北的一些地方發展,圍繞北京建立一小時經濟圈。什么都集中在四環之內是不正常的。應該用經濟手段吸引一些企業事業單位遷到郊區。這就需要發展市中心與郊區的交通,并加大郊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讓在郊區工作與居住的人,感到與市區一樣甚至比市區還舒服。
發展郊區,我認為應該是以后北京發展的重點。“衛星城”的計劃過去也有,但為什么至今仍然不成功?我想,這還在于講得多,但采取的有效措施太少,投資太少。
最后,在我看來,北京的經濟應該以服務業為主,一切以北京的需要為中心,而不能以加快北京的經濟發展為中心。北京有這么多人,僅僅是為他們提供服務,就足以支撐北京的經濟。北京有天然的旅游資源,這些資源無法遷走,發展旅游業也可以成為北京的支柱。我們受“重物質生產,輕勞務”的影響太深了,發達國家勞務在GDP中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世界平均水平勞務也在GDP中占到40%以上,而我國勞務在GDP中僅占三分之一,發展勞務先從北京這樣的城市開始。
控制北京的人口規模,不能就人口講人口,要從改變北京整體發展戰略的思路入手,關鍵則在于打破北京處處要當中心的傳統思維模式。★
(作者為清華大學EMBA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