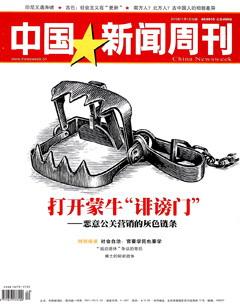一個透明的黃宗江
徐慶全

10月18日,自封為“藝人”的著名編劇、演員、影劇評論家黃宗江在北京301醫院去世,享年89歲。歲月無常,伴隨著黃宗江的仙逝,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登上藝壇的前輩們已凋零無幾,那一代宗師也走進“告別的年代”,行將謝幕!
在黃家吊唁靈堂中,掛著這樣一副挽聯:“真是雜家,作協劇協影協,無協不與;堪稱奇跡,文人藝人軍人,此人大才。”上聯涵蓋黃宗江一生之涉獵,自然精當,但下聯以其“文人藝人軍人”之經歷證其“奇跡”與“大才”,多少有些牽強——且不說從30年代走來的與黃宗江有相似經歷的人就有不少,而考察黃宗江一生行狀就會發現,他的經歷有時候往往成為阻礙其成為“大才”或者說更“大才”的因素。
筆者這樣說,并不是不認同“此人大才”的說法。他出身書香門第,卻帶領一眾弟妹跨入戲劇行當,成為“賣藝人家”;他10歲就發表獨幕劇,之后創作《柳堡的故事》《海魂》等影響了幾代人的電影劇本——“此人大才”也并非浪得虛名。筆者想說的是,黃宗江一生率性而為,與嚴肅的人生目標無緣,這倒使他多少與時代有所游離,也少了時代風云的羈絆,有了快意的一生。
“父親一生從不追名逐利,對于生活追求的就是樸實。”女兒的總結,揭示了其快樂一生的實質。
為情兩次改變人生軌跡
黃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父親是留日學電機的洋翰林后來在北京電話局做工程師。在黃宗江記憶中,父母從小就帶著他看戲,這對他后來的人生道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黃宗江10歲時就寫了一個名叫《人之心》的寓言劇,在當時的《世界日報》上刊載。1935年黃宗江考入有著悠久演劇傳統的南開中學讀高中,開始在校內登臺演出,展示出了才華。1938年,黃宗江考入燕京大學外文系讀書。相比學業來說,演戲對他似乎更重要。
黃宗江說他的初戀,就發生在此時。這其實是一段單相思的暗戀,暗戀的對象是曾與他一起就讀南開中學并一起考上燕京大學的同學。在南開時因為男女分校而無緣“零距離”,到燕京后卻有緣一起排演話劇《雷雨》:他演周沖,她演四鳳。但現實中,“四鳳”卻舍“周沖”而戀“周萍”。17歲的黃宗江竟然服藥自殺,幸而未遂。稍后,黃宗江愛上了一個在他眼中模樣酷似主演《插曲》的英格麗·褒曼的女同學,但依然是單戀——那女孩子卻因為失戀要為別人自殺。此情不可待,惘然成彷徨。與傷心相比,學業算什么?黃宗江竟然一走了之!而以他的聰穎早慧,若是繼續學業,未來成“大才”豈不是有了更高的起點?
1940年冬,19歲的黃宗江前往上海,考進上海劇藝社,走入了真正的戲劇團,并很快站穩了腳跟。不久他又加盟了黃佐臨組建的上海職業劇團。1942年,他輾轉到了重慶,參加了夏衍領導的中國藝術劇社,與夏衍、于伶、鄭君里、金山、藍馬、張瑞芳等名家同臺演出,舞臺生涯的序幕由此拉開。由于他出色的表演,很快就得到了觀眾與同行的認可,擁有了“三大小角色之一”的雅號,并與藍馬、謝添、沈揚一起被稱為“四大名丑”。
就在黃宗江聲譽日隆之際,他又一次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如同第一次改變一樣,這次依然是“情”之所至。戀愛再次無果,又一選擇離開。1943年冬天,22歲的黃宗江參加中國國民黨赴美參戰海軍,當了一名水兵。從此,他為自己的演員生涯畫上了句號。
黃宗江有名言在耳:“演戲比讀書重要,戀愛比演戲重要。”至于在常人看來的人生目標:宏大理想,事業有成等等,在他看來全不重要——情之所至,才是人活下去的理由。這樣的率性,如此的快意,殆有幾人堪比?
一次讓后半生快樂的選擇
1945年黃宗江回國時,日本已經投降,抗日戰爭已經結束。1946年秋天,黃宗江又一次走入燕京大學校園,準備完成丟失的學業。可是,一樁在他看來不幸福的婚姻,使他再一次選擇出走上海,最終也未能取得燕京大學的畢業證書。
既然學業無成,總要干點什么。黃宗江接續了10歲時的理想,開始劇本寫作。1948年,他創作的劇本《大團圓》在上海獲得公演,大獲成功。這是黃宗江第一個搬上舞臺和銀幕的作品,也正是這部作品決定了黃宗江的人生選擇:他從演戲轉為職業寫作。
《大團圓》演出后不久,人民解放軍駐扎在上海的“霓虹燈下”。盡管一直與現實有著一定的間隔,既未加入過國民黨——哪怕在國民黨海軍服役時也未曾有過這樣的念頭,也未曾加入過共產黨,但黃宗江對國共兩黨的政治信念,有著清醒的認識:與國民黨的潰敗相比,欣欣向榮的中共,無疑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利益。年近“而立”的黃宗江,作出了選擇:加入中共領導的軍隊,做一名文藝兵。而《大團圓》的成功,他的才華,秣馬厲兵的軍人更加需要文藝人才的現實,使他如愿以償地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
這一選擇,他對訪談者給出的理由是:那時,軍人特別受到尊重。言語之間,并無“為什么什么而奮斗”之類的宏大敘述。淡淡的,淺淺的,這才是黃宗江!
不過,回溯黃宗江的一生,不得不承認,這是他最明智的選擇。以黃宗江的履歷來說,他若不是在人民解放軍的隊伍里,而是在地方上的文藝團體或者研究機構供職,“文革”前歷次的政治運動必然波及到他,甚至會改變他的命運,他就不會有很平安、很自我的生活。
黃宗江是國統區走來的知識分子,1951年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運動的對象即是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他當然在此之列。但因為他在解放軍隊伍里,他既不用“脫褲子”檢討,也不用“洗澡”來脫胎換骨,而是在精心醞釀日后成名的《柳堡的故事》的劇本。
1943年,黃宗江因情脫離演藝界,加入了國民黨海軍。兩年多國民黨軍人的履歷,若在地方,他首先要與肇始于1953年底的“審查干部”遭遇。此次審干主要由組織部門參照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檔案,對政治歷史不清、或曾與國民黨有過瓜葛的干部逐一排隊審核。在審干開展一年半后,肅反運動爆發。“肅反”成為人人過關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不論是解放區還是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以黃宗江在國民黨軍隊服役的經歷,哪怕他什么也沒有干過,能夠過關,但至少也要一遍一遍地寫出這段歷史的經過,記錄在案。軍人的身份,讓黃宗江再一次幸免。
如果黃宗江在地方,讓黃宗江最難以過關的是他與“二流堂”的淵源。
抗戰時期,從上海遷徙來渝的唐瑜,因家境富裕,生活優越。他身為文化界人,常常來接濟文化界的朋友。后來,他建造了一幢兩層樓的洋房,成為當時重慶文化界名流聚會的場所。像吳祖光、盛家倫、金山、張瑞芳、薩空了、夏衍、喬冠華、黃苗子、郁風、丁聰、馮亦代、徐遲、龔澎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常常流連于此。后來這里被郭沫若戲稱為“二流堂”。至此,“二流堂”大名,迅速傳播開來。“二流堂”在黃宗江記憶里,是一段嬉笑怒罵,無拘無束的歲月。他不但側身其間,而且還介紹著名戲劇評論家、美學家沈祖安成為“堂友”;妹妹黃宗英也在這里得到照顧。
在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中,“二流堂”的堂友大多遭受審查,或淪為所謂“胡風革命集團”的“小分子”,或淪為右派分子,并因此中斷了知識分子生涯,直到“文革”后才獲得平反。而身為“二流堂”“堂友”的黃宗江,因在軍隊,又一次置身事外。即使在1967年,“二流堂”作為“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一大公案,曾使許多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屢被批斗,慘遭迫害,黃宗江也未被提及。當然,在全民族劫難的“文革”中,黃宗江也未曾幸免,他曾被發配到甘肅去。
至情入戲的《柳堡的故事》
作為劇作家,黃宗江創作了《柳堡的故事》《海魂》《農奴》等作品,但最讓華人記住的是《柳堡的故事》,那首傳唱至今的“九九艷陽天”,就出自這部故事片。從中國電影史的層面來看,1949年至“文革”前,是一個個人情感隱退、革命化張揚的年代,且不說表現一般人生活的影片鮮有愛情,現役軍人的愛情更成為禁忌。而黃宗江和石言創作的《柳堡的故事》則成為異數。
電影來源于一個真實的故事:解放戰爭期間,軍人在姑娘心目中地位特別高,找軍人做伴侶是許多姑娘的愿望。駐扎在江南一個村莊的一名戰士被房東姑娘相中,他倆暗暗地相愛。不料,此事被發現,連長狠狠地批評了這個戰士,并不許他再和姑娘有任何來往。不久,部隊開往前線,戰士在一次戰斗中犧牲了。戰斗結束后,部隊又返回原來村莊。姑娘得知心愛的戀人犧牲了,她覺得戰士是為她死的,心里充滿了愧疚,便在一棵樹上上吊自殺了。那位連長覺得這對情人的死與自己當初的批評有關,非常內疚,并用一輩子不結婚來懲罰自己。
這個凄美的愛情故事深深地打動了軍旅作家石言,他以此為原型寫了一篇小說。他為故事增添一個圓滿的結局:戰士沒有死,在勝利后又回到小村,與二妹子在當年約會的地方重逢,有情人終成眷屬。
《柳堡的故事》最初發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南京軍管會文藝處的黃宗江讀到后,認為是一個拍電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商量將它改成劇本。
黃宗江鐘情于這個劇本,自然有他的考慮:一、故事中“二妹子”對軍人的尊敬,切合于他參軍時的心情;二、為情所至,是他的強項。他似乎對于“革命化”張揚的現實考慮并不多。
因為與“革命化”張揚的現實有距離,黃宗江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多次被人非議。有人說,在戰斗生活中,軍人與地方姑娘之間談戀愛,違反軍隊紀律,應當予以批評。甚至有人提出,軍事影片中不應當出現談戀愛的鏡頭。種種意見,使黃宗江和石言的劇本創作陷入困境。
這場爭論最終擺到了當時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周揚面前。出乎意料的是,周揚對這個故事很欣賞。他也指出了故事立意的不足之處,即單純描寫了軍人與地方姑娘的愛情。周揚認為,小說經過改編應該是可以搬上銀幕的。他在批示中表示:軍隊作品并非不能表現愛情,而在于如何表現,“戲中最最關鍵的一點是部隊的紀律,特別是軍民關系方面的紀律問題,如果這戀愛既發生在部隊和駐地居民之間,同時又是在緊張的殘酷的戰斗環境中,像戀愛這類屬于個人情感個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極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現這個題材的時候,不要只表現一種純潔的、真正的、高尚的愛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適當位置上。如果這個位置沒有擺上,那就要成為不正確的,不真實的了。”
周揚的支持,使黃宗江和石言的劇本創作進展順利。1957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投拍。作為編劇,黃宗江對于劇中“二妹子”的角色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因此,他向導演王蘋推薦華東軍區解放軍藝術劇院話劇演員陶玉玲扮演“二妹子”。電影1958年完成并公映。
那個年代,描寫紅色革命戰爭題材的影片是銀幕上的寵兒。《柳堡的故事》大膽地在戰爭題材影片中進行愛情戲的嘗試,更加引人注目。片中插曲《九九艷陽天》至今仍廣為傳唱,黃宗江的名字也隨著歌聲不脛而走。
晚年的黃宗江,曾寫過《柳堡二妹子的親娘——多情的指導員胡實言》一文,談及影片的創作過程,說“我是這個劇本的干娘,或者奶娘,人家親娘是胡實言(即石言)”。不掠功,不居美。
黃宗江是透明的,他一生實踐著自己“我不能灰色地活著,不能黑色地活著,我得亮色地活著”的人生信條,因而一生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