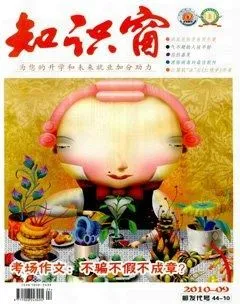童稚邀蟬誰植柳
馬 浩
蟬的成蟲,是一種很美的野味,我們那兒稱之為姐兒龜。這名兒大抵出于民間,曰龜,生動、傳神,至于“姐兒”二字,我始終有所懷疑,似乎無解。
姐兒龜褪去外衣,猶如毛毛蟲化蛹成蝶,美其名曰:蟬,或曰:知了。大約知了因其聲而得名,可感易記,婦孺皆知,名副其實地聲名遠播。知了在我們那兒,那個“了”字讀la,也難怪,了字是多音字嘛!叫la時音輕且短,重音在“知”,聽起來,有種急促之感,很有地方特色,有味。
每至盛夏,暴雨之后,干坼的大地變得松軟了起來,正是姐兒龜爬出窟的好時機,而此時,正有人惦記著它呢,鄉村雨天無農事,男女老幼,家前院后,皆屈膝彎腰,探頭探腦,尋覓著姐兒龜作肴呢。
小的時候,以此為樂,口福倒在其次。右手握把鐵鏟,左手提著罐頭瓶,伙同一群屁孩向野外樹林進發,常常在大樹的根部,用鐵鏟刨去地皮,不時會給你驚喜。除去淺淺的一層土殼,豁然驚現一眼小孔,那興奮勁如同魚兒咬鉤。用手指輕摳小孔,豁然一洞,用細樹枝探進洞中,姐兒龜便會援枝而上,自投羅網。真可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姐兒龜更多的是借著夜色出窟,援樹而上,褪衣成蟬,我們也常趁著夜幕,悄悄地潛入樹林,一個手電筒足矣,對著樹干一照,一晚上下來,收獲頗豐。
那些逃脫手掌的姐兒龜,在高樹之上華麗轉身,悠然地騎在樹枝上,隱沒在綠葉間,打量著這個世界,或許是站得高、看得遠,似有所感悟,高聲叫著“知了,知了”,尤其在暴烈的驕陽下,它叫得更起勁“知了、知了”……它到底知道些什么呢?不可思議。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掩映著村莊的綠樹,是知了的家園,知了繁衍生息,都離不開樹木。偶然,我發現院中柳樹的許多枝條無故干枯了,灰灰褐褐地點綴在濃綠的樹冠上,很扎眼。我便問父親,柳樹上,怎么會有這么多枯枝?父親漫不經心地回答:知了在那兒產了卵。
自然界真的很神奇,知了把卵產在樹枝里,樹枝枯死之后,風落于地,蟬便完成一個生命的輪回。父親不經意的一語,我頓開茅塞,“姐兒龜”應作“截柳龜”啊,如此一來,便從無解變成可解了。如此發現,讓我興奮不已。日后,我又刻意地作了一番觀察,椿樹、梧桐上斷無蟬影,榆樹、銀杏樹尚未發現,它們似乎對楊樹也特別鐘情,大約楊柳同屬吧。鄉間多植楊柳,有意無意保護了蟬。處處留心皆學問,果真如此。
截柳龜,我兒時的美味,白日逮,夜晚捉。捉來之后,用水沖洗,去除其爪中泥土,洗罷,便可直接上鍋煎,殼焦肉嫩,適時撒上少許細鹽,入口脆嫩鮮香,營養豐富。晚上捉回來,夜已深,唯恐其夜里褪衣變蟬,便把它洗凈,灑上適量的鹽腌漬,否則,影響口味。
而今,家鄉的截柳龜幾乎讓人吃絕了,童稚少年再無蟬趣。不知何時,每年盛夏,總有人花大價錢去收購,截柳龜一旦成了炙手可熱的商品,那就很難說了。更何況,近來鄉人少植柳,不容樂觀的生態環境當不可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