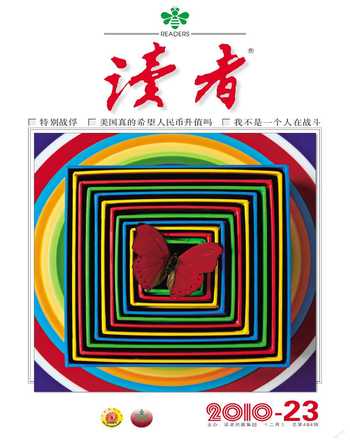初戀時,我不懂愛情
孔慶東
理絲入殘機
高三那年的一個周六,傳達室葛大爺說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張姐。她是我在青年工人讀書小組認識的,讀書小組解散后,再沒見過。張姐說:“這一段時間特別沒意思,想找你聊聊。明天星期天,我八點在兒童公園門口等你,你愛來不來。”
第二天,我帶著一個單詞本去了。張姐說:“你背單詞,我怎么跟你說話?這樣吧,我考你。你如果把這個本子上的單詞都背下來了,就陪我說話。”我說:“行。”一個小時的工夫,我就背下來了。張姐說:“這樣背單詞絕對快,以后每個星期天我都陪你背單詞吧。”我也覺得這種方式頗有效率,頓時產生一種剝削人的思想。
看著張姐的背影,我心想,要是有這么個姐姐,倒挺好。我是長子,無哥無姐,從小受盡大孩子們的欺凌,長大后,感覺難以與父母溝通。意識到這一點的同時,我心中又隱隱萌生了一絲抗拒,因為我一向以為自己堅強剛毅,希望有一個姐姐,仿佛是心中有一塊什么東西融化了,在那種融化的液體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柔弱。
此后,有五六個星期天,我沒有要緊的事,便去“剝削”張姐。次數多了,我有點于心不忍。我說:“高考復習緊張,以后通信聯系吧。”張姐說:“好吧,下次是最后一次。”可到了下次,她又耍賴說:“我說的是下次,并不是這次。你知道什么叫‘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嗎?”我說:“這首《子夜歌》我也讀過,絲就是相思,匹就是匹配,絲線織不成布匹,暗指有情人不能結合。”張姐說:“看你那德行,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我問:“難道我理解的不對嗎?”張姐靜了靜,說:“沒有,姐跟你開玩笑。你快回去復習吧。要是誤了你考北大,你還不恨我一輩子。”我說:“不會的,那張姐我就回去了,以后有事寫信聯系吧。”
張姐揮揮手,轉身就走了。以往都是我先走,她在后面揮手目送的。我也沒多想,轉身也走了。
叫姐無數聲
此后半年多,我們都沒有見面。她給我寫過三封信,談她的工作,她讀的書,她的一些思考。我一向是有信必回,在回信中還隱隱流露出指導和鼓勵的語氣,同時大肆炫耀文筆,也算是作文訓練。她還冒充我的親戚,到傳達室給我送過一回粽子和一回松仁。我與同學們稀里糊涂分著吃掉了。夏去秋來,我收到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臨行前四五天,我去學校閑逛,葛大爺突然遞給我一封張姐的短信,約我在兒童公園見面。我想,也應該跟張姐告個別,就按時去了。
到了約定地點,卻沒看見張姐,過去都是她先在路邊等我。我在四下的樹叢里尋找,忽然眼睛被蒙住。我忙叫:“是張姐吧?”她在后面說:“誰是你張姐?叫姐。”我又連叫三聲,她才松開。
回頭一看,張姐站在綠草地上,穿著水紅色連衣裙,乳白色皮涼鞋,頭上束著一條杏黃色發帶。她說:“你的理想實現了,感謝不感謝我?”我說:“應該感謝你,你幫助我復習了許多次。”她說:“不對,你應該感謝我的,不是我幫助你復習,而是我這半年多來不幫助你復習,根本就不跟你見面。說你不懂事兒,你就是不懂事兒。”我說:“照你這意思,凡是不幫助我復習的人,我都得去感謝嗎?”張姐說:“我的意思你怎么還不明白?我要是幫助你復習下去,你肯定考不上北大。”我說:“不至于。你不過是幫助我,看我背得對不對,又不是當我的指導老師。雖然你的學習成績不如我好,但也不必那么自卑。我主要還是靠我自己。”
張姐聽了,默默看了我一會兒,說:“就你這樣的人,也能上北大呀?”我說:“怎么了?我哪里對不起北大?”張姐說:“看來北大里邊傻子瘋子肯定不少。你走了,有什么話囑咐我?”我一聽有點像孫犁的《荷花淀》,就調皮地說:“我走了,你要不斷進步,識字、生產。”張姐聽了,有點奇怪。我又說:“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別人后面。”張姐迷茫地說:“還有什么?”我憋住笑,接著說:“不要叫敵人漢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們拼命。”張姐這下聽明白了,“撲哧”一笑,說:“好啊,你占我便宜,我現在就和你拼命。”說著,一把抓住要跑的我,在我身上一通亂打,一邊打還一邊胳肢我,直到逼著我又叫了無數聲“好姐姐”才罷手。
目光織瀑布
平靜下來之后,我看出張姐的情緒似乎有些低落,很像學校里那些落榜的同學。
我說:“你以后給我寫信吧。”
“我不給你寫信。我直接去看你,不行嗎?”
“行,行。”我有口無心地答應著。
“放心吧,我不會去的。連你們中學我都不進去,更不會到北大給你丟人的。再說,用不了幾天,你就會把我忘得干干凈凈。”
“看你說的,我孔某人從來不忘老朋友,連小學同學都記得清清楚楚。”
“好,那你就記得我這個老朋友吧。你以后幫助我復習,行嗎?”
一提到學習的事,我便如魚得水,滔滔不絕。
在我說話時,張姐一次也沒有打斷我。她靜靜地看著我,直到我發現自己已經說了很長時間,停下來時,她也沒有言語。
我倆相對呆立了一陣。她說:“你說得真好。我就愛聽你這么瞎說。以后可能再也沒機會聽你這么瞎說了。好吧,我祝你學習進步,生活幸福。”
“我也祝你學習進步,生活幸福。”
“嗯,我有一個請求。”張姐說。
“什么請求?”
“咱們要分別了,能不能……你……能不能,擁抱我一下?”張姐忽然有點不像平時的姐姐模樣,低著頭,好像一個小妹妹似的。
擁抱那時在電影上已經很常見了,可那都是談戀愛的人干的事,跟張姐怎么能那樣?再說,怎么擁、怎么抱啊?我看著張姐水紅色的連衣裙,用手撓著后腦勺,故作鎮靜地說:“擁抱?那,那不太合適吧?我從來沒擁抱過,多不好意思啊。不就是告個別嗎?以后又不是見不著了。革命生涯常分手,要不,咱們就握個手吧。”我覺得臉熱熱的。
張姐的臉紅紅的,她低聲說:“我也沒擁抱過,不擁抱就拉倒。我是想……我是以為你想擁抱呢,我是替你說出來的。瞧你那一本正經的德行,那就握手吧。”說著,張姐筆直地伸過手來。
我伸手握住張姐那細長的手,她猛地用力握了我一下,挺有勁兒的。我很想回敬她一下,但心里跳跳的,沒敢。好像給自己壯膽似的,我連忙說了句:“再見。”
張姐盯著我的眼睛,說:“我送給你的東西,就不交給你了,怪沉的。我直接給你寄到北大去,你等著收吧。”
“謝謝你,張姐。”
我轉身離去。在走向電車站的路上,我總想回頭看看,但努力克制住了。我感覺到后背上一直有一片目光織成的瀑布,從我后腦勺往下,淙淙地傾瀉著。
(劉文娟摘自文化藝術出版社《四十五歲風滿樓》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