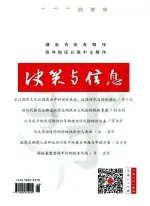“奴”現象的憂思
文/祝福恩 王金榮
目前“奴”與“被奴”兩詞廣為流傳。其實早在2003年“房奴”已作為漢語新詞匯風行一時。現在又有“孩奴”、“車奴”、“蟻奴”、“卡奴”、“節奴”等熱議,口風極盛。這些熱詞是反映人們對社會不滿的極端概括,還是反映改革開放30多年后社會轉型期不可避免的現象?不論怎么說,當今社會的“奴”與“被奴”現實的確從深層說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還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其一,“奴”現象證明我國社會建設滯后。與改革開放30多年相伴的問題,是“經濟建設這條腿長,社會建設這條腿短”。因而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社會建設”,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三位一體”提升為“四位一體”;十七大報告又明確把“社會建設”內涵定位在“五個所”,即“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五個所”實質是解決老百姓的“五個難”,即上學難、就業難、看病難、養老難、住房難。這些難不解決才有“奴”現象。
社會學家陸學藝在其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結構》中指出,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滯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從發展路徑看,發展肯定是經濟在前社會在后,但社會必須跟上,差距在兩三年是合理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大約是兩三年的差距,而我國約是15年,因而產生了諸多“奴”現象。
其二,“奴”現象證明我國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失衡。社會發展的失衡與這些年改革發展的政策偏差有關。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并沒有錯,但有些領域的改革過于追求市場利潤的最大化,忽視了民本、民生的社會責任。如把住房、教育、生育、養老、醫療等公共產品或半公共產品全部交給市場,從而忘卻了公共需求,淡化了人本思想。
其三,“奴”現象證明社會秩序失穩。現實中“被奴”的都是社會最基本的主體,受沖擊最大的是其最基本的權利。如“孩奴”受影響的是生育權,“房奴”受影響的是居住權,“蟻奴”受影響的是勞動權,“學奴”受影響的是教育權等。假如一個社會主體發展所形成的規制,對少數人有利,對大多數人形成制約,甚至被分化為兩極,則必然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阻礙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建設。
如果“奴”現象得不到有效緩解,甚至惡化下去,社會上最普通的主體人群被最基本的物質和精神需求所奴役,就會在某一個時空由“奴”轉為“怒”。1993年~2003年,我國群體性事件的數量由每年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每年約73萬人增加到307萬人,10年上升了5倍。這就足以說明“奴”現象已經影響了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與穩定,影響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應當引起決策層極大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