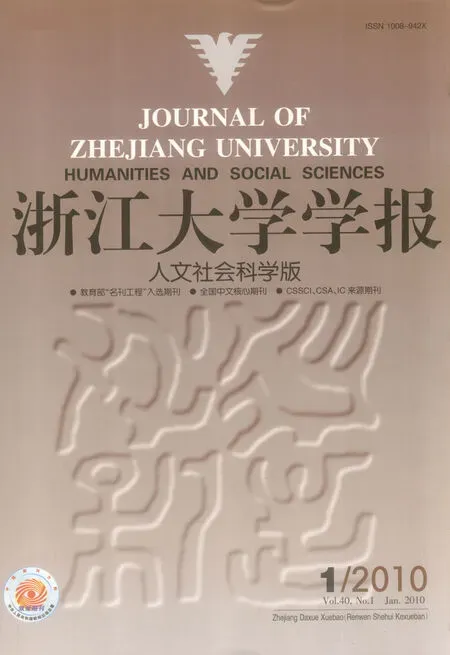縣域經濟發展的激勵結構及其代價——透視浙江縣政擴權的新視角
李金珊 葉 托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浙江杭州310027)
一、引 言
2009年7月,財政部發布的《關于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的意見》明確提出,2012年底前,力爭全國除民族自治地區外全面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很多學者認為,推進省直接管理縣財政改革很可能只是縣政擴權的起步,最終目的是要以全面的省管縣體制替代原來的市管縣體制。
這一政策的推行離不開必要的理論準備、政治經濟條件和實踐探索。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展開了對1983年開始全面推行的市管縣體制的有力批判[12]。任衛東和吳亮將市管縣體制的弊端概括為三大“漏斗效應”,即財政漏斗、權力漏斗和效率漏斗[3]3233。而王吉平更是列舉了市管縣體制的十大“罪狀”[4]32。與市管縣體制呈現出諸多弊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直實施省管縣財政體制與積極推行強縣擴權改革的浙江省培育出了全國最活躍的縣域經濟。進入21世紀后,政治經濟條件的變遷使浙江省的示范效應被大大催化。在城鄉統籌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經濟發展進入了由偏重城市經濟向城市經濟和縣域經濟并重的階段轉換,因此發展縣域經濟具有戰略意義。發展縣域經濟的要求最終轉變為省級政府改革縣政體制的內在激勵,江西、吉林、山東等省陸續仿效浙江省推出了縣政擴權改革試點。
遺憾的是,雖然各地都在仿效浙江省進行縣政擴權,很多和縣政擴權有關的關鍵問題卻尚未真正弄清楚:第一,縣政擴權到底如何推動縣域經濟的發展?擺脫了市政府的束縛,縣政府伸出的到底是“攫取之手”還是“援助之手”?第二,縣政擴權的作用難道僅僅在于成功避免了市管縣體制的各種弊端嗎?實際上,浙江的縣政擴權改革之所以獲得較大的成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設計了一種有效促進縣域之間競爭的激勵機制。第三,縣政擴權糾正了市管縣體制的弊端,難道就不會產生其他新弊端?誠然,過去三十年的浙江經濟高速發展讓人印象深刻,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視,近幾年來浙江經濟的發展遭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難題:低水平模仿和同質化競爭現象嚴重,產業升級困難,企業外遷增加,中心城市的聚集能力和輻射能力不足等。如果對上述問題沒有很好的認識,仿效浙江推行縣政擴權改革無疑只會“得其形,失其神”。
本文試圖回應上述問題,并提出一個一以貫之的理論邏輯來解釋浙江縣政擴權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筆者認為,浙江省過去高速的經濟增長和近幾年出現的發展難題都與浙江的縣政擴權有密切關系。本文據此分析縣政擴權給縣政府帶來的正面和負面激勵。在浙江縣政擴權的初期,正面激勵(收益)要遠遠大于負面激勵(代價),但隨著約束條件的改變,負面激勵所帶來的損失正在逐漸增大。
二、縣政擴權與縣域經濟發展的激勵結構
20世紀90年代以來,轉型國家之間的經濟績效差異吸引了眾多學者投入對政府治理、法律秩序等制度因素的跨國比較研究。在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為何獲得與眾不同的巨大成就時,財政分權和地方競爭成為了研究重點,并且產生了豐碩的成果[5]。然而,絕大多數的此類研究將地方分權假設為中央政府與省級政府之間的分權,忽略了省以下分權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這一重要命題。這一假設并不牢靠:省級政府的職能仍是制定宏觀政策,經濟建設的具體領導者和體制改革的微觀操作者還是省以下政府,而且主要是次省級政府,因為再次一級的政府僅擁有相當有限的行政和財政資源,缺乏自由的行政意志。
(一)縣政擴權與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
實際上,中國省以下分權一直沒有具體劃一的制度安排。1994年分稅制改革只劃分了中央與省級政府之間的財政分權,卻沒有對省以下的財政體制作出任何安排,省以下的財政分權體制均是由各地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自主處理的。正是這種自主性讓浙江政府得以不嚴格遵循分稅制改革所提出來的“一級政府,一級財政”原則而保留了省管縣財政體制,并持續推行四次“強縣擴權”改革①第五輪的“擴權強縣”改革也已于2008年底啟動。由于該輪改革啟動不久,且在有些重要方面區別于前四輪改革,所以本文暫不討論。[6]30。類似于中央對省的分權構成了省政府行為的激勵結構,省以下分權也形成了省以下政府行為的激勵結構,而多樣化的省以下分權制度則意味著不同省的省以下政府可以采用不盡相同的激勵結構。從這個角度看,浙江縣政擴權改革的本質便是浙江省政府給次省級政府提供的一個獨特而復雜的激勵結構。
首先,通過省管縣財政體制擴大次省級政府的范圍。在壓力型體制下,一省的經濟發展績效往往取決于次省級政府之間的競爭關系以及相應的次省級政府行為②壓力型體制的主要特征是“靠各級行政組織從上到下規定各種指標任務,并靠各級行政組織從上到下根據這些規定的指標任務來考核選拔干部”,“帶有靠行政命令推動的計劃體制的痕跡”。可參見榮敬本、崔之元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對于浙江省來說,由于從1953年以來一直堅持省管縣財政體制(除了“文革”后期),縣政府擁有與市政府相同的財政權、主要人事權和部分行政權,因此縣政府與市政府同為次省級政府;而其他省份(除了海南省和臺灣省)在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之初的大部分時間內普遍實施全面的市管縣體制,所以只有市政府可稱為次省級政府。過去,我國地級市的經濟實力普遍較弱,難以發揮“市帶縣”的作用,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確立之后,市縣之間的經濟發展又呈現出明顯的競爭關系。浙江省將縣政府納入次省級政府的范圍不僅防止了“市剝削縣”,也適應了由市場經濟發展自發帶來的縣市之間的競爭性經濟關系。
其次,實施一系列以GDP增長為導向的財政政策,形成對次省級政府的財政激勵效應。從1995年開始,浙江省對所屬68個市縣(不含計劃單列市寧波市及其所屬縣)實施“抓兩頭,帶中間,分類指導”的財政政策,根據經濟水平差異建立了不同的激勵機制:對地方財政收入超過億元的縣(市),實行“億元縣上臺階”政策;對貧困縣和次貧困縣,實行“兩保兩掛”政策;對經濟發達或較發達縣(市),實行“兩保兩聯”政策;對地級市實施“三保三掛”政策③“億元縣上臺階”政策,即對首次上億元的縣(市)一次性獎勵30萬元,以后每年以3 000萬元為一個臺階,每上一個臺階一次性獎勵20萬元。“兩保兩掛”政策中的“兩保”即保證完成中央兩稅(增值稅和消費稅)任務和保證完成當年財政收支平衡,“兩掛”即一掛體制補助隨地方收入增長的1∶0.5比例增長,二掛個人獎勵為地方收入增長的5%。“兩保兩聯”政策中的“兩保”內容與前者相同,“兩聯”則為一按增收額環比獎勵發展資金,二按增收額環比獎勵個人。“三保三掛”政策即在“兩保兩掛”基礎上增加“一保一掛”:一保所轄縣(市)當年財政收支平衡,一掛城市建設補助與全市范圍內增收額掛鉤。。這些激勵兼容機制,即將縣(市)增收和省對縣(市)的財政補助掛鉤,將縣(市)增收和地方官員的獎勵掛鉤,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如浙江省從1995年起對17個貧困縣和次貧困縣實施了“兩保兩掛”政策,同年底便有15個縣實現財政收支平衡。
再次,推行以擴大強縣經濟管理權限為主要內容的強縣擴權,形成對次省級政府的行政激勵效應。從1992年開始,浙江省先后進行了四輪強縣擴權改革,陸續將大部分地市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賦予部分經濟強縣(市)。大多數學者都將強縣擴權視為省政府幫助縣(市)政府進一步擺脫市管縣體制制約的手段。這種角色固然重要,但強縣擴權還扮演了另一種重要角色,即通過特別獎勵強縣(市)來激勵弱縣(市)追趕強縣(市)。擁有相當于地級市的經濟管理權力對于縣(市)來說,不僅意味著在地方經濟發展方面的自主性增強,還象征著自身行政地位的提升。在浙江省的四輪強縣擴權中,強縣的范圍一直是動態變化的:1992年是蕭山、海寧等13個縣(市),1997年則縮小為蕭山、余杭兩個縣(市),2002年又擴大為20個縣(市),2006年則只針對義烏市。每一次改革均會帶來不同的激勵效果。1997年的強縣擴權促成了蕭山經濟的爆發式增長,其他縣(市)“眼紅不已”,不斷要求享受同等待遇;2002年的強縣擴權相當于省政府集中表彰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發展績效突出的縣(市);2006年則使義烏成為了“全國權力最大縣”。
最后,推行與省管縣財政體制和強縣擴權相匹配的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對次省級政府官員的晉升激勵效應。對于晉升激勵效應,周黎安評價道:“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地方官員之間圍繞GDP增長而進行的‘晉升錦標賽’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勵和增長的關鍵線索之一”[7]38。財政激勵和行政激勵無疑構成了次省級政府行為的重要動力,但縣(市)黨政一把手除了關注地方的財政收入和行政權力之外,可能更加關心自身的利益,而這種利益集中體現于官位晉升。從1983年起,浙江省縣(市)黨政一把手均直接由省委任命,他們的晉升與地方經濟增長績效密切相關。根據浙江省委組織部對20個經濟強縣(市、區)的情況分析,1992—2002年擔任書記的共有56人(不含現職),其中有44人被提拔重用,占79%[8]17。2006年,浙江省將提高義烏市主要領導人的行政級別列為第四輪強縣擴權的重要內容,對義烏市和其他縣(市)的主要領導人產生了強烈的激勵作用。
一系列的縣政擴權政策構建了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而該激勵結構對縣政府的激勵強度要遠大于市政府,這便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浙江縣域經濟高速增長的制度和政府因素。該激勵結構促使浙江縣域經濟具有三個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特征:一是縣域經濟的綜合實力出類拔萃。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全國百強縣名單中,浙江省的百強縣數量在2000—2005年一直高居全國首位。二是個別縣(市)的經濟實力超越了其所屬的地級市。以2006年為例,義烏市的GDP、人均GDP和財政收入均超過金華市區,平湖市、海鹽縣的人均GDP也略微高于嘉興市區。三是區別于市的財力差異狀況趨同,縣(市)的財力差異狀況趨異。用人均財政收入差異系數來表征各地的財力差異狀況,則市縣不同的財力差異趨勢如圖1所示:

圖 1 1997—2005年浙江地級市和縣(市)人均財政收入的差異系數① 資料來源:劉強《浙江省地區財政能力差異與轉移支付制度研究》,載《地方財政研究》2007年2期,第73 74頁。
(二)縣政擴權與特定情境
縣政擴權為浙江的次省級政府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激勵結構,但并非決策者在政策制定之前便能準確預測到一切且精心策劃一切,而是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省政府與縣政府逐步意識到縣政擴權政策和次省級政府行為之間的某種相關性,進而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形成一種良好的默契和互動關系。因此,簡單地在縣政擴權和浙江縣域經濟發展之間建立某種必然的聯系明顯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研究態度,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縣政擴權在形成縣域經濟發展的激勵結構中的作用,必須重視對該制度的特定情景分析(context-specific analysis)[9]。
為某種目的而產生的制度或政策能夠逐漸獲得自己的生命,并又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進行變化[10]1416。從制度演進的視角看,無論是省管縣財政體制還是強縣擴權,其初衷均不是為了構建一個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然而最終卻“意外”促成了這一結果。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浙江省三十多個發達縣市的財政收入就占全省財政收入總量的70%。相比較而言,地級市在全省經濟財政收入中的分量遠遠不如其他省份那樣重要,而且浙江地域狹小,地級市和縣的數量均較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行市管縣財政體制,其結果必然是兩難選擇:要么削弱省對地級市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損失集權能力),要么大幅提高省在財政總盤子中的分成比例(損失地方積極性)。保留省管縣的財政體制是浙江省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理性行為,而且還產生了外部效應,即為構建縣域經濟發展的激勵結構奠定了基礎。強縣擴權也有類似的特征。事實上,1992年第一輪強縣擴權并非是省政府對強縣的獎勵,也不是強縣的經濟發展提出了擴權的要求,而是浙江省為了“增強我省鄰近上海幾個縣(市)對浦東開發區輻射的吸納能力”①參見浙江省政府文件《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擴大十三個縣市部分經濟權限的通知》(浙政發[1992]169號)。,所以其擴權對象是鄰近上海的縣(市)。直到1997年的強縣擴權,省政府才比較明顯地賦予了行政激勵的意圖。1997年,杭州市為擴大市區范圍,吞并了蕭山市和余杭市的部分經濟強鎮,蕭山市的工業產值由全省第一降至第七。為了彌補劃鎮調整對兩市帶來的不利影響,蕭山市和余杭市聯合向浙江省提出了擴大經濟管理權限的要求。浙江省不愿因此事影響全省縣(市)的發展積極性,便同意了兩市的要求。可見,強縣擴權最終成為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是一個制度功能的變遷過程,而特定歷史環境則深刻地影響了該過程。
任何激勵結構的背后均會有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競爭和博弈關系,且處在動態變化之中。由縣政擴權構建的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蘊含固有的危機,即侵犯了地級市的“合法”利益。雖然中央政府沒有對省以下的分權作出明確規定,但是按照中央出臺的一些原則和全國的通例,市管縣才是“合法”的,這意味著該激勵結構存在政治張力。地級市政府曾借助中央決定全面推行“市領導縣”體制的時機,在1993年和1994年先后以省管縣財政體制是浙江中心城市經濟實力不強的主因和分稅制的“一級政府,一級財政”原則為由,要求具有管轄縣級財政的權限。2006年,國家行政學院調研組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已下放的經濟管理權限并未到位[11]26。當相互沖突的省、市、縣三方為了使激勵結構朝著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發展,政治張力將使激勵結構的內容、規則和程序不斷變化。浙江省政府沒有因為改革中的質疑而變動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但迫于地級市的壓力和加快建設中心城市的需求,作了不少妥協和讓步。1999年,浙江省政府對地級市實施“三保三掛”政策;1992—2001年,溫州、臺州和杭州先后“吃掉”了鄰近的經濟強縣。時至今日,縣政擴權帶來的政治張力始終沒有撕裂有利于縣域經濟發展的激勵結構,但無可否認的是,每一次的沖擊均對該激勵結構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三)縣政擴權與浙江經濟發展的特點
僅僅考察縣政擴權與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之間的關系,還不能發現浙江縣域經濟發展的全部秘密。世界銀行的《1991年世界發展報告:發展面臨的挑戰》曾提出:“發展的核心是政府與市場的相互作用。”“當市場和政府協調一致地運行時,就會取得驚人的成就,而當它們相對立時,則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12]1市場機制和政府行為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中都存在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只有兩者的互利耦合才能產生最佳的經濟發展效果。
浙江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自發生成的民營企業。改革開放初期,禁錮在計劃經濟之中的市場活力逐步被解放,浙江的很多地方已經開始自發地從事個體經營活動。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浙江的小商品生產、交易活動和個體經營經濟呈現如火如荼之勢。在1987年中央政府認可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之前,浙江各地就已經采用“戴紅帽子”、“掛戶”等做法保護和推動私營經濟的發展。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和十四大的召開為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寬松的政治環境,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更加迅速。2001年,浙江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突破50%,并在2005年攀升至71.5%。
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得益于浙江各級政府一直扮演“市場增進型”的“有效政府”角色,并根據市場體系發育的進程及其客觀要求,不斷調整自身的職能定位和行為模式[13]。學界普遍認為,支持民營經濟的發展是浙江政府在特定的改革初始約束條件下作出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之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肩負起了發展地方經濟的重任。當時的浙江,國有和集體經濟非常薄弱,根本難以指望其振興地方經濟。以溫州為例,1978年全市沒有一家大型全民企業,中小企業也只有百余家,當年11.2億元的工業產值中,國有企業僅貢獻35.6%。這樣的改革初始約束條件迫使浙江政府放棄依靠公有資本來發展地方經濟,而轉向支持民營化和市場化改革。
省級政府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想法需要借助特定的次省級政府的行為模式才能轉變為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實際行動。如果特定的次省級政府的行為模式不具備“市場保護型”的特征,那么上述轉變過程將會遭遇阻礙。然而,浙江通過縣政擴權構建起來的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恰好滿足了民營經濟發展對“市場保護型”政府的需求,這種一致性使縣政府伸出的是“援助之手”,而非“攫取之手”。其結果是,由縣政擴權構建的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和浙江經濟發展的第一個特征之間的這種互利耦合關系促使浙江經濟發展呈現出第二個重要特征,即發達的塊狀經濟。20世紀90年代之后,浙江的縣(市)政府紛紛借鑒溫州、臺州、義烏等地商品市場“帶動一片產業,活躍一地經濟,富裕一方百姓”的經驗,積極推進專業市場建設,形成了專業市場在全省遍地開花之勢。截至2003年,浙江省工業總產值在50億元以上的產業集群有35個,100億元以上的有26個,200億元以上的有6個。這些塊狀經濟往往以縣(市)為單位進行集聚,全省88個縣、市、區中,有85個出現了塊狀經濟,總產值5 993億元,約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49%。塊狀經濟越發達,縣域經濟發展就越具有獨立性,越試圖擺脫市管縣體制的束縛,也進而增強了縣政擴權的動力。
三、約束條件變動與縣政擴權的代價
對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有利的制度對另一個時期則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效果。制度的有效性取決于它對約束條件的適應程度,而約束條件也會隨著制度的建立和延續而發生深刻變化,因此制度的有效性還取決于它適應這些變化的能力。改革開放至今,浙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已經發生了比較深刻的變化,但是縣政擴權并未適應這一變化,進而出現了“水土不服”的征兆。盡管近些年浙江縣域經濟的發展勢頭并未減弱,卻已存在很大的隱患。
(一)約束條件變動與經濟轉型悖論
在縣域經濟繁榮的背后,浙江經濟發展一直存在隱憂,那就是浙江經濟長期停留在粗放型增長狀態,低水平重復和過度競爭成為現階段浙江縣域經濟的一大特征。盡管浙江省政府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意識地強調產業升級轉型的戰略意義,但這一意圖總是遭遇現實的困境。更加令人疑惑的是,經濟轉型的主要約束條件已發生較大的變動,但是產業卻遲遲未升級。
1.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動:從供給短缺到產能過剩
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體制內生的短缺經濟為浙江發展低層次、低成本的制造業提供了絕佳的機會。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國內需求日益得到滿足,浙江民營企業又發掘了另一個巨大的市場空間——外貿出口,將生產過剩的產品銷往海外。借助先發優勢和組織優勢(即以縣為單位的產業集群),浙江產業集群在全國出類拔萃,其中全國市場占有率達40%以上的產品就有160多種。但是,這些產業集群集中于技術含量不高的低端行業,進入門檻低,很容易模仿和復制。目前,浙江經濟賴以發展的條件正在發生深刻的轉變。其一,國內需求由改革開放初期的全面短缺變為目前的結構性短缺,即高技術、高加工度的產品迫切需要依靠進口,低層次、低成本的產品出現產能過剩。其二,國際需求越來越受到人為的限制。2002—2005年,浙江遭遇來自美國和歐盟等提起的貿易摩擦案件125起,其中反傾銷調查涉案84起,金額近15億美元,占全國反傾銷總涉案數和涉案總金額的40%以上。一旦國內和國際的市場供求關系同時發生激烈的異動,浙江的縣域經濟必然會遭遇重大危機。
2.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從資本稀缺到資本溢出
浙江的塊狀經濟是在資本稀缺的約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1952—1980年,浙江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134.02億元,僅占全國總投資額的1.56%;1953—1978年的26年中,浙江人均獲得的國有投資僅411元,居全國末位。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為發展縣域經濟的必然選擇,而產業集群的組織形式又解決了資本稀缺帶來的規模問題。在經歷三十年的高速發展后,要素稟賦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資本的相對豐裕程度大大提高。但是,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浙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并沒有相應地升級,而是出現了資本溢出現象,即積累的資本遠遠超過省內現有產業的容納程度,過剩的資本為了尋求“利潤”不斷地流往全國各地乃至國外。2005年,浙江省銀監局公布的《浙江企業省外投資情況調查報告》指出,3.3萬個在浙企業在省外投資額高達3 000多億元。更典型的是,還有浙江炒房團、炒煤團等巨額游資。
由此看來,浙江經濟轉型正在面對一個悖論:一方面,由于產能過剩,縣域經濟陷入了長期低成本競爭的陷阱,浙江的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大量資本來推動產業升級;另一方面,由縣域經濟發展而積累起來的大量資本并沒有反哺浙江的產業升級,而是“出逃”省外。如果任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繼續吸引浙江的資本,中西部省份也憑借勞動力和資源優勢誘使浙江民營企業走出浙江,浙江的經濟將有被“掏空”的可能。
(二)縣政擴權的代價
浙江經濟轉型為什么存在這樣一個悖論?究其原因,以塊狀經濟為特征的縣域經濟是一個分散的、低資本密度的發展模式,根本容納不了過多的資本,而浙江省中心城市的要素吸納和集聚能力并不突出,因而只能任憑資本溢出。這是縣政擴權的代價。
1.區域分割
縣與市、縣與縣之間的獨立性和競爭性在浙江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確實有力地推動了塊狀經濟的蓬勃發展,但是隨著市場供求關系從供給短缺轉為產能過剩,要素稟賦結構從資本稀缺轉為資本溢出,區域分割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逐步擴大,最終成為產業升級難以實現的關鍵因素。縣政擴權賦予縣政府發展經濟的自主性,使其對地級市的依賴相對較小,同時縣與縣之間的經濟聯系也因行政區域分割而相對獨立,由此浙江經濟形成了“蜂窩狀”的特征,每個塊狀經濟都成了封閉的或自成體系的經濟實體。這些塊狀經濟以低附加值的傳統制造產業為主,往往只需要整合單個縣域的要素就能釋放巨大的產能,極少需要跨區域的協作和分工。由于不存在跨區域協作的經濟動力,縣政擴權又大大削弱了地級市統籌各縣發展的行政權力,縣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通常忽視與其他區域之間的協調以及重復建設所帶來的資源浪費。區域分割和產業分割相互強化導致塊狀經濟“鎖定”于特定的產業,阻礙了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區域間的優勢互補,從而不利于推進產業升級。積累的資本一部分用于擴大產能來追求低額利潤,另一部分由于超出了縣域開發容量而被迫另覓“財路”。
2.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不強
由縣域經濟發展而積累起來的資本大量“出逃”省外,沒有向浙江省內的中心城市聚集,是因為這些中心城市缺乏強大的要素聚集能力。以2002—2003年為例(表1),浙江地級市財政收入占全省財政收入的比例僅為50.69%,而廣東、江蘇和遼寧則均超過60%。縣政擴權是浙江中心城市要素聚集能力不強的重要原因。其一,縣政擴權延滯了極化效應的自然進程。赫希曼指出,經濟增長空間傳遞過程中存在著兩種效應:“滴流效應”和“極化效應”。滴流效應是指增長極區域影響其他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有利過程,而極化效應則反之①轉引自華東師范大學西歐北美地理研究所、城市和區域開發研究中心編《區域經濟和城市發展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大多數地級市作為經濟增長極,尚處于極化效應起主導作用的時期。地方官員出于政績的考慮,往往借助市管縣體制“刮縣”、“卡縣”以強化地級市的極化效應。浙江通過縣政擴權成功避免了這種扭曲行為,但也帶來了另外一種扭曲行為,即區域分割延滯了極化效應的自然進程。縣政擴權帶來的區域分割,特別是市縣分割,導致了中心城市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自然地集聚要素。其二,由縣政擴權構建的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對地級市政府的激勵強度要遠小于縣政府。縣政擴權的政策意圖在于增強縣政府發展縣域經濟的自主性,地級市政府在這一改革中扮演了“利益受損者”的角色。再加上省政府沒有構建出一套針對地級市政府的、與縣政擴權同樣有效的激勵結構,地級市政府發展地方經濟的動力明顯不如縣政府。

表1 2002—2003年浙江和廣東、江蘇、遼寧的地級市財政收入比較 單位:%
四、結 語
如果說浙江省前期的經濟發展主要得益于縣政擴權所帶來的縣域經濟繁榮的話,那么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就是如何減少縣政擴權的弊端。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浙江通過縣政擴權發展出了一套有效的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正是這套激勵結構與民營經濟發展之間形成的互利耦合關系極大地促進了浙江縣域經濟的發展。隨著市場供求關系從供給短缺轉變為產能過剩,要素稟賦結構從資本稀缺轉變為資本溢出,縣政擴權的弊端越來越凸顯。如果浙江不能適時地發展出新的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來促進次省級政府的行為轉型,那么次省級政府的行為很有可能從前期的“援助之手”變成“阻礙之手”,使浙江難以實現產業升級。雖然我們尚未完全明白浙江應該構建一個什么樣的新的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以及如何構建起這個新的次省級政府的激勵結構,但它至少應該包含以下內容: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有利于跨區域的要素自由流動;解決次省級政府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問題;增強發展中心城市的激勵等。
(感謝《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
[1]毛壽龍:《中國地級政府的過去與未來》,《安徽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第1 5頁。[M ao Shoulong,″The Past and Future of Prefectural Government in China,″Journal of Anhui Institute of Education(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No.2(1995),pp.1 5.]
[2]周振鶴:《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現狀及問題》,《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 5期,第 17 22頁。[Zhou Zhenhe,″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Reform in the Local Governments,″Strategy and Management,No.5(1996),pp.1722.]
[3] 任衛東、吳亮:《審視行政“第三級”》,《瞭望》2004年第23期,第32 35頁。[Ren Weidong&Wu Liang,″A Reflection on the Third Level of Government,″Outlook,No.23(2004),pp.32 35.]
[4]王吉平:《理論界對市管縣體制改革的探討》,《蘭州學刊》2005年第5期,第 32 33頁。[Wang Jiping,″A Research Review of City-Governed-County System,″Lanzhou Academic Journal,No.5(2005),pp.32 33.]
[5]張軍、周黎安編:《為增長而競爭:中國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Zhang Jun&Zhou Li'an(eds.),Growth from Below: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Shanghai:T ruth&Wisdom Press,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
[6]陳國權、李院林:《地方政府創新與強縣發展:基于“浙江現象”的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第25 33頁。[Chen Guoquan&Li Yuanlin,″The Innov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sperous Counties:A Study Based on Zhejiang Phenomenon,″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and Social Sciences),No.6(2009),pp.25 33.]
[7]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第 36 50頁 。[Zhou Li'an,″Governi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Tournament M odel,″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No.7(2007),pp.3650.]
[8]沈錫權:《強縣經濟撐起經濟強省》,《今日浙江》2002年第24期,第15 18頁。[Shen Xiquan,″Development of County Economy Leads to a Strong Economic Province,″Zhejiang Today,No.24(2002),pp.15 18.]
[9]A.Greif,″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8,No.2(1998),pp.8084.
[10][美]阿維納什?K.迪克西特:《經濟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學的視角》,劉元春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A.K.Dixit,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A Transaction 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trans.by Liu Yuanchun,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4.]
[11]張占斌:《政府層級改革與省直管縣實現路徑研究》,《經濟與管理研究》2007年第4期,第22 27頁。[Zhang Zhanbin,″Study on the Government-Hierarchy Reform and the Path to Province Directly-Administrated Counties,″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4(2007),pp.22 27.]
[12]世界銀行編:《1991年世界發展報告:發展面臨的挑戰》,北京:中國財政出版社,1991年。[The World Bank(ed.),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Beijing:China Financial&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1991.]
[13]何顯明:《政府與市場:互動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變遷——基于浙江現象的個案分析》,《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第2 10頁。[He Xianming,″Government and Market:Role T 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n Mutual Promotion:A Case Analysis of Zhejiang Phenomena,″Zhejiang Social Sciences,No.6(2008),pp.2 10.]
-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預印本的其它文章
- 新聞框架的傾向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