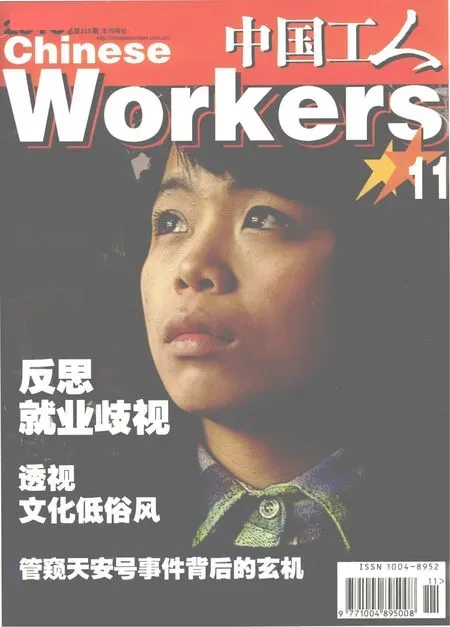重新審視勞動在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江松
重新審視勞動在社會結構和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江松

關于勞動在社會生活和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個爭訟紛紜的問題。一些論者傾向于夸大勞動的地位和作用,一些論者傾向于貶低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試圖對勞動的地位和作用有一個更為客觀和理性的認識。
1 勞動范圍的絕對擴大與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
所謂勞動范圍的絕對擴大是指,人類改造自然界的廣度、強度、力度和深度,人類勞動的平面的和立體的、橫向的和縱向的半徑,一直在并且還將要不可遏止地增加。所謂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是指,勞動在社會生活結構中所覆蓋的范圍在逐步縮小,所占有的比重在逐步降低,相對而言,人類其他的實踐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范圍在逐步擴大、比重在逐步提高。
這似乎是兩種方向相反的運動,但其實是指向一個方向——人類自由的擴大和人類文明的發展。這是因為,第一,勞動邊界的相對縮小恰好是勞動范圍的絕對擴大的結果,相反,人類與自然的物質變換的范圍越狹窄,人類改造自然的程度越低,勞動在人類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的邊界就越寬、比重就越大,乃至勞動就是唯一的和包羅萬象的實踐活動和社會生活;第二,其他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的發展,比如政治實踐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會管理的科學化和人性化、文化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等等,反過來也在極大地推動勞動生產力的發展。
并不是每個人都理解了這種相反相成的運動。很多人看到勞動改造自然界的范圍的絕對擴大,就誤以為勞動在社會生活中的范圍和邊界也在絕對擴大,于是在人們的潛意識和意識中,自覺不自覺地出現了勞動概念的泛化。
一是把勞動混同于生產,于是進行人口再生產的家務活動被稱之為“家務勞動”,進行精神文化產品生產的活動被稱之為“腦力勞動”或“精神勞動”,政治活動被稱之生產公共產品和服務,進而又被稱之為“管理勞動”。如果順著這一邏輯,性愛活動能夠“生產”出小孩,那么男女戀愛和做愛也是一種勞動了。
二是把勞動混同于工作或職業,于是舉凡一切在各個社會生活領域提供一定的投入、產出并獲得相應報酬的職業活動,都被稱之為勞動。日常用語和學術研究中經常提到“不勞動者不得食”、“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實際上都是把勞動等同于工作或把一切工作等同于勞動了。為了與黃、賭、毒等非法牟利活動相區別,我們可以把工作或職業界定為是合法的謀生或贏利活動,但許多這樣的活動也顯然不能稱之為勞動。比如股票交易活動也要付出一定的體力而且要付出極高的智力,這種活動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很高的回報并且因為繁榮了資本市場而促進了市場經濟和物質資料生產的發展。這是一種合法的并且受到社會鼓勵和保護的工作或職業。我們還經常在各個彩票售賣點上看到若干彩民在非常認真地從事他們的職業活動。社會上還有許許多多與物質資料生產沒有直接聯系的工作或職業活動,它們都要付出一定的體力和智力,都在為社會提供這樣或那樣的產品和服務,都在以某種方式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它們都叫做“勞動”。
面對著勞動概念的泛化,筆者堅定地把勞動界定為活勞動或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這樣一種活動的確在絕對地增長和壯大其改造自然的力量,但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也的確在相對地縮小自己的范圍和邊界。
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Labour的本義指分娩時的痛苦(與中文“生產”的原義同義),也指人的身體的令人焦慮的損傷、張力、壓力、重負等狀態,因為人最初的確主要是運用其體力去與比自己更強大的、異己的自然力量作斗爭的。古希臘和中世紀把勞動看作是由奴隸或窮人所從事的卑賤的養家糊口的活動,而把自由人的擺脫了謀生壓力的活動叫做Art。這種理解雖然帶有階級的偏見,忽視了勞動所包含的主體性和個體性內容,但還是比較忠實于勞動的詞源學意義,強調了勞動所具有的直接改造自然的含義以及勞動的辛苦與艱難。無獨有偶,中國古人也很強調勞動的這一方面。筆者認為,應該在繼承對勞動的這一傳統理解的基礎上,確定現代勞動的范圍和邊界。
筆者反對用勞動泛指一切生產活動、經濟活動、職業活動、實踐活動,并不是要讓勞動保持在某種原生狀態,或停留在某種原始水平上。實際上,現代勞動在量和質兩方面都遠遠超出了原始的和古代的勞動。首先,雖然勞動在現代人類生活結構中的比重已經并還在不斷降低,但現代勞動的絕對量和總量已經千百倍地大于原始勞動和古代勞動了;其次,現代勞動在質上也已經無可比擬地高于原始勞動和古代勞動,這主要表現在現代勞動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正在上升為主導的方面,智力與知識要素、科學技術和管理要素正在成為主要的勞動生產力。因此,如果說在原始和古代社會,只有那些利用簡陋的工具、運用初級的經驗知識并受血緣和地域條件制約的物質資料生產才叫做勞動的話,那么在現代社會,物質資料生產已經發育和發展為分工極為細密、層次極為豐富、結構極為復雜、范圍極為廣大的網絡體系,所有加入這個網絡體系的活動,除了資本的投資經營活動之外,都可以叫做勞動,即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那些體力支出雖然很小但直接加入物質財富產出鏈條的科學技術活動和組織管理活動,也是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勞動,而且是比較高級的復雜勞動。
當然,在現代社會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與其他生產活動、經濟活動、職業活動、實踐活動密切聯系和依賴、相互轉化和滲透的情況下,要在勞動和其他活動之間畫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是不可能的,在兩者之間會有一塊比較模糊的區間,其間的很多活動兼有勞動和其他活動的雙重性質。但是不管怎么說,離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產比較遠的活動,就不再屬于勞動的范圍。
2 勞動在人類實踐和社會生活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厘定了勞動的性質、范圍和邊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來探討勞動的地位和作用了。
勞動是一種最核心、基本、關鍵和重要的實踐活動
人類實踐活動包括物質資料生產、社會變革活動、文化產業活動和日常生活實踐四種形態。在這四種實踐中,迄今為止,物質資料生產仍然是人類第一位的實踐活動,這不僅僅是因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受到自然界的永恒制約,只有物質資料生產才能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和人類的其他實踐提供物質條件,而且還因為其他實踐活動最初都是從物質資料生產中發展出來的。物質資料生產又可以進一步被區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種形式,即勞動和資本經營活動,其中勞動對于資本經營活動具有本體論的和歷史的優先性:被開發的土地等自然資源、生產工具、作為交換媒介和儲藏手段的貨幣等等生產條件和生產資料是積累和凝固起來的活勞動,是勞動的產物;只有在相當發達的勞動分工和交換的基礎上,資本才能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被產生出來并被運營起來。雖然被集中經營的資本相對于分散的勞動表現出強大的優勢,但資本之所以能夠被集中經營,本身又是分散的勞動長期積累的結果。
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世界和社會結構的基礎
人類的動物性活動、實踐活動和精神活動,構成了人類生活的總和,構成了人類的生活世界和人類社會,而勞動正是這座宏偉建筑物的基礎。正像馬克思所說的,只要人類停止勞動哪怕是一周的時間,這座建筑物就會轟然倒塌。我們不妨反過來想一想,在所有活動中,人類的動物性活動能夠作為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精神活動能夠作為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政治活動能夠作為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文化產業活動能夠作為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日常生活活動能夠作為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人類的資本經營活動能夠作為生活世界的基礎嗎?不能!這一切被排除之后,只剩下勞動可能具有這樣的功能,而勞動也真的具有這種功能——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為此作證:一旦失去勞動所提供的吃穿住的資料,我們就會活活地被餓死和凍死;我們的確需要其他人類活動所創造的條件才能夠活得更好一些,但沒有勞動所創造的生活資料,我們連活著都是不可能的。
3 勞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說過,所謂世界歷史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恩格斯也說過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并相信可以在勞動中找到打開社會歷史奧秘的鑰匙。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也可以說是一種勞動主義歷史觀(勞動史觀),或勞動決定論,或勞動一元論。不過,從馬克思、恩格斯也很重視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的能動作用而言,勞動的地位和作用又是受到限制的。借鑒19、20世紀其他歷史哲學的成果,我們試圖重新確定勞動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勞動是人類歷史的出發點、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并不能決定和解釋一切
勞動使人直立行走從而擴大了人的視野和腦容量,勞動使語言交流成為必要并得以實現,勞動創造了人賴以生存和進一步發展所絕對必需的物質財富,勞動過程孕育了人類全面發展的萌芽,勞動使人與自然對立起來又使人與自然相統一……所有這些都表明勞動是人類歷史的當之無愧、無可替代的出發點、入口、奠基石和母腹。但出發點并不預先決定終點,入口并不是出口,奠基石并不等于整個建筑,從母腹中產生出來的兒女后來會長大成人并成為獨立的個體。問題的關鍵在于,從勞動這一原點中分化、分岔、滋長、蔓延出來的東西,比如語言、巫術、宗教、政治、戰爭、法律、習俗、社會管理、社會交往、科學、技術、哲學、藝術等等實踐形式和生活領域,后來都得到了獨立的發展,并且反過來促進了勞動的發展,這些東西是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勞動諸要素的;它們和勞動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又具有自身獨特的發展規律,不能簡單地用勞動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去說明它們本身發展的邏輯和辯證法。
最初,正是勞動的發展使這些非勞動領域的產生和發展成為必要和可能,但人類的創造力一旦投入到這些領域,它們就不僅在范圍上不斷擴展起來,而且在地位和作用上也不斷提高起來。于是就在這些領域之間以及這些領域與勞動之間形成了極為錯綜復雜的相互作用。當然,相互作用并不等于各個領域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它們交替地起主導作用,有時是革命和戰爭,有時是經濟制度的改革和發展,有時是科學技術,有時是思想意識形態,而勞動則始終是所有這些矗立于其上的基礎。
勞動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但不是唯一的動力
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前提和基礎,同時也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并且至今仍然是主要的動力。馬克思主義指出,勞動生產力推動了科學技術的變革,推動了生產關系的變革,推動了政治制度、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變革,推動了人們的社會心理、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那么,又是什么推動了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呢?是人類與自然的永恒矛盾,是人類物質需要的永不滿足和物質財富的永恒匱乏。這樣的一幅歷史畫卷看起來是脈絡清晰、簡明扼要的。
但這種分析對于深思熟慮的頭腦來說還是過于簡單的。它至少忽視了另外兩種推動歷史運動變化的力量:精神的創造力量和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前一種力量在性質上高于勞動生產力,后一種力量在性質上低于勞動生產力。
精神的創造力量來自于又高于勞動生產力。勞動本身包含了精神的創造力量,但勞動中的精神創造力量是局限于當前勞動過程、服從于眼前利益和目標的,因而是受到很嚴格的限制的。從勞動中分化出去的精神創造活動則超越了物質利益的局限和當前勞動任務的限制,而取得無限發展的自由和空間,使得人類創造出輝煌燦爛的精神文化。這些精神文化表面上是不實用的甚至是無用的,但卻通過種種管道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滲漏到勞動過程中去了,從而大大地提升了勞動的水平、層次、生產力和財富創造能力。
如果說精神的創造力量是與勞動生產力呈正相關的關系,它們共同推動了人類歷史的進步,那么反精神的破壞力量則是與勞動生產力呈負相關的關系,它破壞了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把人類歷史拉向后退的方向。
反精神的破壞力量主要有兩種:暴力和狡智。
我國當代歷史學家吳思通過對中國歷史的解讀,提出了著名的“血酬定律”,揭示了暴力在歷史中觸目驚心的地位和作用。
所謂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報酬,體現著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系。從晚清到民國,吃這碗飯的人比產業工人多得多。血酬的價值,取決于所拼搶的東西,這就是“血酬定律”。
強盜、土匪、軍閥和各種暴力集團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對暴力的報酬,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報酬、利息是對資本的報酬、地租是對土地的報酬一樣。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于拼搶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于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愿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
為了將暴力行業性命交易中買主和賣主兩大集團區別開來,我們稱皇帝、軍閥、匪首等暴力集團首領為“血本家”,稱賣命的士兵為“賣血者”。血本家在招兵買馬之后就對平民百姓獲得了生殺予奪的暴力強權,平民百姓要想活下去,就要向血本家繳納貢賦或保護費。
血酬第一定律:匪變官。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
血酬第二定律:官變匪。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團也可以退化為土匪。
血酬第三定律:匪變民。隨著血酬逐步降低,生產行為的報酬相對提高,土匪可以轉化為農民。
血酬第四定律:民變匪。假定血酬不變,隨著生產收益的減少以至消失,大量生產者將轉入暴力集團。
血酬第五定律:變法改制。為了追求血酬的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么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愿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暴力靠硬搶,狡智靠巧奪。仿照吳思的“血酬定律”,我們也可以在歷史的生存游戲中發現某種“狡智取酬定律”,而且這條定律起作用的范圍和程度一點不弱于“血酬定律”。
血淋淋的歷史還告訴我們,在很多時候,靠發展勞動生產力和精神的創造力量并不能遏制和戰勝狡智和暴力,勞動者和創造者為了奮起反抗、戰勝邪惡,也不得不使用狡智和暴力的手段。馬克思就說過,暴力是歷史的助產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于是階級斗爭和用正義的暴力武裝反抗邪惡的暴力就構成了另一條歷史的進化路線,補充了勞動推動歷史進化這一條主線。我國當代作家姜戎在其蜚聲中外的《狼圖騰》一書中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勞動創造人”的命題是片面的,必須補充“戰斗創造人”這個命題。
從上述論述可知,勞動雖然是極為重要的但不是決定一切的力量,僅僅擁有勞動力對人類和個人來講都是不夠的。貶低勞動當然是錯誤的,但盲目崇拜和夸大勞動也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