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三圣難再的浮想
○淮 茗
五四三圣難再的浮想
○淮 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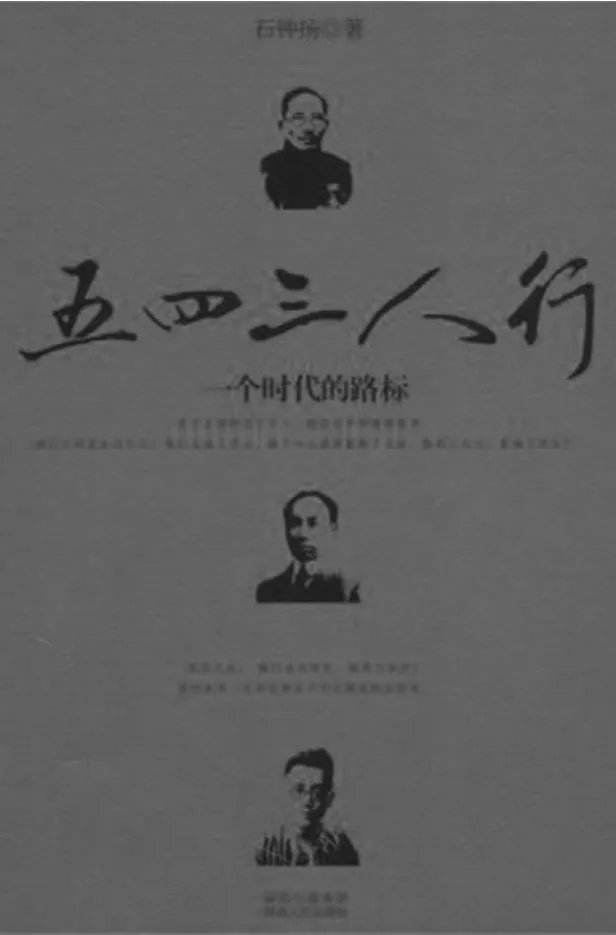
《五四三人行:一個時代的路標》,石鐘揚著,陜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38.00元
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不僅僅在其影響力和知名度,更為重要的是它為后人提供了無限的想象和談論空間,即便幾十年、幾百年過去了,人們仍然可以津津有味地談論它,常談常新。這里所說的經典,既可以指文學藝術、學術著作,也可以指那些著名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比如“五四”,如今它成為一段神話,其對20世紀及其之后中國的深遠影響不用筆者多言,相關的研究著述可以用成百上千來形容,但只要靜下心來,細細回味這一歷史事件,仍然能獲得一種鮮活的感受,仍然能從中獲得啟發。近讀石鐘揚先生的《五四三人行:一個時代的路標》一書,對此感觸頗多。
在該書的前半部,石鐘揚先生用了較長的篇幅以及頗為生動、感性的筆墨,重新回顧、描述了這段歷史,既講到了前臺的學生,更講到了幕后的老師,當然,其重點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三位人物;由此切入,分析“五四”發生的歷史背景及必然成因,特別強調“五四三圣”人物的重要歷史貢獻。其中不少事件和細節,我們已經頗為熟悉,但在閱讀時仍然感到新鮮,仍然會被打動。讀罷全書,意猶未盡,心潮起伏,難以平靜。何以如此?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俗話說,讀史可以使人明智。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人們在閱讀歷史的時候,有自身所處的現實作為背景,不時可以進行對照,從歷史反觀現實,從中獲得人生智慧和啟迪。石鐘揚先生寫作此書,顯然也有這個用意在。三人行則必有我師,作者以此作為書名,正表達了這個意思。我們今天回味“五四”這段歷史,之所以感到新鮮,之所以仍能被打動,顯然與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現實有關,對那些我們生活中欠缺的東西往往會格外關注,引起共鳴。
如今回顧這段歷史和人物,特別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三人,心中的第一感受就是:這是一段不可復制的神話,這樣的人物再不可能出現,將來若干年內也未必能夠;再也沒有這樣一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校長,再也沒有這樣充滿生氣、不拘一格的文科總長,再也沒有這樣一呼百應、開疆拓土的教授。更不用說這三位人物自身的巨大人格魅力了。當下大師、泰斗之類的阿諛之詞滿天飛,寫幾篇文章、出幾本書就是專家;弄了幾個獎、當了個官,就成了著名學者;熬得年歲大些,就變成了大師、泰斗。有的人竟然還欣然接受,頗為自得。評價得有標準,將當下這些所謂的大師、泰斗和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放在一起,其荒謬可笑立即就會顯現出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樣的規律到了當下似乎已經失靈,號稱或被尊為大師、泰斗的人倒有不少,但其中有幾個能領風騷幾百年哪怕幾十年?如今的教育及學術體制與“五四”時期的草創相比,要更為系統、完善,中國人口也已是當年的數倍,教育的普及程度也非昔日可比,學術積累日益豐厚,有更多經驗、教訓可資汲取、借鑒,按道理說應該出現更多像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樣的人物,但為什么這樣的人物再也沒有出現呢?相反,不少人在談論現在的大學和學術研究時,更多的是充滿憂慮和無奈。翻開報刊,打開網絡,要么是教授抄襲,要么是學術不端,要么是學術腐敗,要么是文憑作假。當嚴禁抄襲、遵守學術規范變成對教授學者的最高要求,需要反復強調時,當抄襲者比揭發者還理直氣壯時,你還能指望這個時代能出現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這樣領時代風騷的人物嗎?
石鐘揚先生將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三人定位為時代的路標,這是非常準確到位的,也是頗有啟發性的,它實際上反映了作者對內心知識分子的一種期許。反觀當下的教授學者,其影響力早已不能與這些人物同日而語,他們不僅不是時代的路標,相反還被公眾丑化,成為卑瑣、無能的代名詞,甚至被視為時代的絆腳石。這固然是因為各自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但更重要的是,人們對這一階層的看法和評價也完全發生改變。當下,“白天是教授,晚上是野獸”已成為一個流行語,教授學者從人們敬仰的對象已經變成被嘲諷、蔑視的靶子。如此鮮明的對比,怎么能不讓人為之感慨萬千,產生今不如昔的感嘆。當大學失去靈魂,當知識分子喪失人文精神,自我矮化,淪為官僚或論文機器時,你能指望他們成為時代的路標嗎?
據說該書最后一章圍繞著一個假設展開論述,那就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三人如果生活在20世紀下半期的大陸地區,他們的命運該會如何?這樣的假設是很吸引人的,此前人們曾熱烈討論過類似的問題,不過主角則是魯迅。當然這一假設會讓一些人感到尷尬乃至不舒服,所以這一章最后被刪去了,讀者無緣看到。我對這一話題頗感興趣,覺得可以繼續問下去,提出如下一個假設,也許更有意思,也更有現實感:假如三人生活在21世紀之初的中國,他們的命運又會如何?
依照我對當下高校教師生存狀態的了解,最可能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
身為大學校長的蔡元培肯定比當時更忙,他必須應付上級主管部門的本科評估以及各類名目繁多的檢查,要為本校多上幾個博士站點、多出幾名院士、長江學者之類的面子人物而積極公關,更要為學校的搬遷和基建費心,要么坐在談判桌上,要么坐在主席臺上,要么坐在酒店的包間里。至于本校的學生和老師,那是肯定見不到這位校長的,除非在開學或畢業典禮這樣的場合,因為他是副部級干部,因為他是大官。
身為文科總長的陳獨秀盡管行政級別不如蔡元培,但他忙碌的程度也不亞于校長,讓他費心的,是各種學科、中心、基地、項目、獎項的評選以及各種名目的考核、會議。他還要為全院的創收和教師員工的福利絞盡腦汁,和校內、校外的其他單位競爭,至于老師的職稱、住房乃至同事間的吵架、配偶的偷情、孩子的入學等,都是他必須關心而且要解決的。他會忙得像華威先生一樣滿天飛,平常很難見到其蹤影。如此忙碌,自然沒有心思來辦《新青年》,即使辦的話,也難免不收版面費。
至于身為名教授或學術明星的胡適,同樣會忙碌異常,職稱、項目、評獎一個都不能少,都是需要極力爭取的,否則很難在學校立足。電視、報刊上露露面,保持知名度,也必不可少。閑暇時再到什么講壇、講堂之類的地方走走場子,掙點外快。至于文章,也不能隨便發表,一定得選擇核心刊物,最好是CSSCI收錄的期刊,否則像《文學改良芻議》、《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這樣的文章在年終考核時,什么都不算,不管這些文章水準有多高,影響有多大。假如任務量或工分不夠,是要被扣津貼的。
忙碌歸忙碌,個人的好處自然是少不了的。假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生活在當下,他們得到的東西可能連他們自己都感到驚奇,從自己寫的、編的、掛名的一套套、一本本的學術著作,到國家級、省部級的各類金光閃閃的榮譽、獎項、名號,再到連自己都弄不清名目的各種收入。盡管“五四”期間教授的工資相當之高,曾令后人羨慕不已,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如果生活當下,他們的收入肯定會超過當時。但問題在于,如此庸庸碌碌的蔡元培還是蔡元培嗎?如此八面玲瓏的陳獨秀還是陳獨秀嗎?如此利欲熏心的胡適還是胡適嗎?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理由不必多說,用一句流行語來說,那就是地球人都知道。這也正可以解釋,為什么90多年過去了,中國再也出不了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這樣的人物,大家只能在平庸的年代里隨波逐流、稀里糊涂地過著平庸的生活。
一個人再睿智,再有能力,也無法改變整個社會,何況當下的一些知識分子早已經沒有改造社會的雄心壯志,大家更愿意“與時俱進”、同流合污。更多的時候是環境改變人,而不是人改變環境。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他們能大刀闊斧地改造當年的北京大學,但他們假如生活在今天,可能面對一個中文系都一籌莫展,在鐵板一塊的教育和學術制度面前碰壁。當大學淪落為等級森嚴的衙門,當校長、院長淪落為搖頭晃腦的官僚,當教授淪落為麻木不仁的論文機器,你還能指望這樣貧瘠荒蕪的土地能培養出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嗎?畸形的機制產怪胎,這大概是對當前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體制的準確描述。
感謝石鐘揚先生和他的《五四三人行:一個時代的路標》提供了這樣一個浮想聯翩的好機會,它讓筆者重新回顧了這段歷史,也更看清了現實。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