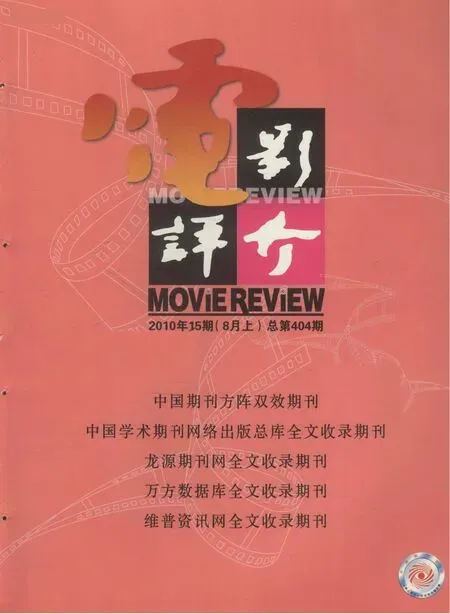《山海經》中變形神話蘊含的生命觀
一、引言:變形神話概述
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提出:“如果神話世界有什么典型特點和突出特征的話,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則的話,那就是這種變形的法則。”[1]死與再生,是所有民族神話的共同主題,探尋死亡的原因與再生的要求是人類最初而且最熱切的問題,而由死到生的過渡,通常是由這種變形神話來完成的。變形神話是一切神話的母題及共通內核,解釋變形神話也成為神話內涵的關鍵之一。
“變形”(metamorphosis),一般學術討論上也稱之為“變化”,指的是:“一個人、一個動物或物體改變了自身的形狀并以另一種新的形狀出現(xiàn),我們稱之為變形。”[2]人在他生存的現(xiàn)實世界中,永遠不會超越其天生的特定形體和時空的限制,但人類憑借他們內心深處突破限制的強烈欲望和智慧的幻想,克服了形體上的束縛,以彌補現(xiàn)實的不足,變形神話就應運而生了。在《山海經》這本上古奇書中,不僅保存了中國最原始的瑰麗神奇的各種神話,而且在其中關于變形的神話多次出現(xiàn),給本已神秘的山海神話又蒙上了一層面紗。變形神話不僅解釋了生命與死亡的問題,表達了原始初民在這方面的感受,而且發(fā)揮了原始的智慧,以充分自由的想象將他們的感受和需要用象征的方式表達出來。
變形在原始人那里是宗教信仰的執(zhí)著表現(xiàn),是對生命永恒的追求,是對死亡的抗拒,是他們變有限為無限的一個創(chuàng)造,其中最核心的意念,便是對生與死的解釋。原始初民對死亡是抗拒的,在他們構筑的神話世界中,對死亡進行否定,“在某種意義上,整個神話可以被解釋為就是對死亡現(xiàn)象的堅定而頑強的否定。”[3]
二、變形神話蘊含的生命觀
1、萬物有靈觀
萬物有靈觀是原始初民通過對夢境、幻覺、睡眠、影子等現(xiàn)象的認識中萌發(fā)的。在遠古時代,人們并不了解自己的身體構造,無法解釋一些自己困惑的現(xiàn)象,便通過對夢境或幻覺的回憶來理解,產生了靈魂可以脫離肉體而獨立存在的意識。原始初民在形成相對獨立的靈魂不死的觀念后,又進一步提升,將已形成的靈魂觀念擴而大之,擴展到自然界的萬物,也就是萬物有靈。他們相信,不僅人有靈魂,日月山河、樹木花鳥等無不具有靈魂,靈魂具有獨立性,人死后會離人而去,寄存于海洋、山谷、動植物或他人的身上,而且,人的靈魂與宇宙萬物的靈魂是息息相通的,可以互相轉化。正因為如此,原始初民用他們無窮的幻想和智慧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詭奇神秘、生機勃勃的神話世界。在這個神話世界里,人與自然萬物融為一體,同出一源,無論是人還是動植物,都可以相互變化,通過這種變化,使靈魂得到了轉變和遷徙,生命得到了延續(xù)。
在《山海經》中,人與宇宙萬物融為一體,同出一源,無論動植物還是其他生物,都可以互相轉化,物種的界限被打破了,人變成鳥,草化為蟲,靈鼓化為黃蛇等等,在這里,原始初民化宇宙的存在為人類的生命,各類生命統(tǒng)歸一源,處處充滿超自然的生命力。《大荒西經》云:“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及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顓頊死即復蘇,生命以另一種形態(tài)得以延續(xù),在這里,靈魂在人與物之間是相互流動的,生命借助靈魂不死的方式而等到了永恒的無限。神話是以這種形式教導人們死亡并非生命的結束,它僅意味著生命形式的改變,存在的一種形式變成了另一種形式,如此而已,生命與死亡之間,并無明確與嚴格的區(qū)分,兩者的分界線曖昧而含糊,生與死兩個詞語甚至可以互相替代。這種宇宙萬物泛生泛神,萬物息息相通的觀念,正是原始初民樸素幼稚、生機勃勃的心靈境界的反映。
2、超時空觀
原始初民在面對脆弱的生命時,延續(xù)生命的途徑和方式是變形,用“新”的生命形式來代替“舊的”生命形式,從而獲得在時間與空間上的無限性,將有限的生擴展到無限的生。一種生命可以通過變形而開始另一種生命,生生相續(xù),變形使得生命不僅在空間上具有任意性,而且也超越了時間的局限性,變形使得生命絕對超越時空,生命從有限走向無限。
死亡是時間流逝的結果,在死亡時間的重壓之下,原始初民渴望從時間的流逝中將自己解脫出來,對時間的超越也成為了對死亡的超越。原始初民最早對時間的認識來源于對自然現(xiàn)象的觀察,日月運行形成了他們最早的時間觀念,因此,早在遠古的神話時代,日與時間的關系就很明確了,在初民的意識之中,日即時間,兩者是相疊合的。在《山海經》中,《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夸父逐日,正是追趕著時間,希望能夠超越它,將死亡遠遠地拋在背后,也就能夠超越死亡,獲得生命的無限。而“夸父逐日”是以失敗而告終的,他的形體因“道渴而死”,但在初民們追求生命無限的執(zhí)著信念中,夸父“棄其杖,化為鄧林”,也就是在舊的形體上創(chuàng)造出了新的生命,使舊有的生命以另一種形式得到了延續(xù),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夸父是戰(zhàn)勝了時間的。就這樣,在不斷流逝的時間長河里,生命成為息息不止的循環(huán),死亡僅僅是由一種形體向另一種形體轉變的過渡而已。
變形神話,不僅在時間上使生命超脫了出來,而且在空間上也連絡了甚至消除了生命種類的區(qū)別,充滿神奇怪誕色彩的變形再生,使生命得到擴展。《大荒西經》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作為中國生命創(chuàng)造之神的女媧,其腸化為十人,生命在數目上得到增加,并通過這種形體的變形,超越了自身生命形體的局限,使生命在空間上獲得擴展和延伸。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原始初民認為生命的形成不是通過“生殖”的方式,而是通過“變形”的方式而來的,他們用這種“變形”的方式來解釋生命的生成,解釋著自然萬物的形成。類似的神話除了上面提到了“女媧之腸”以外,還有英雄的軀體可以化生萬物的神話,如盤古、女媧以及夸父的神話,以此來解釋人類以及宇宙萬物的由來。
3、拒絕死亡觀
弗洛伊德認為:“生命的無限延續(xù),即不朽被原始人視為是很自然的事情。死亡的觀念只是后來才被人們勉強地接受。”[4]原始初民本能中蘊含著強烈的生命意識,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對死亡抱著拒絕與否定,對生命的復活與循環(huán)抱著強烈的信仰,他們將延續(xù)生命的希望寄托與變形神話,以此來戰(zhàn)勝死亡帶給人的恐懼。
尚處于原始階段的原始初民較之現(xiàn)代人更必須常常去赤裸的面對嚴酷的現(xiàn)實,尤其是死亡。根據考古發(fā)現(xiàn),從舊石器晚期開始,人類已經萌發(fā)了很強的生命意識,求生的欲望已經很強烈,然而那時生存環(huán)境的極度惡劣使得原始人類時刻面對著死亡的威脅,因此他們形成了對死的恐懼與生的渴望的強烈心理。死亡是一種令人驚異和恐懼的特殊現(xiàn)象,對于原始初民來講,死亡是一種全新而未知的領域,他們對這一未知的神秘現(xiàn)象感到既困惑又恐懼,在他們簡單而又單純的意識形態(tài)里,就用變形來代替生命終結這一事實,用變形的途徑來回避著死亡。在這里,生命成為了流動和循環(huán)的,是生生不息源源不止的,死亡是被拒絕的。
《北山經》云:“又北二百里,曰發(fā)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wèi),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wèi)。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這種悲劇性的死亡,表現(xiàn)了初民生活的艱難和精神的頑強,也使得原始初民以變形的方式來更換現(xiàn)實中脆弱的生命,使其延續(xù)下去。勇敢而執(zhí)著的女娃選擇化為精衛(wèi)鳥從而使她的生命和使命以另一種方式得以延續(xù),對原始初民而言這是一種補償性的滿足。這種主動的選擇象征著一種升華,體現(xiàn)了初民與命運抗爭的力量。
《中山經》云:“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為牙瑤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買如菟丘,服之媚于人。” 美麗的瑤姬年輕貌美卻早亡,是非所愿而死,初民便將她化為“瑤草”,拒絕死亡,以另一種形式延續(xù)她美麗的生命。宇宙萬物充滿永恒的生命力,人與物之間,不用考慮人的生、物的死,因為死亡已被否定,被拒絕,現(xiàn)實生活中的生死無非是生命的轉化或升華。這一人類最初的生命意識,是原始初民生存的精神支柱,也是人類最早“戰(zhàn)勝”自然的思想武器。
此外,從這三個基本的觀念中還可以拆分衍化出其他很多的亞類,如生命循環(huán)意識、生命復活意識、生命永恒意識等等。這些基本的原始生命觀都是原始初民在面對生與死這個永恒的命題時,觀照自身和宇宙萬物所做出的回答,體現(xiàn)著人類在童年時期最質樸最單純的見解。
三、結語
原始初民們對生命長駐的追求,對死亡的抵制,達到無比的追求,因此能將靜止的生命力變?yōu)榱鲃拥纳Γ瑥亩a生了多姿多彩的變形神話,也帶來了《山海經》中美麗而奇特的神話世界。變形神話不但解釋了生命與死亡的問題,表達了原始初民在這方面的感受,而且發(fā)揮了原始智慧,以充分自由的想象將他們的感受、體認和需要用象征的方式表達出來,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從他們瑰麗神奇的想象中窺見他們的生命意識。
[1]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104頁
[2]斯蒂?湯普森.民俗、神話和傳說標準大辭典.鄭海等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162頁
[3]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107頁
[4]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