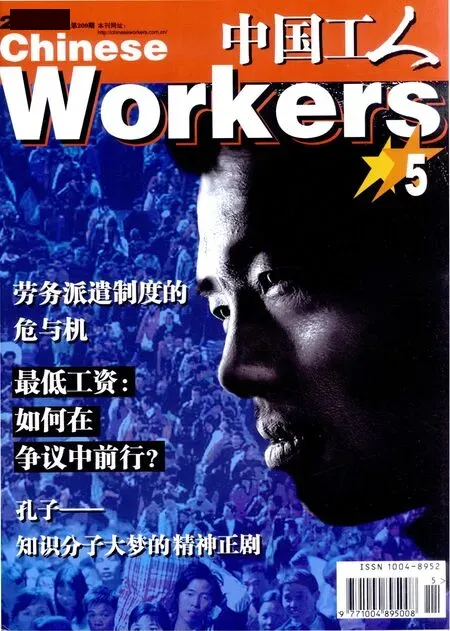打工詩歌中的打工者形象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譚黎
打工詩歌中的打工者形象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譚黎

自從20世紀80年代深圳經濟特區開始大批內地招工以來,外來務工者已經成為深圳、廣州等地的常駐人口。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在工作艱辛、條件惡劣的打工生活中,用文字記錄打工者的生活,寫成了反映打工者“生存狀態、情感世界和理想追求”的詩歌。隨著這樣的詩歌被大量創作和刊登,人們開始將它們統稱為“打工詩歌”。
打工詩歌與打工者這一特殊群體的身份和處境緊密相聯,因而具有特殊的社會意義。打工者在戶籍制度中屬于農民身份,但他們離開經濟日益凋敝的農村,來到工業日益繁榮的城市,成為車間、流水線、城市角落的臨時雇工。他們屬于城市的暫時居住者,沒有城市公民的正式身份,無法享受城市市民的社會保障待遇,而且被城市當做異己者對待,遭到歧視和排斥。但是,他們的勞動滿足了城市工業化擴張的需要。他們在工廠、工地和各種服務行業承受著長時間或高強度的勞動,僅獲得微薄的薪金。無數打工者懷著對城市文明的憧憬而來,在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之后,始終無法獲得正式的城市身份,最終只能回到貧瘠的故鄉。甚至,許多打工者在高風險的生產過程中失去了自己的肢體,造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身體殘障和心靈創傷。數量龐大的打工者為中國的經濟騰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他們的處境卻只能被概括為:身心俱傷,進退兩難。
打工詩歌就是打工者在痛苦的生活處境之中,以特殊的形式發出的聲音。打工者歷來屬于“沉默”的底層群體,他們沒有能力講述自己的生存處境,也難以獲得其他階層的傾聽和理解。他們既沒有政治話語權,無法在政策決策中表達自己的權利要求;也沒有經濟實力,無法通過市場影響力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也沒有文化話語權,不能像學者、評論家那樣在輿論話語中占據一席之地。當所有主流的話語渠道幾乎都對打工者關閉之后,他們把壓抑的痛苦、困惑、迷茫、憤怒進行提煉,轉化成半熟的詩句,用自己的微弱聲音引起了主流媒體的注意,使得被遮蔽的底層現實得到了部分呈現。
話語是建構自我的方式之一。打工詩歌中打工者建構的自我,既有生產過程中的自我形象:麻木、被動、機械、標準化,也有在城市和鄉村、農業和工業之間分離的自我,另外也包括對于自我的肯定。總體來說,打工詩歌中建構的打工者形象大致有以下幾種:
生產中受支配的主體
工作是打工者生活的核心內容,因此,很多打工詩歌的主題都是以描寫打工者的生產過程為主,如下面一首《焊花落下 焊花落下》,描述了打工者在機械生產過程中的感受:

“用幾萬噸的力砸斷他們的骨頭/用幾萬噸的力焊接他們的靈魂/焊花落下/焊花落下”(程鵬:《焊花落下 焊花落下》)
這一段描寫生產過程,“幾萬噸的力”非常夸張地表現出巨大而強悍的機械力量,這其實是工人在生產過程中要承受和面對的沖擊。在巨大的壓力下,工人仿佛鋼鐵一樣被“砸斷”和“焊接”,處于受人擺布、無法自主的狀態。在現代化的工廠生產過程中,工人在感受上似乎與機械融為一體了,感到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在受這巨力的支配。
下面一首《在電子廠》,側重的是打工者在流水線上統一化和標準化的形象:
“被剪裁的草木,整齊地站在電子廠間/白色工衣裹著她們的青春,姓名,美貌/被流水剪裁過后動作,神態,眼神……”(鄭小瓊:《在電子廠》)
下面描述的是被操縱的、麻木的主體:
“可是我已經麻木。一如被操作了命運的鐵/切割、鍛打、彎曲或者扭直/它不懂得什么是疼痛/也不懂得什么是幸福/“哧哧”的火花在凌晨漸次熄滅/又一個日子被打磨、煅燒”(孫海濤:《鐵》)
以下這一首則展現的是打工者在現代工廠的嚴密監控下的心理活動:
“在監控器下工作的心理活動:總感覺有雙眼睛/在背后偷偷地看/她的脊梁陣陣發涼……連打哈欠伸懶腰/也得小心翼翼……懷疑廁所里/也裝上了暗處的眼睛”(張守剛:《在監控器下上班》)
總的來說,在生產情境中的打工者,是在鋼鐵和機械的環境中備感壓迫的個體,也是經過流水線標準化和統一化的個體,還是受到操縱和監控、無法自主的個體。在現代的技術化生產過程中,工人受到機械的支配,成為機械的附庸;工廠對于生產環節的嚴密控制,又使工人無論在身體還是大腦都失去自由,一種受操縱、被監視的感受逐漸由外向內深入到工人的意識,給他們的精神也戴上了枷鎖。在生產過程中,工人是一種受奴役的狀態。
城鄉分離的主體認同
打工者既不能真正地進入城市,又不能回到鄉村;既帶著對城市文明的憧憬,又揮不去對鄉村的依戀;既要在城市工作,又要回鄉村生活。他們在城鄉二者之間進退兩難,這種矛盾又分裂的主體,是他們的真實狀況。
下面這首詩抒發的是打工者想要融入城市而不能的情感:
“南方啊/我們多想敞開真誠的胸懷把你擁抱/但為什么我們總是如履薄冰/若踩針尖/蒼白的臉龐面黃肌瘦布滿憂愁/我們是一群群候鳥/被一個個城市不住驅趕無處棲身”(許強:《為幾千萬打工者立碑》)
面對城市,打工者始終是無法融入的外來分子,而且自己的停留也岌岌可危:
“城市永遠是別人的城市/打工者沒有任何發言權/稍不留意,就會被當做皮球/踢出生活的主題之外”(何永飛:《又漲房租》)
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打工者的身體和靈魂是分裂的,他們的身體付出難以改變他們的靈魂認同:
“身體是城市的身體/靈魂是鄉下的靈魂/我空成兩片蚌殼/向城市敞開胸懷/我的青春、血肉/一生中的精華部分/沒有變成黑土地上的一顆土/已經成了萬丈高樓里的一粒沙”(屏子:《在城市里嗑著瓜子》)
“漂流,在鄉村與城市之間漂流/不屬于鄉村也不屬于城市/打工永遠沒有安全感歸屬感/永遠望著水泥建筑流兮盼兮/……這個城市沒有記住我的名字”(黃海:《這個城市沒有記住我的名字》)
打工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與身份相關聯的社會遭遇會給他們帶來什么樣的生存感受?
“在東莞,我用了九年時間/才漸漸地把自己遺忘/農民工?打工仔?都不必/太過認真。在任何一張陌生/或熟悉的面孔面前/我只是一個干活拿錢的人”(李福登:《這些年,我一直把看到當成聽見》)
為何打工者最終要選擇“把自己遺忘”?打工者遺忘的是“農民工”、“打工仔”這種身份,這種身份只帶給他們負面感受,降低了他們對這種身份的認同。為了求得內心平衡,他們刻意忽視了“農民”的身份。在城鄉的身份分裂之中,打工者對自己的身份缺少一個確定的認同,他們要么處于持續的掙扎和焦慮之中,要么只能選擇逃避其中之一。
作為弱勢群體的主體
打工者在城市中是弱勢群體,他們的權益沒有得到有效保障。
在城市,打工者為了生存而出賣自己的勞力,他們因此而得不到尊重:
“我已經如同一枚過河的卒子,沒有退路/再苦再累,付出再慘重的代價,也必須從這里打撈/活命的銀兩……很多時候,僅僅為了一碗飯和一鋪床,就不得不考慮/去一個地方接受人的任意驅使和訓斥/正因如此,在某些人的眼里我們并不比牲口高貴”(劉大程,《南方行吟》)
打工者也在各種細枝末節受到歧視和區別對待:
“用幾千萬人的身體將大廈筑起/用幾千萬人的雙手將城市建設/你要進入大廈/請你走貨梯”(程鵬:《焊花落下焊花落下》)
他們在生活中時常要面對壓迫和不公,這些遭遇引發了他們無休止的追問。
“在別人的城市中/為什么我們的心靈/只能戴著腳鐐手銬/在砧板上和熱鍋中/一點點耗盡自己的青春……/一雙雙筷箸決定了多少打工人的命運”(許強:《為幾千萬打工者立碑》)
他們的自尊因此變得極低:
“在城市里我是最卑微的野草”((唐以洪:《春節與一盤河粉相聚》)
他們也對于自己的處境進行思考,也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受到嚴重的剝削,受到城市、老板、工廠、房屋的剝奪:
“一百來斤身體,大部分流進別人腰包/……到頭來,底層的一個個我一個個你一個個他依舊穿得只剩下自己身體/而巨大的城市從一個個出租者身體上抽稅一樣抽走大量夢,淚,汗,命”(張紹民:《租房》)

打工者的弱勢地位在打工詩歌中得到了呈現,打工者通過自身的認識和思考,清楚他們的弱勢地位。整個城市都在剝削他們的勞動價值,他們在城市中也得不到絲毫尊重,但他們為了生存只能留在這里,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他們無力改變這種狀況,只能通過詩歌這種形式發出自己的微弱聲音。
自我肯定的主體:尋求外界的理解和認同
打工者雖然承受著生存的重負和外界的歧視,但他們也在不斷尋求對自我的肯定,建構自己的積極自我。
首先,打工者對自己的勞動意義具有非常積極的說明。
城市的高度我無法測量/兄弟,我只記得/你為這個城市的建設/搬運過3298噸鋼筋(陳忠村:《短夜021:城市的高度我無法測量》)
我們是在山城不可缺少的/一項運輸工具……我們在心底特別充滿信心/我們挑著重擔可以走一樓/也可以上五樓/還可以爬九樓/甚至更高更遠……(彭盆雨:《重慶扁擔》)
這也是我的北京/這里的繁榮/也有我的一份(郁金:《今夜,北京的冷》)
其次,打工者對自己的勞動動機相當肯定,甚至是自豪。
我們安慰自己/我們一點也不怨言/為家人勞作是最光榮的事情(彭盆雨:《重慶扁擔》)
當患者的病情允許條件下,可將患者移動至半坐位,該姿勢的呼吸效果更佳。同時短時間的肢體運動也是配合呼吸鍛煉的重要方式。
把這個月的工資/還有年終的獎金/一起寄回給家里/就像寄回去了一個春天/從此家里不再寒冷了/阿爸阿媽笑容里/也就有了溫暖的陽光/放學的小妹穿上新衣/盼著哥哥回來過年/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寒風乍起的日子里/打工仔在郵局/排隊郵寄春天(薛廣明:《郵寄春天》)
打工者的自我肯定,不僅可以增加他們對自我的認同,增強他們繼續承擔這種生活重負的信念和決心,而且也有助于增進外界對他們的理解。他們強調了一種吃苦耐勞、忍辱負重的精神,這是比干活拿錢更高的境界。
反思的主體:打工詩人的特殊角色
打工詩人作為打工者的一部分,他們代表了打工者的智力和文化水平的佼佼者,對打工者群體自身的生存處境進行思考。作為打工群體的一員,他們經歷著所有打工者的重負和磨難,與他們有著經歷和情感上的共鳴。同時,他們又超越了普通打工者,產生了對于群體處境的更多反思。他們的角色具有多重意涵。
作為反思者
打工者之中不乏知識分子,他們在經受生活的磨難之余,不免對打工者的群體處境進行思考。
他們具有對于群體處境的宏觀思考:
“農民問題/出門問題/坐火車問題/買票問題/擠車問題//農民問題/吃飯問題/干活問題/干什么的問題/到哪里干的問題/干誰的問題//農民問題/稅收問題/子女上學問題/父母下葬問題/蓋房穿衣問題/養豬養雞問題//農民問題/怎樣不做一個農民的問題/怎樣做回一個農民的問題/農民問題/我的問題”(謝湘南:《農民問題》)
他們也表現出對工廠非人性化生產過程的反思:
“向左是螺絲,零件,工具/菜刀,圖紙,機器,向右是人性,自然/社會,經濟學,政治。”(鄭小瓊:《在鐵具上》)
打工詩人的反思超越個體的命運,涉及對流水線生產非人性化的反思,對現代工廠無處不在的監視制度的反思,對城鄉不平等的反思,對資本家剝削和壓榨的反思。他們是代表打工者對于自己命運進行主動思考的那部分人。

作為良知和道德的守護者
打工詩人也自覺地在詩歌中表現對于良知的呼喚、對于道德的堅守。打工者大多較為年輕,不僅心智不夠成熟堅定,而且還面臨城市的種種誘惑。因此,在艱難的生存處境中,打工者失足或走上歧途的也不在少數。打工詩人一方面以悲憫之心看待他們,同情他們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如此,另一方面也鼓勵工人們用積極進取的心態面對生活的重負。
打工詩人用銳利的語言描寫打工者的不道德行為:
“他有著失敗的愛情/漂亮的湖南小妞/拋下他走進了/一個有錢老頭的懷里/南下五年 打工五年/沒有謀到一官半職/在工廠做車位工/每天穿針引線/卻將針扎進自己心尖上/那個痛啊/是湖南小妞拋棄他的那種……”(張守剛:《和工友聊天》)
這些行為屢屢常見,詩人在銳利的言詞底下,埋藏的是對同伴不幸命運的關懷和同情。
詩人也號召打工者們努力進取,改變自己的命運:
兄弟們,姐妹們,我知道你們心里苦,需要宣泄/可你們是否想過:該怎樣在艱苦的打工生涯中/鍛打自己,成長自己,從而改變自己的打工命運/才不至于荒廢了青春年華?盡管事實上許多事情很難/很難,但又怎能沉溺于悲觀的泥淖?有誰會來扶你啊(劉大程:《南方行吟》)
對于打工詩歌的功能,打工詩人鄭小瓊在一次發言中說:“用詩歌建立內心的秩序,保持著一種人性的善良與正義;用詩句來抵抗權力與資本世界帶給內心的損傷,保留著人類對內心的理想與尊嚴,更加熱愛我們內心的本身。”
作為反抗者
打工詩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并不主要為了追求審美價值,它也用于發出正義的呼喊。打工詩人也在詩歌中包含著對于現實不公的反抗。
以下這首詩,就是打工詩人們集體為受害工友劉晃棋所作,為他申討不義而吶喊:
哦兄弟 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這樣畏懼膽怯/我們不是現代包身工/我們不是奴隸/為什么不說一聲“不”/為什么不把抗爭的拳頭高高舉起?!(羅德遠:《劉晃棋,我的打工兄弟》)
打工詩歌的聲音雖然微弱,但是透露出了工人生產之中爆發的反抗性。在打工者普遍失語的現實中,這一點微弱的聲音至少能夠反映工人的心聲。
打工詩人的反思對象,既包括造成群體處境的外部社會環境,也包括打工者自身的問題和缺點。他們將自己的反思化為詩句向整個社會發問,一方面要喚起社會對打工者的關注,進而帶來群體處境改善的可能性;一方面可以鼓勵和引導更多的工友,鼓勵他們自身保持積極上進的進取精神。在精神氣質上,打工詩人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他們勇于揭露現實生活中的不公和丑惡;他們也是具有悲憫之心的人,對于工友的悲慘遭遇和失足墮落都懷有深深的關切同情;他們也必然是敏感之人,對于周遭現實擁有超過常人的洞察力,善于捕捉其中的關鍵細節,看到社會規則的潛流。他們是底層的文化精英,是底層民眾的代言者。

打工詩歌自出現以來,就受到工人讀者的熱烈歡迎。一份報紙剛出來,馬上就被工友們搶購一空。這一方面表現了工人們渴望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化,渴望這種精神上的滋養和交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工人進行自我話語表述的強烈需求。
打工詩歌作為一種蘊含豐富打工經驗和打工感受的文學形式,為關注打工者的人們提供了一種“健全的主體感受”,讓人們可以“探測到來自底層的原生態的聲音”。他們的經歷記錄,構成了中國社會轉型期痛苦記憶的一部分。他們理應獲得社會的關注和理解,以及政策措施帶來的切實的處境改善。但是詩歌所能產生的社會效應和反抗力量仍然有限,要改變現實,仍然需要將話語付諸行動,去爭取切實的改善。對于打工詩人來說,當他們為群體命運呼吁和吶喊時,他們是在呼喚社會整體層面的正義和公平,呼喚對于當下現實的改進,他們此時就具有了一種新的身份:社會公民。
欄目主持:胡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