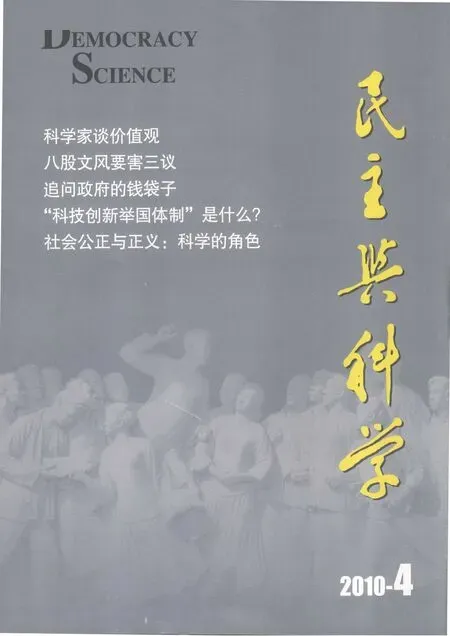社會公正與正義:科學的角色
■李大光
社會公正與正義:科學的角色
■李大光
2010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會見中外記者并答記者問時說:“我們國家的發展不僅是要搞好經濟建設,而且要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和自由的發展,這三者不可偏廢。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其根本目的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而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我認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我們無法推測溫總理所說的“太陽”是什么,但是,至少我們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將社會公平和正義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中國歷史上似乎還不多。談論社會正義和公正,一定是有不公正和非正義的存在。在科學技術為王的時代,我們的耳邊似乎響起了埃及諺語:“我們走得太快,讓我們停下來等待靈魂。”我們的靈魂是什么?是理智,是審視力,是反抗非正義的能力。
一、GDP還是GHP:社會富裕還是社會正義?
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馬克思都對“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有很多的思考和觀點。我們大概可以將這些觀點歸納為:1、非社會意義上的正義觀:個人倫理角度、宗教倫理角度的正義觀;2、泛正義觀:人際關系的正義;群體關系的正義;種族關系的正義;國家關系的正義;社會之間的正義;公民和族群關系正義;3、社會正義觀:政治生活的政治正義;經濟分配關系的經濟正義;教育與文化生活的教育正義;社會生活的社會正義(指社會工作、社會服務和社會福利等)。
以上角度的正義觀是在傳統的社會發展形態中討論的正義觀。但是,當社會發展形態進入到信息時代,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模式受到經濟關系的影響逐漸變小,而信息逐步占據人們生活形態主流地位的時候,我們應該增加第四種正義觀,即“信息社會正義觀”。“信息社會正義觀”指的是在網絡高度發達,某一個群體的行為模式由信息支配的時候,享受信息、理解信息和傳播信息就構成了獲得信息社會的正義的權利。當這種權利受到損害,或者消費信息失衡的時候,社會的震蕩同樣會產生與經濟分配不合理所產生的動蕩同樣的效應。獲得完整和真實的信息與獲得經濟正當所得一樣,具有同樣的幸福。
2008年3月,與中國接壤的不丹宣布實行了100多年的君主立憲制廢除,實行民主選舉制。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正式宣布將在2008年退位,產生第一個民選政府。不丹報紙援引國王的話報道說:“君主制度可能已經不再適合這個國家,現在可能是最佳的立憲時機,讓本國擁有一個最能確保未來繁榮安寧的民主政府。”辛格國王面對著對他無限敬仰的臣民說:“一個優秀的制度比國王更重要。”
不丹民選制度改革固然引人矚目,但是,更引人注意的是辛格國王的“幸福指數”。在辛格國王提出他自己的幸福指數之前,已經有很多學者和研究機構提出幸福指數的定義和指標。但是,多數是西方國家學者。很多人認為,只有在經濟發達國家才能論及幸福問題。從這個角度講,辛格國王的幸福指數值得研究。
幸福指數除了生存狀況滿意度和情緒愉悅度這些一般基本指數以外,更重要的是個體與社會的和諧程度。包括對人際交往的滿意程度、身份認同,以及個人幸福與社會和城市發展之間的關系。辛格國王提出的幸福指數包括:政府善政;社會文化保存;環境保護。其中政府善政指的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任何人都有權利表達自己的意愿,政府的所有事務都公開,任何人的意愿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為此,這位“平民君主”經常與百姓在一起交談,了解他們的想法。百姓甚至可以在他經常經過的地方將寫有自己的意見的紙條壓在石頭下,這位英俊的國王會隨時拾起這些紙條帶回宮內仔細閱讀。
辛格國王的言行使得我們不得不思考,長期以來,人們都在議論的在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問題。大多數人都會說,發展中國家不適合民主制度。這種論斷似乎成了定論。筆者在與歐洲和美國學者談論科學體制問題的時候,他們似乎都詢問這個問題。這不是一個定論,而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就像在改革開放之初,多數學者不都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實行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不可行嗎?當一個家庭由過去的窮困變得富裕,幸福是否就已經獲得了呢?我們想象一下,當你在一個家里,吃飯的時候你被招呼到桌邊,但是,在談論家庭下月的支出和消費計劃的時候,你被支開。你有幸福感嗎?
前幾日,媒體宣布,中國網民人數已經達到3.4億,中國已經進入到信息時代的前夜。獲得信息和享有獲得信息的權利已經不是少數人的專利。獲得信息已經成為公眾享受幸福的主要指標。任何阻擋公眾享受這種幸福的做法都有悖民主的準則。
二、“技術為王”時代的朦朧
幾乎是在不丹國王宣布實行民主改革的同時,2008年4月22日的《科技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重要文章“公眾參與規劃環評難在哪?”。這是中國層次最高的科技傳統媒體少有的對科學議題的質疑。文章報道了整個環評決策過程的尷尬一幕:“2006年6月,《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征求意見稿)》成型時共有46條1萬余字。之后,在部門利益的博弈中,幾經修改,如今已經‘面目全非’:具體的規定成了抽象的概念,原有的棱角被消磨殆盡,條例的可操作性已經很差。尤其是有關公眾參與的內容,在最早的草稿時一個專門的篇章,現在只剩下照搬《環評法》的原文。而按照慣例,出臺條例就是為了進一步細化上位法。”“而有知情人透漏,這一章之所以被刪除,歸根結底是有關部門怕惹來公眾這個‘麻煩’”。有關部門的“怕麻煩”背后其實是無視公眾對信息的享有權。在政府部門和科學家團體的共同操作下,信息社會的正義被無情的毀掉了。
2009年11月底,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教授及其同事的兩個轉基因水稻品種獲得農業部頒發安全證書。華中農業大學所獲得的是“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轉基因抗蟲水稻汕優63”在湖北省生產應用的安全證書,有效期為五年,起始日期均為2009年8月17日。但兩個多月后的10月22日,該辦公室才在其主辦的中國生物安全網中透露了上述信息。這個網站平時極少更新,轉基因水稻的信息又與一堆轉基因棉花品種混雜在“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之中,當然很難引起媒體和公眾的注意。直到11月底,媒體才從一些專家那里獲知消息。這個決定引起了自從建國以來科學問題的最大范圍的討論。2010年3月初,在11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120位學者聯名簽署公開信,要求農業部撤銷轉基因作物的安全證書。這封公開信認為:“批準轉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商業化意味著中國將成為第一個種植轉基因主糧作物的國家,將威脅國家安全。”此后,經濟學家郎咸平等社會學者和人文學者對轉基因農作物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引起了更大范圍的討論。《國際先驅導報》的說法帶來了更大范圍的恐慌:“中國成為國外轉基因糧的生死試驗場”,“民族的噩夢”,“已經兩個月了,有關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各種擔憂仍然在網絡上持續發酵,并逐漸蔓延形成一種恐慌。”
在這場越來越激烈的爭論中,除了少數農業專家以外,社會學者和人文學者占據了反對聲音主流。轉基因水稻專家不斷告誡說轉基因農作物沒有問題,是安全的。但是,為何擔憂越演越烈?關鍵不在于轉基因農作物的是否安全,而是公眾的知情權是否得到了應有的尊重。如果我們說,專制導致社會正義的喪失,我們似乎沒有異議,但是,如果我們說,一貫被認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科學家在傷害社會正義,我們是猶豫的。事實是,我們從這件事上看到了什么呢?
同樣,垃圾焚燒也在舉步維艱。在全國100多個垃圾焚燒廠的建設過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居民的阻攔。使得目前的垃圾焚燒廠只有10多個建成投產。公眾對于二噁英的恐懼勝過垃圾圍城的恐懼。政府的環境整體建設與公眾的利益與對環境技術的理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類似的科學事件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在觀察每個事件的產生與發生過程中,我們幾乎都可以發現,科學家群體與公眾之間的矛盾隨處可見。我們似乎感到科學家團體害怕與公眾接觸和交流。但是,說到底,是科學家害怕公眾理解。這個理解指的不是對各種決策的理解,而是對科學原理的理解和技術核心的理解。害怕公眾理解的另一層涵義是,科學家團體自己讓公眾理解的能力具有某種程度的擔憂。科學家的擔憂導致了公眾的擔憂,盡管兩種擔憂是完全不同的。
三、我們離社會正義還有多遠?
中國與西方國家相比,最顯著的落后不是科學技術研究,而是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作用的研究。我們的社會學,尤其是科學技術社會學十分落后。我們的科學傳播或者科學普及僅僅停留在讓公眾相信科學這種淺層次的水平上。在20世紀后半葉到70年代,人們對已經進行了長達幾個世紀的科學技術傳播活動進行了思考。一般認為,人們一直是采用線性模式進行傳播活動的。線性模式認為傳播的源頭是科學家,傳播的末端就是公眾。這個階段將科學家描述成真正科學知識的生產者,然后要把知識“翻譯”成通俗易懂的語言,以便向更多的公眾傳播。而“公眾”只是被動的接受者和沒有多少權利、整齊劃一的群體。這種模式基于這樣一種認識:科學家是不同于一般人的專家,他們的知識是理性的、更為高級的,而公眾的知識僅僅是感性的,是可以忽略的。因此,科學知識的傳播是由科學家向公眾單向流動的過程,呈現出線性的模式。這種線性模式最大的問題是硬性的教育導向的思維方式,將普通公眾想象為什么都不懂的空桶,而科學家的任務就是向這個空桶里放東西。科學家認為,只要這個空桶里放的東西和他們自己腦子里的東西是一樣的,那么,公眾的思維就會是理性的,是熱愛科學的,公眾必定會支持科學事業,公眾理解科學的目的就達到了。但是,這種線性模式所導致的結果卻與科學家希望獲得的結果相反。公眾對科學的權威性懷疑增強,對科學家所做的科學研究更加不理解,面對三哩島事件、瘋牛病事件、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件以及轉基因實驗等各種科學家活動更加迷惘,對科學的未來充滿懷疑。而公眾拒絕對自己進行的聽不懂的科學知識灌輸的行為,科學家認為是他們缺乏信息,從而導致公眾對科學的敬而遠之。這種教育導向的傳播模式最大的弊端是傳播的主體忽略了人的社會性,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你的科學知識沒有到達他們的大腦之前,他們由于自己生活的環境和特定文化的影響,已經對自然和客觀事物有了自己的認識和固定的看法。復雜的知識使他們認為科學果然很復雜,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從而“重構了他們與科學之間的距離”。科學傳播宣告失敗。
社會正義主要依靠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任何一個社會公民群體都不能僅僅依靠賜予獲得自己的利益。這是因為無人愿意出讓自己的利益。在科學技術發達和市場化的今天,科學家已經變成了利益集團,讓利益集團出讓自己的利益更是困難的事情。那么,我們的公民社會發展到了哪一種程度呢?
筆者在過去的幾年內,對中國公眾對自身權利的認識進行了非概率意義上的定性調查。調查點考慮到經濟、教育和文化等變量。在對預選調查點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教育、文化、民族等人口特征充分的研究分析基礎上,在全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各選擇一個有經濟發展水平代表性的省,在每個省選擇城區、城鄉結合部、農村(兼顧民族特征)的座談調查點。從2007年1月到2008年3月期間,共實施了11組座談,每組約15人參加。調查課題組對參加座談討論的人員的性別比例、教育程度和年齡等人員構成狀況進行了必要的控制。參與座談會的人員總共153人(其中少數民族28人)。江蘇省:共42人(南京玄武區16人;南京雨花區14人;揚中縣三茅鎮12人);山西省:共46人(太原市干峰街道:15人;太原市小店街道14人;太原市陽曲縣17人);云南省:共65人(昆明市虹山中路社區:13人;昆明市龍泉街道:13人;紅河州開遠縣灰土寨:14人;紅河州甲寅鄉(彝族村寨):兩組共25人。
定性調查主要以焦點群體座談會(focus group)方式進行。引導話題采用“半介入式”的方法,將大家討論的范圍限制在預先設定的話題之內。調查人員將大家討論的內容進行概括和歸納,得出趨勢性的結果,從而更深入的了解被訪者對有關問題的看法。
1.公民支持科學技術發展的思想基礎主要是愛國意識
大多數人表示,科學技術,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他們一概支持,盡管他們起初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區別并不十分清楚。基礎研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甚至永遠也不會直接對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直接的促進作用。而應用研究或者技術開發卻有可能使他們直接受益。作為納稅人,我們的公民卻表達了他們無論什么樣的科學都堅決支持的觀點。甚至有人認為,即使百姓勒緊褲腰帶也要支持科學研究。大家認為,作為一個世界上的大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都應該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盡管被訪者對科學技術形成的態度基礎并非完全是理性的,但是,愛國主義在科學態度上的體現應該說是中國公民的一個重要特征。
2.公民了解并珍惜自己參與科學決策的權利
在調查中,我們清晰的感覺到我國公民明確的知道自己擁有知情權和參與決策的權利。這種權利的意識和參與的意識不受地域、經濟狀況和教育水平的限制。這與學界在此之前認為我國公民參與意識不強的看法差距很大。近些年來,從薩斯、圓明園防滲膜事件、廈門P X事件等一系列的科學技術事件中,我們已經看出,在技術或者工程事件與公民利益發生沖突以后,公民要求參與的意識非常強。那種認為公民科學素養水平不高,沒有能力參與的認識是錯誤的。首先,尊重公民在科學決策中的權利與他們參與決策的能力不是一回事。科學在促進社會的文明和進步過程中承載著重要的責任和義務,沒有真正的民主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科學家和政府的義務就是要啟蒙公民的知情權意識,并且盡可能的動員公民參與決策。公民參與決策的意義還在于,公民所擁有的地方性知識或者經驗對于科學決策具有重要的意義。另外,公民對某些問題的擔憂,比如環境問題、宜居問題、宗教問題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問題,都是在科學決策中應該慎重考慮的議題。但是,在科學家團體和政府層面上,這些問題很容易被忽略。因此,公民參與是十分重要的過程。
3.公民參與決策的思想基礎是公民意識
調查中,我們可以明確地感覺到公民具有強烈的參與決策的意識,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參與決策是公民的權利。但是,公民權利意識的思想基礎是什么呢?他們為什么認為自己具有參與決策的權利呢?
為了深入的了解公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觀點,我們設計了幾個引導話題:(1)因為我是納稅人,科學研究用的是納稅人的錢;(2)我是國家的公民;(3)科學研究結果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4)科學家的工作也需要公民的監督。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參與者十分積極,發言踴躍。有80%至90%的人認為“自己是國家公民,所以,擁有參與決策的權利”;大約同樣比例的人也同時贊同“科學研究結果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僅有極少數的幾個人認為自己是納稅人,所以擁有參與決策的權利的看法。但是,沒有人認為“科學家的工作也需要公民的監督”。他們認為公民不僅無權監督,而且實際上也無法監督。
從這個調查結果看出,長期以來的關于主人翁的教育和輿論宣傳使得公民的國家主人意識比較強,這種意識對他們的社會權利意識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納稅人的責任與義務對于參與決策意識中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4.公民參與決策的主要目的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
為了在討論中得到更多的結果,關于公民參與決策的目的,我們設計的引導話題有:“這個科學研究項目花了多少錢,這些錢都是怎么使用的”;“研究項目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么好處,是否有副作用”;“了解這個領域的科學知識”以及“科學家是怎么工作的”。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更關心的是“研究項目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么好處,是否有副作用”。從這個調查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公民更關心的是科學研究的結果以及作用。
這個結果讓我們思考的是,作為納稅人的普通公民,他們并不太關心他們的錢是被如何使用的。這個結果與自己權利認識的追問結果相關,很少人認為:“因為我是納稅人,科學研究用的是納稅人的錢”,所以,他們才認為自己有權利參加科學決策聽證會。絕大多數人認為“我是國家的公民”和“科學研究結果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所以,他們才有權參加科學決策的聽證會。更沒有人同意:“科學家的工作也需要公民的監督”的觀點。看來,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發展形勢下,公民參與是在初級階段狀態下的參與,即,建立在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真正的制度建設或者決策建設意義上的參與。
5.環境問題的認識更多地來自自身感受
對于環境問題,從討論中明確感受到,我國公民對環境的認識大多數來自自身的感受。南京公民認為,空氣污染最嚴重,這是因為他們看到自己的鐵窗被腐蝕。昆明人認為污染最嚴重的是水系污染,那是因為滇池的水與大約20年前相比,相差很多。至于全球變暖的問題,他們關心的程度似乎并不如他們感受到的污染問題嚴重。我國公民對于環境問題的認識也是與自身利益相關的。
山西的污染問題在全國是比較嚴重的。但是參加座談會的公民雖然知道他們的環境污染嚴重,但是,與經濟發展相比,他們更注重的是后者。如果經濟發展,他們可能對污染的問題是能夠容忍的,或者,他們至少認為并不是那么嚴重。從這個角度上講,對環境問題的監督和控制,以及通過法律和政策減緩環境的污染或者改善環境問題,主要還是要靠政府。這是中國治理環境問題方面,在文化層面上必須認清的問題。
我國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還是處于感性的、自我判斷階段。他們對信息的享有權和理解能力都處于很低的水平。從他們的陳述中可以看出,大多數人對科學技術的理解還是處于原始的愛國主義宣傳所形成的認識基礎上。我們的公民社會遠遠沒有成熟。
四、結 論
社會正義的討論從古希臘時代直到今日都是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重要話題。但是,社會正義由權貴與公眾的經濟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和正義性的討論,進入到今天在信息社會的信息享有權的爭論。當權者或者強勢團體對信息的控制和封鎖必定導致社會公正性的喪失與失衡。
科學技術發達的今天,在中國對于科學有利的主體思想控制語境中,對“技術為王”時代的到來不是在信息共享與公眾理解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發展,無論是政府還是科學家團體均采取自我決策,都處于自我實行的機制中。這種機制預設思想是:科學技術是為公眾謀利益的,政府和科學家是為公眾謀幸福的,公眾自然不必了解其過程甚至其不確定性。但是,殊不知,公眾的頭腦中不是空桶,沒有信息進入他們的頭腦,他們就從自己生活的社會環境所形成的理解模式中對科學技術進行理解。更危險的是,影響他們對科學技術理解的還有政治影響因素和各種非科學的因素。
在一系列的中國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理解的定性調查中,公眾呈現出對科學技術的理解從感性認識和淺層次認識的程度。我們的公眾對科學技術的態度還是處于輿論宣傳所形成的理解模式中。中國的公民社會遠未形成。沒有獨立和成熟思維能力的公民社會,社會的正義和公正就不能實現。
(作者單位: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
book=46,ebook=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