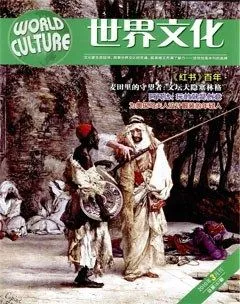威廉與榮格的東西文化觀
《紀(jì)念理查德·威廉》是瑞士心理學(xué)家榮格在德國漢學(xué)家理查·威廉逝世后而寫的一篇悼詞,既高度評價了威廉一生的漢學(xué)成就和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xiàn),更主要的是借此闡述了自己在中西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共創(chuàng)人類大同文化的觀點。這些觀點至今仍具有積極而深遠(yuǎn)的文化意義。
榮格何許人也?理查德·威廉又何許人也?
其實他們都是西方人中敢于面向東方、向東方學(xué)習(xí),并將接受的東方文化向西方輸入的杰出代表。他們不以自己的專業(yè)為束縛,而是從專業(yè)拓展的角度出發(fā),博覽東西文化,以關(guān)注歷史的發(fā)展和人類的命運(yùn)為己任,架設(shè)起東西方文化交流、借鑒和促進(jìn)相互滲透的橋梁。可以這樣說,他們是20世紀(jì)初期成就卓著的中國文化研究者和中學(xué)西漸的傳播者。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1875-1961)是瑞士著名心理學(xué)家、精神分析學(xué)家,是分析心理學(xué)的始創(chuàng)者,現(xiàn)代心理學(xué)的鼻祖之一。著有《無意識過程心理學(xué)》《心理類型》《分析心理學(xué)與夢的釋義》和《記憶、夢、思考》等書。1902年獲蘇黎世大學(xué)醫(yī)學(xué)博士學(xué)位。除精神病學(xué)研究外,對于人類靈魂之秘密的知識,他是無所不學(xué)的。由于不倦努力,他后來成為瑞士乃至西方著名的分析心理學(xué)家,也是杰出的東方文化研究者,曾為英國皇家醫(yī)學(xué)會名譽(yù)會員、瑞士醫(yī)學(xué)學(xué)術(shù)院名譽(yù)會員、巴賽爾大學(xué)醫(yī)學(xué)教授、瑞士聯(lián)邦工業(yè)研究所哲學(xué)及政治學(xué)名譽(yù)教授。榮格經(jīng)歷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目睹過西方科技文明和基督教文化的嚴(yán)重危機(jī),深感西方文化需要東方文化的參與和制衡。因此,他繼承萊布尼茨、叔本華、尼采、歌德等西方思想家面向東方的傳統(tǒng),潛心研究東方文化,把東方文化尤其印度和中國文化的珍寶融入自己的心理學(xué)理論之中,從而使自己的理論建構(gòu)帶有東西文化兼容并蓄的現(xiàn)代特色。他在其近兩百種大大小小的著作中,闡述了分析心理學(xué)的主要觀念,如原欲觀念、無意識與潛意識、宗教心靈與積極想象法等,揭示出與現(xiàn)代人類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心理癥問題,正如他在其著《人及其象征》中所言:“我深信,心靈的探討必定會成為未來一門重要的科學(xué)。……這是一門我們最迫切需要的科學(xué)。因為世界發(fā)展的趨向顯示,人類最大的敵人不在于饑荒、地震、病菌或癌癥,而是在于人類本身:因為就目前而言,我們?nèi)匀粵]有任何適當(dāng)方法來防止遠(yuǎn)比自然災(zāi)害更危險的人類心靈疾病的蔓延”。
理查德·威廉(1873-1930)出生于德國斯圖加特——當(dāng)時符騰堡王國的首府,是20世紀(jì)初葉德國最著名的漢學(xué)家之一zdpgqSw1XnPihxP1b8RsPQ==,法蘭克福大學(xué)漢語教授。原是魏瑪同善會傳教士,1899年被派到中國青島,從事慈善事業(yè),并在青島、濟(jì)南等地講學(xué)。來中國后他給自己取了漢名衛(wèi)希圣,字禮賢,亦作尉禮賢。1922年再次來華,被聘為北京大學(xué)德文教授。與來華傳教使命迥然相反,威廉的傳教成績幾乎等于零,在華25年不曾給一個中國基督教徒施行洗禮,但令人驚異的是,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二十多個年頭是在中國度過的,且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方面表現(xiàn)出博大的胸襟,并取得令人稱羨的成就。他把《論語》《易經(jīng)》《道德經(jīng)》《莊子》和《列子》等重要儒道經(jīng)典譯成德文出版,并撰寫《實用中國常識》《老子與道教》《中國的精神》《中國文化史》《東方——中國文化的形成和變遷》《中國哲學(xué)》等十余種專著,可謂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學(xué)西播”的一位功臣,對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xiàn)。
榮格和威廉是什么關(guān)系呢?為何有《紀(jì)念理查德·威廉》這樣的悼詞呢?
作為學(xué)者的榮格,既不懂漢語,也未曾到過中國,他得借助翻譯資料來了解中國文化,進(jìn)而研究中國文化,并將其融入自己的心理學(xué)建構(gòu)中。架設(shè)這種研究橋梁的工程師,就是威廉。正如榮格在悼詞中所言,他有幸與一位西方的中國文化研究者建立聯(lián)系,并結(jié)成跨國界的心靈契合的摯友,“我從未去過中國……也不熟悉它的語言……我的確像一個陌生人那樣站在這一知識和經(jīng)驗的廣闊領(lǐng)域之外,而威廉卻在其中游刃有余。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自己的專業(yè)領(lǐng)域,他作為漢學(xué)家我作為醫(yī)生很可能永不會發(fā)生聯(lián)系。但我們在人文領(lǐng)域中相遇,它一開始就超越了學(xué)院的疆界,在那里有我們的接觸點,在那里心靈的火花點燃了智慧的明燈,而這注定將成為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
威廉懷著對中國和中國人民以及悠久華夏文化的無比熱愛,在其不長的一生中勤奮著譯,終因積勞成疾,于1930年3月1日在德國圖賓根逝世。但他走得是那么平和,就像一個已經(jīng)大徹大悟的中國哲人一樣,是面帶著微笑永別人世的。他身后大量的譯作、著述和在東方學(xué)社、中國學(xué)院工作的成就與影響,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化在德國乃至整個西方的傳播,不僅改變了中國自近代以來在歐洲的落魄形象,而且為西方人打開了個新的、放射著異彩的精神世界,誠如當(dāng)代德國著名漢學(xué)家鮑吾剛教授在《衛(wèi)禮賢——兩個世界的使者》一文贊揚(yáng)威廉無疑是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悼詞《紀(jì)念理查德·威廉》,全文近7000字,言辭切切,感人至深!
一方面,榮格懷著感激和敬仰的心情對威廉一生的貢獻(xiàn)做出了恰如其分的總結(jié)與評價,“(威廉)這顆心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架設(shè)了一座橋梁,把一種持續(xù)了數(shù)千年、也許注定要永遠(yuǎn)消逝的文化珍貴遺產(chǎn),給予了西方”、“這種人超越了自己的專業(yè),其對知識的追求逐漸變成對全人類的關(guān)懷。或者勿寧說,這種關(guān)懷自始至終一如既往。此外還有什么能夠這樣完全地將他從歐洲人——的確,從傳教士——的狹隘眼界中解放出來,以致他剛一探究中國人心靈的奧秘,就立刻覺察到那兒隱藏著我們需要的珍寶,并為了這一稀世珍寶而犧牲其歐洲人的偏見呢?”“威廉具有母性智慧的罕見天賦,他把他無與匹敵的才能歸因于這種天賦,摸索著進(jìn)入東方精神的道路,致力其舉世無雙的翻譯工作”“正是理查,威廉,作為歐洲精神的使者,從東方為我們帶來了新的光明”、“威廉的畢生工作對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為它大大地澄清和確證了我在努力緩解歐洲人的精神痛苦時所一直尋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許多東西”。
另一方面,榮格也毫不隱諱地道出了他對東西文化的看法。這些觀念實際上也是榮格分析心理學(xué)的主要內(nèi)容之一。沒有對東西方文化共同性和差異性的比較研究,無法想象他的心理學(xué)建構(gòu)是對全人類關(guān)懷的理論產(chǎn)物。正是這種將東西方文化相互結(jié)合而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和原型理論,深刻揭示了人類心理和人類文化的根本一致性,從而得出了人類將可以在同一地球上培育一種人類共同的幸福與未來,這實際上就是東西合璧、世界大同的理想。
首先,榮格對傳統(tǒng)的“歐洲中心論”予以激烈地抨擊。眾所周知,從歐洲爆發(fā)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文化價值觀,“世界大戰(zhàn)之浩劫所帶來在我們意識觀里的革命,已在我們內(nèi)心生活中產(chǎn)生了,它摧毀了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價值”。這兩次都在歐洲首先爆發(fā)的世界性災(zāi)難,使人難以解釋,西方具有高度發(fā)展的科學(xué)技術(shù)和基督教文明,何以把人類引向世界大戰(zhàn)的血腥浩劫之中?似乎對此詰問的最好回答是西方人的精神出現(xiàn)了危機(jī)。榮格的分析心理學(xué)產(chǎn)生其間,其治療對象就是人的精神危機(jī)。榮格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已經(jīng)危機(jī)四伏了,“基督宣揚(yáng)其理念已近千年的今天,我們眼見的不是救世主再度君臨之天國的千福年,而是存在于基督教國家之間的世界大戰(zhàn)、鐵絲網(wǎng)、毒瓦斯。這真是一場天上人間的大浩劫”、“我們的世界已經(jīng)獲得了足以摧毀人類,使之變成宇宙塵埃的力量”。對此,榮格首先起而抨擊“歐洲中心觀”。他指出:“神秘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獲得了無以與之相對應(yīng)的復(fù)興——西方精神之光幾乎因此而熄滅。我現(xiàn)在想到的不是我們的高等學(xué)府及其代表人物。作為一個與普通人打交道的醫(yī)生,我知道大學(xué)已不再是傳播光明的地方。人們厭倦了學(xué)科的專業(yè)化,厭倦了唯理主義與唯智主義。他們希望聽見真理的聲音,這種真理不是束縛而是拓展他們,不是蒙蔽而是照亮他們,不是像水一樣流過而是深入到他們的骨髓之中。這一追求只是太容易把大批即便是無名的公眾引入歧途”(貝《現(xiàn)代靈魂的自我拯救“現(xiàn)代人的心靈問題”》)。在榮格眼里,以“歐洲中心論”自傲的白人無疑是一群貪得無厭、幻想到處為王的“雅利安種猛獸”,他們到處侵占土地,用甜酒、性病和鴉片等對付東方和非洲黑人,對此“中國人或印度人對我們將有何感想?我們在黑人之中引起了怎么樣的感想?”很明顯,這種猛獸必將引起東方和非洲人民的正義抗?fàn)帲⒈粨魯 ?br/> 面對西方的窘境,榮格非常贊賞威廉面向東方、為西方的精神世界的洗禮而深入研究中國文化的博大胸襟,“……是威廉從東方帶來了新的光明。這是一種文化任務(wù),認(rèn)識到東方在我們的精神需求中必須貢獻(xiàn)出多少東西”。威廉從東方帶來的新的光明,正是西方社會所缺乏的文化的多樣性和兼容性,以及社會的穩(wěn)定性和人民生活的寧靜狀態(tài)。因此,在悼詞中,榮格首先就以西方人的現(xiàn)實性精神危機(jī)為鏡像,極力消除基督單一文明和自欺欺人的“歐洲中心論”在西方人中所造成的心理陰影,鼓勵西人“睜眼”看東方文化,以增加自己對于社會發(fā)展的理解力。
其次,榮格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同時,鼓勵西方人無所畏懼地轉(zhuǎn)向東方,汲取東方文化的精華。在其分析心理學(xué)中,榮格認(rèn)為科學(xué)思想是西方心智的基礎(chǔ),但科學(xué)技術(shù)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片面的科學(xué)發(fā)展是危險的,片面的科學(xué)思維也是博學(xué)之士悲慘的空虛的精神反映。只有將現(xiàn)實的科技文明與更開闊更高級的心靈理解力結(jié)合到一起,才能使人類文明與人類大同命運(yùn)和諧而進(jìn)。然而,這種期望只有在東方才有通過生存而積累獲得的廣闊而深邃的生命意義的理解力。所以,榮格無所畏懼地轉(zhuǎn)向東方,并鼓勵已經(jīng)飽受文化單調(diào)和人性壓抑之苦的西方人也勇敢地面向東方,向東方學(xué)習(xí)。在悼詞中,榮格非常贊賞了威廉能拋棄歐洲偏見而直面東方文化的精神,“只有一種包羅萬象的人性、一種洞察全體的博大精神,能夠使他面對一種深相脖異的精神,毫無保留地敞開自己,并通過以自己的種種天賦和才能為它服務(wù)來擴(kuò)大其影響”。同時,榮格借此批判了基督徒的驕橫,“因為所有平庸的精神接觸到外來文化,不是夭折于放棄自己的盲目企圖,就是沉溺于不理解和批判的傲慢熱情。他們僅僅以外來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自娛,始終沒有嘗到它的真正好處,因而從未達(dá)到真正的心靈交流,那種產(chǎn)生新生命的最親昵的輸入和相互滲透”。
由此可知,榮格所說的面向東方并不是去獲取東方文化的外表與皮毛而自娛,而是要發(fā)現(xiàn)并汲取東方文化的精華,達(dá)到東西文化的互滲,以求全人類的和諧社會的創(chuàng)建。在悼詞中,榮格推崇威廉對《易經(jīng)》的譯注,“我認(rèn)為他最偉大的成就是他對《易經(jīng)》的翻譯和評注……威廉成功地以新的形式,使這部古代著作重新獲得了生命……很可能再沒有別的著作像這本書那樣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的生動氣韻……它歷盡滄桑歲月卻依然萬古長新,永葆其生命與價值”。言如心聲,這實際上反映出榮格對東方文化、尤其中國文化之精華的認(rèn)識,“幾年以前,英國人類學(xué)會當(dāng)時的主席問我,為什么中國這樣一個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卻沒有科學(xué)上的成就。我回答說,這一定是一種視覺錯誤,因為中國人確有一種科學(xué),它的標(biāo)準(zhǔn)經(jīng)典就是《易經(jīng)》。只不過這種科學(xué)的原理,也如同中國許多別的東西一樣,完全不同于我們科學(xué)的原理罷了”。應(yīng)該說,榮格是非常重視《易經(jīng)》的,幾乎可以說,《易經(jīng)》一直伴隨著他的生活與工作。在威廉的《易經(jīng)》譯本出版前,榮格使用的是英國漢學(xué)家詹姆斯·列格的譯本。在讀到威廉譯本后,榮格才深刻讀懂了《易經(jīng)》的心理學(xué)意義,從而使,之成為分析心理學(xué)的例證和淵源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榮格不僅不同意將《易經(jīng)》視為符咒的說法,“不僅許多漢學(xué)家,而且大多數(shù)現(xiàn)代中國人,都不能看出其真正的價值而把它僅僅視為荒謬的巫術(shù)符咒的匯編”,而且認(rèn)為威廉這項工作的更重要方面,是“他把中國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種到我們身上,能夠?qū)ξ覀兊氖澜缬^造成一種根本變化。我們不再被降低為崇拜的或批評的旁觀者,而是不僅參與到東方精神之中,而且還成功地體驗到《易經(jīng)》的生氣盎然的力量”。
我們知道,東西方的科學(xué)思維方式在本質(zhì)上就是不同的,那么東方文化的精華究竟能帶給西方人什么好處呢?在榮格看來,當(dāng)西方人已經(jīng)對科技至上和唯理性主義感到厭惡的時候,《易經(jīng)》恰好適應(yīng)了西方人自我認(rèn)識的心理需要,它以純樸而經(jīng)久不衰的生命力,為西方人提供了一種更適宜和更正確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具有轉(zhuǎn)變?nèi)祟愋撵`的巨大力量,“這種根據(jù)同步原理的思維,在《易經(jīng)》中達(dá)到了高峰,是中國人總的思維方式的最純粹的表現(xiàn)”、“就在這時候,《易經(jīng)》響應(yīng)了我們心中某種需要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東西”、“任何有幸與威廉一道體驗到《易經(jīng)》的神奇力量的人,像我一樣,都不可能不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阿基米德點,憑借這一個點,我們的西方心態(tài)將被撬離其基礎(chǔ)”。上述所言,集中到一點就是,在西方土壤里移植古代中國智慧的生命胚芽,可以改變西方人狹隘的世界觀和生命觀,只有這樣才能補(bǔ)救西方現(xiàn)代化發(fā)展的偏頗。東方文化的精神與精華的價值,也正在此。
總之,《紀(jì)念理查德·威廉》雖是榮格對威廉在傳播東西文化的貢獻(xiàn)及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所做的最好總結(jié),但更主要的是再現(xiàn)了榮格本人對于東西文化的重要觀念。榮格畢生所建構(gòu)的分析心理學(xué)更是他將東西方文化有機(jī)結(jié)合的結(jié)晶,表達(dá)了人類能在共同人性的基礎(chǔ)上、由東西文化交融相合而能培育人類共同的幸福與未來的美好愿望。榮格的東西文化觀,對于我們當(dāng)前積極吸收外來一切文明成果、促進(jìn)本民族文化發(fā)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借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