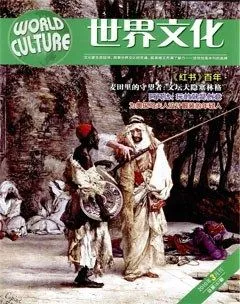隱秘而熾熱的愛情
1820年,青年普希金由于《自由頌》等反專制暴政的詩歌,被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流放南方。1823年,他從基什尼奧夫轉到敖德薩,受南俄總督沃龍佐夫伯爵監管。在敖德薩,普希金追求自由、無拘無束的詩人氣質與嚴謹古板的沃龍佐夫的官僚習氣經常沖突,于是,他的唐璜習性便更加突出,愛上了一批年輕婦女和姑娘,以致特羅亞認為這個時期,“他在女性身上所花的心血比寫詩還要多”。其中在其“唐璜名單”上留下名字的有兩個女人,一個是敖德薩富商里茲尼奇的妻子阿瑪麗婭,這是普希金青年時期最狂熱的愛情之一,但由于她后來懷孕、生子,接著因病出國不久病逝,他們的愛情中斷了,普希金為她寫下了《在自己祖國的藍天下》、《招魂》、《你離開了這異邦的土地》等名詩:另一個便是沃隆佐娃。
伊麗莎白·克薩維里耶芙娜·沃隆佐娃(1792?-1880)(沃隆佐娃確切出生于哪一年,暫不可考,法國傳記作家特羅亞在其《天才詩人普希金》中認為,1823年下半年,她與普希金相識時剛過30歲,當為1793年;英國傳記作家比尼恩在其《為榮譽而生——普希金傳》中則認為她是31歲,并且明確宣稱她“比普希金大7歲”,當為1792年;而我國學者劉文飛在其所譯《普希金全集》第二卷第146頁注釋2中則認為她出生于1790年),出身于波蘭一位貴族家庭,富有教養,也很有頗高的藝術修養,長相嬌美,風韻迷人,而又聰明多情,有人甚至這樣寫道,“對沃龍佐夫伯爵太太的美貌、精神和優雅的風度,我找不到恰當字眼去形容”。直到晚年,她一直保持著青春時的魅力,作家索洛古勃見到晚年的她以后寫道:“沃隆佐娃是當代最有魅力的女人之,已經上了年紀,但她還是那么優雅、裊娜,穿戴又那么時髦、講究。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像普希金、拉耶夫斯基這樣的人會如此強烈地愛上這個女人。”普希金可能對她是見鐘情,而她對這位不修邊幅、長得像猴子的著名詩人起初是好奇,后來隨著接觸漸多,感情漸深,最終愛上了這位詩人,甚至與他在山洞里幽會。沃龍佐夫本就對詩人極其不滿,知道詩人與妻子相好之后,更加憤怒,一再上書朝廷,要求讓普希金離開敖德薩。于是,1824年8月,詩人被迫離開敖德薩,被押送到北方荒僻的一個山村——他母親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村。盡管此后兩人再沒見面,但詩人的心里直裝著沃隆佐娃,后來還一再為她寫詩。而沃隆佐娃也對詩人柔情未斷,不僅詩人離開敖德薩時送給他一條嵌有自己肖像的金質頸飾和一枚帶有紅玉髓寶石(這種寶石在民間是愛情的象征且能消災除病)、寶石上刻有古文的戒指(普希金非常珍惜這枚戒指,把它稱為“護身符”,一直帶在身邊,從未離開過它,去世前將它遺贈給自己的詩歌老師和忘年之交茹科夫斯基,后來茹科夫斯基的兒子巴維爾又把它送給了著名作家居格涅夫),而且在分別后的一段時間里背著丈夫與詩人通信頻繁,并且終生熱愛普希金的詩歌,幾乎每天都要閱讀,年紀大了視力衰退后,就叫別人給她朗讀。
從1824年到1830年,普希金為沃隆佐娃創作了一系列愛情詩,大約14首,它們是:《普洛塞爾皮那》、《致大海》、《致航船》、《愛情的居所,它永遠……》、《陰霾的白天已逝去;陰霾的夜晚……》、《就算我已贏得美人的愛情》、《被焚的書信》、《渴望榮光》、《“在秘密的洞中,在被逐的日子”……》、《保佑我吧,我的護身符……》、《為了對你的懷念》、《護身符》、《天使》、《道別》,堪稱‘沃隆佐娃組詩”。這組詩只有幾首創作于敖德薩,大多寫在詩人離開南方后,盡管是抒情詩,而且為了避免麻煩,詩人在詩中運用了象征手法,但我們還是可以從這組詩中基本了解他們相愛的大致情況,這組詩也因此可以稱為隱秘而熾熱的愛情。
《普洛塞爾皮那》借用古羅馬神話形象——冥后普洛塞爾皮那溜出地獄,來到人間,愛上一位凡人青年,并且與他幽會:“脫去皇袍和皇冠,/她服從于欲望,/將那隱秘的美麗,/用熱吻給了那青年,/她沉湎于甜蜜的溫情,/在默默地繾綣地呻吟……”《愛情的居所,它永遠…》進而寫到他們是在海邊的山洞幽會“愛情的居所,它永遠/充滿朦朧、濕潤的清涼,/羞怯的波浪那悠長的轟鳴,/永久地在那居所里回響。”透過始終的“朦朧、濕潤的清涼”和波浪的“悠長的轟鳴”,隱隱約約交待了幽會的地點是海邊的一個山洞,這在該詩的草稿中寫得更加明確:“在海邊古老的懸崖下面/有一個僻靜的山洞,/里面是一片涼爽的陰暗……”《護身符》和《“在秘密的洞中,在被逐的日子”……》更具體地寫到他們在大海邊荒涼的懸崖下秘密的洞中幽會,神奇的女人沃隆佐娃還送給他一個具有“奇異神秘的力量”的護身符,上面鐫刻著“神圣的話語”,盡管它不能使詩人擺脫疾病,逃脫墳墓,但卻能使之不致在愛情上犯罪,也不會變心、遺忘。《就算我已贏得美人的愛情…》則寫到沃隆佐娃把自己的肖像贈給詩人,以及詩人分別后對她的一往深情:“就算我已贏得美人的愛情,/珍藏的金盒中嵌著她的倩影,/隱秘的書信,長久痛苦的獎賞,/可是在苦苦別離的輕輕時分,/沒有任何東西能愉悅我的眼睛,/無論是我的戀人的唯一的所贈,/還是愛情的誓言,凄情的安慰,/都治愈不了這瘋狂無望的愛情。”《致航船》則寫到沃隆佐娃1824年6月14日乘船離開敖德薩去克里米亞休養,詩人對她的關心與真情:“你這海上有翼的美人!/我在呼喚你,漂流吧,/請護佑這祈禱、希望/和愛情的無價的抵押。/風兒,請你用晨的呼吸,/鼓滿那張幸福的風帆,/別用波浪劇烈的搖晃,/使她的胸口感到苦酸。”《被焚的書信》還寫到詩人被迫聽從沃隆佐娃的命令,焚毀了她寫給他的情書:“別了,情書!別了,這是她的命令。/我拖延得多么久!那么久,我的手/不愿將我所有的歡樂都投向烈火!……/但是得了,時候已到。燃燒吧,情書。/我已準備,我的心靈聽不進任何聲音。/那貪婪的火焰已在吞食你的信紙……/等等!……著了!它們在燃燒,/輕煙騰起,又隨我的祈禱散去。/那忠誠手指的印跡已在消逝,/封漆在冒泡……哦,預見啊!/終于應驗!焦黑的信紙已卷起;/白色的字跡還在輕塵上閃亮…/我感到胸悶。親愛的灰燼啊,/我憂郁的命運中可冷的歡樂,請你永遠留在我憂傷的心上……”
但這組詩寫得更多的,是詩人離別的思念和深情。在寫于敖德薩的《致大海》一詩中,詩人已深感自己“為有力的激情所迷惑”,停留在海岸,難以離開。離開敖德薩后,詩人更是時常思念沃隆佐娃,一再寫詩表達自己的深情。《陰霾的白天已逝去:陰霾的夜晚…》設想戀人思念自己,又去到他們時常幽會的海邊隱秘的峭崖旁,滿懷憂傷,偷偷飲泣:“陰霾的白天已逝去;陰霾的夜晚/又給天空穿上了鉛一樣的衣裳;/像幽靈一樣,在松樹林的背后,/升起輪朦朧的月亮,/這一切使我的心沉進陰暗的憂傷。/遠方,月亮在那邊明亮地爬升;/那邊的空氣充滿了傍晚的溫暖:/那邊的大海在藍色的天幕下涌動,/掀起華麗美妙的波浪……/這時,她正沿著山路走向海岸,/一排排咆哮的波浪拍打著岸邊,/那邊,在隱秘的峭崖旁,/此刻她孤獨地坐著,滿懷憂傷……/孤身一人……沒有人對她哭泣,感傷:/沒有人去忘情地親吻她的雙膝;/孤身一人……她不讓任何人的唇去吻/她濕潤的唇、雪白的胸和她的肩膀。/……沒有人能配得上她天仙似的愛情。/是不:你孤身一人……你哭泣……我平靜:/……但是如果……”《渴望榮光》不僅表達對她深情思念,而且希望自己在流放的厄運中,在痛苦、背叛、誹謗的黑暗中,盡管本已厭倦榮光,但是為了愛情,還是希望擁有更大的榮光,以便自己的名字時時刻刻響徹在戀人的耳旁,讓她總是記住自己:“當我沉緬于愛情的溫柔,/默默地跪在你的腳旁,/看著你,我在想你是我的,/親愛的,你知我是否渴望榮光;/你知道:遠離輕浮的圈子,/對詩人的虛名感到無聊,/我倦于長久的風雨,完全/不再理會遠處的指責和贊揚。/當你向我遞來繾綣的目光,/輕輕地將手放在我的頭上,/輕聲問:你愛我嗎,幸福嗎?/你可會愛上另一個像我的女人?/朋友,你永遠也不會將我遺忘?/而我卻保持著害羞的沉默,/我渾身都充滿了幸福,我想,/不會有未來,可怕的離別/永遠不會到來……可是怎樣?/眼淚,痛苦,背叛,誹謗,/這一切突然都落到我的頭上……/我怎么了,我在哪里?我站著,/像個在荒原上遭遇閃電的旅人,/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如今,/我又在受累于新的渴望:/我渴望榮光,好讓我的名字/時時刻刻響徹在你的耳旁,/好讓你被我所包圍,好讓/你身邊的一切都高聲將我談講,/好讓你在寂靜中傾聽忠言時,/能回憶起我最后的禱告,/在花園,在黑夜,在分別的時光。”在《保佑我吧,我的護身符……》一詩中,詩人祈求沃隆佐娃送給自己的護身符能在各種困境和逆境中保佑自己,從側面表達了對戀人的思念。1830年秋天,在和心愛的岡察洛娃結婚前,詩人最后一次深情地寫詩向沃羅佐娃《道別》:“最后一次,我在想像中/愛撫著你可愛的倩影,/用內心的力驚起幻想,/懷著膽怯、憂傷的溫柔,/回憶著你對我的愛情。∥我們的歲月變換著逝去,/它也變換了我們和一切,/你已經為你的那位詩人,/披上了墳墓中的黑暗,/他對于你也已不存在。∥遙遠的女友,請接受/我這發自心靈的道別,/像一位喪夫的妻子,/像朋友,在友人被囚前,/默默地擁抱他的雙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