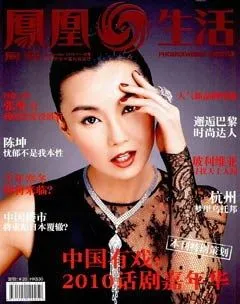中國有戲2010話劇嘉年華
2010-12-31 00:00:00郭薔
鳳凰生活 2010年11期


都說“看話劇,看的是人生百態”,2010年歲末,在深圳,你只需坐在劇院里,就可以穿越時空,穿越城市去體味人生百態。在舞臺下,你可以領略繁華鬧市的愛情糾葛,也可以回到古城胡同追溯那段崢嶸歲月……
從臺北的小城故事到法國的浪漫演繹,從古代的金瓶故事到如今的時代獨自,讓我們來看戲吧。
戲劇一向被稱為集詩歌、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于一體的“第七種”藝術。100年來,“話劇”這朵奇葩,一直散發著迷人的芬芳,它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與中國近代的歷史血脈相連。
話劇是集體共同參與的一種精神生活方式,它是神圣的,它解決了許多人的精神渴求。
2010年的年尾,深圳這座城市再一次迎來了“話劇節”,這不僅是一次文化的盛宴,更是一次對話劇的集中檢閱和重新激活。
在北京,田沁鑫沿著老舍先生的胡同,在《四世同堂》中述說京城沉重的抗戰生活;
在中國臺北,賴聲川連續24年繼續“暗戀著桃花源”,李國修用喜劇手法在《三人行不行》中輪番呈現都市的混亂生活和疏離的人際關系;在上海,
《金瓶外傳》實現了宋朝人物的時代穿越與華麗轉身;在中國香港,林奕華用《命運建筑師之遠大前程》引領人們尋找幸福生活;在紐約,蔡錫昌導演引領你去欣賞百老匯最經典的話劇表演。賴聲川:彼岸的桃花源此岸的夢想地
《暗戀桃花源》這部戲,我覺得它的形態會變,但本質的東西是不會被改變的,就像一個人,他的口音會變,服裝可換,但靈魂深處的東西將永遠存在。
他29歲開始劇場創作,至今編導舞臺劇27部(包括轟動亞洲的七小時史詩《如夢之夢》)、電影兩部(包括享譽國際的《暗戀桃花源》)、電視影集300集(包括家喻戶曉的《我們一家都是人》),另有劇場導演作品22部(包括奠扎特歌劇三部)等。他就是賴聲川,他被全球媒體譽為“亞洲劇場導演之翹楚”。
栗小衣:聽說您06年在浙江的時候,就開始“密謀”做一出越劇版的《暗戀桃花源》,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想法?
賴聲川:06年我們推出臺灣歌仔版,當時與最富盛名的明華園戲劇團合作。演出空前成功,當時,明華園團長說:“這次成功的嘗試之后,任何地方的戲劇我們都能做了,譬如說越劇。”他當時提到越劇時,我心中忽然就生出一種感覺,我就決定要做一個越劇版的《暗戀桃花源》。這次排戲的時候感覺很好,我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
栗小衣:今后有沒有考慮做一個川劇版,昆曲版,或者京劇版的《暗戀桃花源》呢?
賴聲川:地方戲種各有利弊,選擇越劇因為它的視覺唯美,節奏感比較好。譬如京劇,節奏就慢了一點,但也不排除將來會考慮其他劇種。
栗小衣:賴導您每次選角都有獨到之處,也很敢起用明星,發掘他們的戲劇潛力。這次的桃花源部分,用到的也是越劇名角,像趙志剛就是上海越劇院的當紅小生,人稱“越劇王子”,以優雅著稱。這次在戲里卻以顛覆的漁夫老陶形象出現,在選角方面,賴導是怎么考慮的呢?
賴聲川:這對演員確實是一個蠻大的考驗。趙志剛平素的造型都十分優雅,他也一直想尋求突破,覺得這是一次非常好的機會。他是個彈性挺大的演員,這次他的演繹十分精彩,戲迷都說認不出他了。
栗小衣:電影海報上還有這樣的一句英語介紹:One stage;Two plays;Same dream。兩出戲劇同臺演出,卻共同持著同一夢想。他們的夢是什么呢?其中又映射了您心中何樣的理想呢?
賴聲川:無論是桃花源的夢想,還是江濱柳回憶中最美好的狀態,都默默道出了一種亙古永恒的情感。這句話也解釋了為何24年來《暗戀桃花源》不斷上演,卻不會讓觀眾心生厭倦,因為它傳達的主題是永遠的追尋。這是一種沒法用語言準確描述的感覺,但我們每人都能真切感知他的存在。
栗小衣:《暗戀桃花源》從1986年臺灣首演至今,已經走過了24個年頭。你曾經說過: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運,一部戲有一部戲的命運。你認為《暗戀桃花源》最終會通往哪里呢?
籟聲川:《暗戀桃花源》這部戲,我覺得它的形態會變,但本質的東西是不會被改變的,就像一個人,他的口音會變,服裝可換,但靈魂深處的東西將永遠存在。
栗小衣:六個版本的云之凡中,臺灣的丁乃竺,林青霞,蕭艾,到香港的蘇玉華,再到大陸的袁泉和孫莉,你覺得她們身上誰更有山茶花的味道?
賴聲川:丁乃竺是創造這個角色的,因而她在我心目中是最特別的,從這個層面上說,她是永遠特殊的,獨一無二的。袁泉,孫儷,她們各有各的特色,這不像NBA籃球,能準確計算姚明一個籃板得了幾分。看不同的演出,能感受到幾代演員對角色獨到精彩的詮釋。
蔡錫昌:我追求照耀人性光輝的作品
采訪/郭薔
中國話劇本身就是世界戲劇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北京人藝早于上世紀80年代向西方證實了我國的貢獻和實力。走向市場是一個危機,因為只有“懸鏡于世”、照耀出人性光輝的作品才能登上世界劇壇大雅之堂!
與蔡導見面是在一個戲劇沙龍上,聽蔡導講西方戲劇的發展史,介紹美國紐約百老匯經典戲劇和紐約地區知名的藝術學院,就約好了要做一次專訪。
郭薔:您怎樣看當代香港話劇與世界戲劇的關系?
蔡錫昌:中國香港話劇的源頭有兩個:一是五四運動以來,內地劇人南下發展的延續。第二,香港劇人自60年代以來,從英、美及歐洲學成歸港,引進了與西方同步的發展。近八至十年來,亦有本港戲劇學生回內地的學院學習,譬如中央戲劇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等。另一方面,新加坡郭寶昆先生大約十年前開辦戲劇訓練及研究課程,香港也有數人前往就讀。總的來說,發展系統以英語國家戲劇系統為基礎,但是也隨著現代戲劇的發展趨勢,越來越注重非文本劇場的傳統,與世界戲劇一同邁進。
郭薔:有資料說,與大陸、臺灣情況有所不同,香港于上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翻譯和演出西方戲劇,不知道是否確切?
蔡錫昌:港人多諳英語,到英、美兩國接受訓練也是順理成章的事。至于香港戲劇發展的足跡,開埠不久己有英語話劇,根據紀錄上世紀初開始有中文話劇的出現。翻譯劇應該早過50年代,只是那個時候發展得比較好。60年代就更加興旺了。商業劇場的發展其實牽涉了由政府主導的生態環境。由香港方梓勛教授與北京田本相教授合編、遼寧教育出版社剛出版的《香港話劇史稿》中對于藝術家與作品有頗詳盡的闡釋,在此就不贅了。
郭薔:今年年初,您執導的《哥本哈根》在香港上演,反響熱烈,可惜我沒有機會欣賞到,“科學”戲搬上了中國舞臺,肯定會給觀眾帶來了不一樣的舞臺體驗和審美感受。當時基于什么原因促使您把這出戲搬到中國香港的舞臺?
蔡錫昌:搬演《哥本哈根》,就是為了上述的原因,因為劇本的深邃淵博,值得介紹給香港的觀眾。演出后所得到的反應,也證明了多元化市場的存在和需要。可是要指出的是,《哥本哈根》談的并非科學那般簡單,其主題內容涉及人文價值、科學與宗教的關系、民族思想與愛國等等,就在較低的層次,也是一出挺出色的“whodunit偵探劇。正如任何好的作品一樣,可有不同的層面供觀眾欣賞、玩味。
個人而言,80年代下來+多年,我都致力本土原創劇的發展,到了干禧年代,有眾劇團的成立,既演經典,因為我們應該認識前輩所走過的路,也要以戲劇反映時代,因為這是劇場的社會責任。
郭薔:您自己寫劇本嗎?
蔡錫昌:如上面所言,眾劇團走的是創作及演譯經典的路線。的確,許多原創劇都出自我的手筆。特別是,在1985年與杜國威合作的《我系香港人》,一共演出了144場、述說了香港自開埠以來的140多年的歷史活報劇,在我心中占著一個特殊的位置。
郭薔:您認為中國話劇(包括中國香港及中國臺灣)走向世界的路還有多遠?
蔡錫昌:中國話劇本身就是世界戲劇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份。北京人藝早于上世紀80年代向西方證實了我國的貢獻和實力。走向市場是一個危機,因為只有“懸鏡于世”、照耀出人性光輝的作品才能登上世界劇壇大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