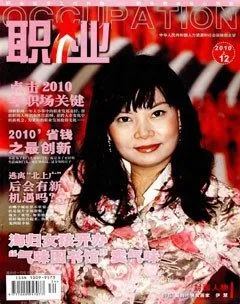“被”選擇的職業角色
我們這一代人,大學畢業后是分配工作,沒有吃過找工作的苦。靠分配得來的工作,因為身后有一份人事檔案,像繩子一樣牢牢地拴著,想重新選擇、調整一份新工作,難上加難。即使這樣,從青年到中年,一路走來,我先后在四個正科(局)級以上單位輪崗,在十個以上部門工作過,與職業性質相類似的大多數同齡人相比,不可謂經歷不豐富。其中有的調動是我蓄謀已久、主動爭取的;有的是服從組織安排、工作需要,時也、勢也。時至今日,我經常問自己:到底哪一個職業更適合我?
“匠”
我最初的職業是鄉村語文老師,先中學,后小學。我是非常熱愛這個職業的,當初讀師專的班上,我是唯一自愿選擇讀師范類而且如愿以償讀中文專業的。現實就是現實,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鄉村教師,經濟、社會地位太低,低得連找對象都成問題,我漸漸對這個職業失去了興趣。我的性格也有致命的弱點:面對那群小毛孩,我傳道授業、釋疑解惑缺少最起碼的耐心——我喜歡創新,不喜歡走重復的路。那個職業,只能允許我按部就班、年復一年地在三尺講臺上熬白頭發。我不得不醞釀逃離、選擇“跳槽”。若干年后,回頭看看,我仍然希望自己有重返講臺的機會,但不是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而是大學的課堂。我非常希望自己退居“二線”后能找到一家民辦高校,為一群生機勃勃的年輕人講課。我有信心講好的有兩門課:寫作和新聞采寫。我曾經為這個職業努力過,希望通過考研的路直接從中小學的講臺走上大學的講臺,可惜我不是一個博聞強記的人,沒有那個心智,不適合專門做學問,所以我不得不放棄。經過這些年的歷練,我獲得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在外發表了有關這兩門課的一些論文,我想,也許可以一試了。
“家”
我最在意的頭銜是作家。雖然我現在已掛著一個省級作家協會會員的稱號,可我從來不敢真的把自己當作家看。作家是什么?他應該有才華、有學識、有思想,我呢,什么都沒有,只有生活。我只是用文字在講述自己的生活。這是層次很低的寫作,與作家的名號是不相匹配的。如果才華是與生俱來的內在素質,我怕是這輩子都與才華無緣了。學識呢,學是學了一點,多是皮毛,不求甚解,還遠沒有到化為己有、成為“識”的地步。至于思想,更是無從談起,我只有零碎的想法、念頭,成系統的思想,從來不敢奢望。我渴望自己成為大作家、大文豪,這樣的渴望連理想都不可能是,只能是夢想。我所能做的努力,是離那個遙遠的夢想接近一點、再接近一點,最終相差多少距離,我想也不敢想。
“者”
我做過許多年的新聞記者,我獲得的最高職稱就是記者中級。如果說我最愛做夢的年齡獻給了鄉村中小學講臺,那么,中年之前的大部分寶貴時光,我是獻給了新聞采訪工作。這個工作我做得很好,得到的最高榮譽是大市級“十佳”新聞工作者,《人民日報》這樣的中央級大報也多次用較大版面刊登我采寫的人物通訊。盡管這樣,我還是不能說這個職業最適合我。記者這個職業與現實靠得太近、平時太熱鬧,我不喜歡。累、有壓力倒在其次,關鍵是辛苦之后很難收獲想要的東西,連靜下心來好好理一理思緒的時間和氛圍都沒有。有人干了一輩子記者,說自己到頭來就像漂浮在水面的油花,表面風光無限,骨子里水還是水,油還是油,薄薄的一層,似有似無,從未真正溶于水。我喜歡這個比喻。話歸這么說,記者這個職業還是讓我獲益頗豐。年輕人如果想在較短的時間內比較全面地認識這個社會,最好的職業無疑應該就是記者。
我先后還充當過機關秘書、部門管理者等角色,我心甘情愿、孜孜不倦去竭力干好的職業,似乎還是做一名文字工作者。做一個蹩腳的作家,我是文字工作者;做一個人在曹營心在漢的記者,我是文字工作者;做一個成天為領導寫講話稿、為活動制定方案的機關秘書,我是文字工作者……從事這些工作,我都在提醒自己:千萬千萬,不要把自己退化成為文字匠!家、者、匠,它們是不同層次的寫作,前者追求心靈的自由,后者主要是謀生的手段,審視自己的天賦,我將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中間。無論是我選擇了職業,還是我被職業選擇,我都有勇氣說自己是一個兢兢業業的人。做一名文字工作者,或者再跳一跳,做一名優秀的文字工作者。這不是什么十分崇高的理想,也不是什么十分榮耀的職業,但對于我,已經十分滿足。因為這個職業,既可以承載我個人的人生價值,也可以承載我為這個社會應盡的義務。做好這個職業,同樣需要我付出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