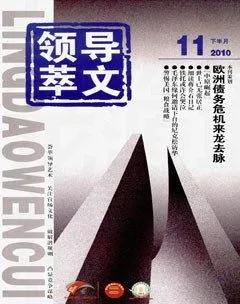歐洲債務危機來龍去脈
編者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國際金融危機的延續與深化。本期刊登的《歐洲債務危機來龍去脈》對此問題做了深入解讀,對讀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發展大有助益。
閱讀1
歐洲債務危機主要成因
早在2008年10月華爾街金融風暴初期,北歐小國冰島的主權債務問題就浮出水面,而后中東歐債務危機爆發。鑒于這些國家經濟規模小,國際救助比較及時,其主權債務問題未釀成較大全球性金融動蕩。2009年12月,希臘的主權債務問題凸顯,今年3月進一步發酵,開始向“歐豬五國”(五國第一個英文字的縮寫,即“PIIGS”,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愛爾蘭、Greece-希臘、Spain-西班牙)蔓延。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則投井下石,連連下調希臘等債務國的信用評級。至此,國際社會開始擔心,“歐豬五國”的債務危機可能蔓延全歐,由此侵蝕脆弱復蘇中的世界經濟。
一、金融危機是主要導火索
實際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延續與深化。一般情況下,在一國經濟繁榮時期,私人借貸即債務相對較高,而在危機時期或危機之后,由于經濟下滑,財政收入減少,以及抗衰退增加支出,政府財政狀況會惡化,主權債務會增加。本次金融危機的源頭在美國次貸危機,其引發的華爾街金融風暴涉及全球金融市場,導致世界經濟全面衰退,結果點燃希臘等歐洲國家已經暗藏多年的主權債務風險。一方面,金融危機使2009年歐元區GDP下降4.1%,降幅超過美國的-2.6%,為過去60年最嚴重。經濟衰退使各國政府稅收減少,財政收支狀況惡化;另一方面,為應對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各國政府不得不采取財政刺激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又使政府財政赤字增加,由此加大財政收支缺口。
事實上,自2004年以來,歐盟部分國家已經突破《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和政府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標準。如2007年,希臘的財政赤字達到3.9%,政府債務高達104%,均超過《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上線。金融危機加劇歐洲各國的財政與債務狀況。據統計,2009年,歐元區的平均財政赤字占GDP的6.3%,公共債務占GDP的78.7%,尤其是5f82a54a655d1c71a76ba9b5d07613d5PIIGS國家(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財政赤字分別占GDP的13.6%、12.5%、11.2%、8%和5.3%,政府債務占GDP的113%、66%、54%、77%和119%。其財政赤字與主權債務規模上升,遭致評級機構對其信用評級的下調,進而引發信心危機,使融資成本上升,融資難度加大,最終導致債務危機爆發。
二、體制性缺陷是深層原因
歐元區“天生”的體制性缺陷,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二元性”是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本性原因。基于各國政治意愿,歐元區成立之初只統一貨幣政策,未統一財政政策,財政大權依然被視為各國經濟主權范圍內的事。這種二元結構自一開始就遭到質疑,但直到債務危機爆發,其危害性才真正顯現,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從事前預防來看,這種二元結構無法對歐元區成員國財政狀況進行有效監督和及時糾正,造成成員國財政紀律松懈。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的貨幣政策使各國在面對危機沖擊時,過多依賴財政政策,并且有擴大財政赤字的內在傾向。事實上,歐盟對此缺陷設有防火墻,即《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成員國財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否則將被懲罰。然而到2005年初,歐盟同意其成員國財政赤字可“暫時”超過3%,這為而后突破防火墻埋下了伏筆。
二是從事后應對看,二元結構充分暴露出歐元區危機處理能力不足。為便于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單一貨幣區成員國即便不能統一財政,也應在財政上保持步調一致。針對歐元區財政“短板”的天生缺陷,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規定應該成為成員國必須遵守的財政紀律。但事實證明,公約執行力相當有限。由于在制定和實施財政政策時缺乏協調機制,債務危機爆發后,各國在救助過程中爭吵不休,又各自為政,致使危機持續擴散。可以說,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二元性”相當于歐元區各成員國的貨幣政策“一條腿”被綁在一起,而財政政策“另一條腿”則自行其是,最后造成“一條腿走路”的困境,結果導致公共支出過度膨脹,財政赤字大幅上升,進而出現債務累積和主權信用危機。
三、結構性矛盾是重要誘因
首先,近幾年,隨著歐盟成員日益擴大,由15國增加到27國,歐元區由12國擴大到16國,成員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開始參差不齊。德國、荷蘭等西歐國家與希臘、西班牙等南歐國家之間出現經常項目嚴重失衡。德國、荷蘭等具有很強的出口競爭優勢,長期擁有經常項目順差,2009年順差余額達到GDP的5%。而希臘、西班牙等南歐國家因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出口競爭力較弱,出現巨額經常項目逆差。結果,歐元區自身出現內外發展失衡問題,由此加大貨幣政策的調整難度。
其次,雖然希臘等南歐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比西歐低,自加入歐元區以來,迫于政黨與工會的壓力,這些國家在福利制度方面極力向富國看齊,在稅收與財政不允許情況下,過度提高公務員工資和退休養老金等福利待遇。加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不僅給政府造成巨大財政壓力,而且使單位勞動成本上升,使希臘等南歐國家在與亞洲等新興市場的低成本競爭中更處于劣勢。
最后,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歐元的持續升值,使南歐國家以往具有的傳統產業的競爭優勢喪失殆盡。加之歐元區實施統一貨幣政策,各國在面臨內外失衡時無法通過貨幣政策,以提高出口競爭優勢,只能采取財政刺激政策,以維持國內經濟增長。在經濟擴張期,只要經濟持續增長,政府稅收就會增加,財政支出可通過增加稅收來彌合。但當金融危機爆發時,經濟衰退、稅收減少,希臘等國的財政赤字驟然惡化,成為主權債務危機的主要引爆器。
四、游資炒作起推波助瀾作用
2001年希臘加入歐元區時,為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提出的要求,即政府預算赤字不超過GDP的3%、未清償債務總額不超過GDP的60%,希臘政府通過與美國投行高盛集團合作,與其簽訂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協議,將財政赤字降為1.5%。最近披露,當時希臘的真實財政赤字是GDP的5.2%,遠遠高于3%。尤其是,以各種手段讓債務維持在規定水平之下的國家不只希臘一家,還有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德國也造假。
當時對財政赤字情況的隱瞞,為今天危機爆發埋下禍根。債務危機爆發后,高盛等投行又大肆做空歐元,導致全球市場一片恐慌,美歐股市連連下挫,歐元大幅貶值,經濟出現“二次探底”風險。在對沖基金等游資推波助瀾下,希臘等債務危機國家的融資成本飆升,使其無法用借新債來還到期的債務,由此助長危機爆發并蔓延。
閱讀2
歐洲債務危機演進過程
一、希臘成為歐洲債務危機的引爆點
2009年12月,希臘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問題曝光。隨后,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紛紛下調其信用評級,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全面爆發。今年上半年,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一直致力于為希臘債務危機尋求解決辦法,但分歧不斷。因為,歐元區成員國擔心,無條件救助希臘可能助長歐元區內部“揮霍無度”,并引發本國納稅人不滿。同時,歐元區內部協調機制運作不暢,致使救助希臘的計劃遲遲不能出臺,導致危機持續惡化,并向歐元區其他國家蔓延。
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意大利等國接連爆出財政問題,德國與法國等歐元區主要國家也受拖累。美國評級機構則落井下石,連連下調PIIGS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2010年4月26日,標準普爾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從BBB+降至BB+,淪為“垃圾級”;將葡萄牙信用評級連降兩級至A-。國際市場對歐元信心大降,歐元兌美元一路下跌,主要股指連續下挫,整個歐洲被債務危機陰霾籠罩。直至5月2日,歐盟與IMF才聯手推出3年內向希臘提供1100億歐元的救助計劃。然而,此時市場已被恐慌情緒控制,投資者對希臘可能陷入“國家破產”的擔憂無法平息,救助計劃未能達到預期效果,金融市場依然加劇震蕩。
對沖基金則借機蓄意沖擊歐元,致使歐元陷入自建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市場開始擔心歐元前途。為制止希臘債務危機蔓延,造成多米諾骨牌效應,歐元區16國首腦于5月8日召開特別峰會,正式批準救助希臘的1100億歐元方案,同時要求創建針對歐元區任何陷入困境國家的緊急基金,表示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歐元,一場史無前例的“歐元保衛戰”由此打響。
二、歐洲主權債務存在系統性擴散風險
雖然歐盟采取空前救援措施,但市場依然擔憂希臘債務危機向全歐擴散,原因是希臘債務危機只是歐洲債務的冰山一角。
第一,歐元區國家無一財政盈余且債臺高筑。據歐盟統計局統計,2009年歐元區整體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均超《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上限,而且經濟下跌4.1%,失業率上升至9.4%。經合組織(OECD)預測,2010年歐元區財政赤字將增至6.6%,政府債務升到84%,失業率達10.1%,GDP增長則低于1%。關鍵是,不僅小國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國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嚴重超標,而且西班牙、意大利、德國、法國(四國GDP占歐元區的76.8%)等大國的兩項指標均超警戒線,尤其是西班牙與意大利已被列入債務危機的黑名單PIIGS國家內。2009年,意大利財政赤字為5.3%,但政府債務高達118.6%,2011年將增到135%,債務風險明顯上升。西班牙債務危機已被引爆,成為繼希臘后第二個危機國家。2009年,西班牙財政赤字高達11.2%,為歐元區第二高赤字國,失業率達到18%,居歐元區最高。左翼少數派政府為預防危機發生,大力推進勞工改革并收緊銀根,由此得罪傳統盟友工會,被其他黨派孤立,政府陷入下臺危機,又遭評級機構惠譽降級,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政局相當不穩。
第二,小國債務危機引發市場大幅震蕩。6月初,歐洲上演了一幕節外生枝的驚恐場面。不被人關注的小國匈牙利,更迭后的新政府夸張性自曝“家丑”,聲稱“發現上屆政府偽造部分經濟數據,其財政狀況遠比先前預計糟糕”,在金融市場掀起巨大風波。歐美股市再次大幅下挫,歐元兌美元匯率跌破1.20關口,創四年來新低,歐洲主權信用違約掉期(CDS)報價大幅上揚,融資成本進一步提高。一個小國債務問題引發市場如此驚恐,緣由主要是遭華爾街金融風暴襲擊后的世界經濟異常脆弱,市場猶如驚弓之鳥,承受風險能力明顯減弱,對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做出過度反應。需要關注的是,波羅的海小國的債務與財政狀況很嚴重,任何內外星火都可能引發其債務危機,一旦發生難免再次上演匈牙利式“小鬼鬧宮”的驚恐場面。
第三,英國是歐洲另一枚隱形債務炸彈。英國的財政赤字問題非常嚴重。OECD統計,2009年英國財政赤字達11.3%,2010年將升到11.5%,高于歐元區平均水平,遠超過3%的警戒線。同時,英國的政府債務已超60%的警戒線,2010-2011年將分別增到78.2%和91%,而且其銀行尚有1000億美元的有毒資產未處理。新任首相卡梅倫上臺不久即宣布,英國的財政赤字問題比預期嚴重,將影響經濟、社會乃至居民生活,并將持續多年,因而削減財政赤字將是新政府的第一要務。7月13日,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英國國債達4萬億英鎊,比該機構之前的說法高4倍,比獨立分析人士評估的高2倍;平均每位英國人背負6.5萬英鎊債務,每個家庭需工作5年才能付清。
第四,歐洲內部債務/債權鏈錯綜復雜。這是歐洲的特殊情況,其國家間債務與債權鏈相當緊密,單一國家的債務違約會迅速擴散成系統性風險。國際清算銀行統計,希臘的債權人以歐洲為多,其中法國、瑞士、德國、葡萄牙分別持有750億、640億、430億和100億歐元;西班牙的債權人是德國、法國、英國,分別持有2360億、2220億和1140億歐元;而西班牙則持有葡萄牙860億歐元的債權。一旦歐洲債務鏈上任何環節出問題,均可引發大范圍系統性違約風險。加之,債務危機具有極強的傳染性,即使財政狀況相對穩健的德國、法國也會被卷入其中。因此,一國債務違約勢將掀起歐元區“地震”,投資者會對整個地區喪失信心。
三、歐洲債務昭示西方債務問題岌岌可危
據統計,2010年2月全球政府債務總額已突破36萬億美元,2011年將達40萬億美元。與歷史不同,當前全球主要債務國多為發達國家。雖然歐洲爆發債務危機,但美國、日本等債務狀況比歐洲更糟,財政赤字更高。故此,歐洲債務只是發達國家債務鏈上的一環,全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威脅是整個西方的債務危機。
一是西方債務呈結構性與長期化趨勢。OECD預測,2011年其成員國平均債務占GDP比重將超100%,財政赤字將達6.7%(2010年為7.8%)。如果不采取措施削減支出、提高稅收、改革勞動力市場、提高競爭力,此困境將延續至2025年。世界銀行報告認為,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債務與財政赤字達到不可持續的地步。2010年,七國集團(G7)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將達到113%,為1950年以來最高,而且形勢更加嚴峻。因為前者為戰爭所致,后者是金融危機后遺癥。關鍵是,所有發達國家均面臨人口老齡化,養老金與保健開支增加,且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面臨增收與減支兩難困境。IMF預測,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高峰期尚未到來,最困難時期應在2011-2018年,2023年債務占GDP比重只能降到80%,如果能削減政府開支達到GDP的8.8%,2030年前才能使債務恢復到危機前水平,即降至60%警戒線以下。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更悲觀,認為主要工業國(日本、德國、英國)將深受債務之困至2084年。可見,未來20余年西方國家將深陷債務危機不能自拔,無疑將影響其經濟持續發展,新興市場持有的債權安全風險將上升。前車之鑒是,拉美債務危機使其陷入“失去的二十年”,至今陰影仍揮之不去。前蘇東地區債務危機最終導致政經劇變,國家分崩離析。當然,歷史不會原本復制,西方國家會使用種種手段,將自身債務風險轉嫁給債權人。故此,其解決債務危機的路徑將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更大風險。
二是日本主權債務居發達國家之首。目前,日本國債高達600萬億日元,約占GDP的189%,居發達國家首位。二戰結束時,日本國債規模為GDP兩倍,國家幾近破產,今天的債務規模在重蹈當年覆轍。IMF估計,2010年日本國債占GDP比重將達227.3%。新任首相菅直人已多次表達對財政赤字的不安。OECD預測,2011年日本的財政赤字將由2009年的7.2%攀升至8.3%。學界對債務前景相當悲觀,經濟評論家淺井隆預言,2014年日本將“破產”;法政大學教授小峰隆夫稱,目前雖然日本財政狀況十分惡劣,但恐慌主要來自歐洲債務,因為“既然狼出現在希臘,民眾擔心這匹狼可能也會出現在日本”。據他估計,日本債務將在2020年前后超過家庭金融資產,從而引發政府是否能夠償還公債的疑慮。若政府維持財政擴張政策,日本財政可能在10-15年內崩潰,但若市場信心動搖,引爆點將更早到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債務主要由本國公民持有,即使爆發債務危機,對其他地區影響也較小。
三是美國債臺高筑是全球最大威脅。高失業率、龐大赤字、沉重債務,是后危機時代美國面臨的三大棘手問題。2009財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達1.45萬億美元,占GDP的11%,2010財年赤字將攀至1.56萬億美元,占GDP的10.7%,未來10年赤字累計將達9萬億美元。美國財政部公布,2010年美國國債將達13.6萬億美元,相當于每個美國人負債超過4萬美元;2015年美國國債將攀升到19.6萬億美元,占GDP的102%。評級機構穆迪公司預測,2010年底美國國債將達92.6%,2011年達97.4%,2013年更高達101%。穆迪據此認為,如果債務比率和利息成本繼續上升,政府又不采取任何穩定措施,可能將導致主權評級被下調。問題是,美國國債中相當部分由外國人持有,一旦爆發債務危機,全球債權人的財富將類似次貸危機那樣被吞噬。
閱讀3
危機影響與治理措施
一、危機沖擊力大但影響可控,經濟“二次探底”可能性小
(一)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歐洲債務危機的最大沖擊波首先體現在金融領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受歐洲債務危機影響,今年以來國際金融再次動蕩不已。全球股市連連下挫,美股曾日跌千點,數次跌破萬點大關;國際匯市加劇波動,歐元持續走貶,兌美元一度跌破1.20。估計,在債務危機困擾下,又有美評級機構推波助瀾,歐元對美元總體呈震蕩走低態勢,未來很可能跌回起點,即1歐元兌1美元。在歐債危機背后,總能隱約看到美國的影子,其中不乏兩種貨幣(美元與歐元)與兩種模式(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和歐洲的萊茵模式)之博弈。迄今,市場對歐洲債務問題及其蔓延的擔心仍未平息。另外,歐洲債務危機將使歐美銀行再次遭受損失。據統計,英國、德國、美國銀行分別持有的西班牙債務是希臘債務的7倍、5倍和3倍。美國銀行共持有“PIIGS”國家1900億美元債務。如金融機構為避險再次收緊貸款,可能導致全球信貸再次緊縮。
債務危機嚴重影響歐洲銀行業。6月21日,惠譽將法國巴黎銀行信用評級從AA下調至AA-。同日,標普調高西班牙銀行業的壞賬損失預期,2009-2011年累計信貸損失將達993億歐元,比之前預期多出177億歐元。這進一步加劇市場對歐洲銀行業的擔憂。7月19日,穆迪將愛爾蘭的評級從Aa1降至Aa2,主要原因包括該國債務上升、銀行救助計劃以及增長前景疲弱。7月28日,惠譽公布調查結果稱,主權債務危機使歐洲銀行發債融資幾乎陷入停頓,過去3個月歐洲銀行業一直處于資金缺血狀態,投資者對歐洲銀行業債務展期能力的擔憂日增。
(二)拖累世界經濟復蘇進程。歐洲債務危機的最大影響是,給脆弱復蘇中的世界經濟平添諸多不確定性,再次打壓投資與消費信心。在巨額救援機制背后,從危機中的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到大國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均開始緊縮財政。然而,歐洲是本次世界經濟復蘇中最薄弱地區,不少國家經濟尚未復蘇,一些國家經濟雖開始復蘇,但主要靠政策支撐。該地區退出政策本應晚于其他地區,但迫于債務危機各國不得不提前收緊銀根,加之歐元主導利率已處于歷史低位,貨幣政策幾無下調空間,其他復蘇動力亦無處可尋。市場普遍擔心,財政緊縮將使歐洲陷入“雙底衰退”。世界銀行認為,受債務危機和財政緊縮影響,今年歐元區經濟只能增長0.7%,2011-2012年將分別增長1.3%和1.8%,為全球復蘇最乏力的地區。OECD預測,今年全球經濟負增長的國家主要集中于歐洲債務國,包括希臘、西班牙、冰島和愛爾蘭,分別為-3.7%、-0.2%、-2.2%和-0.7%。歐盟委員會將歐洲債務列為經濟復蘇的主要威脅,認為各國削減財政赤字勢必拖累經濟復蘇。
另外,歐洲債務危機通過信心、金融、貿易、資本等渠道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影響。IMF總裁卡恩認為,歐洲債務危機是阻礙全球經濟復蘇的“最大挑戰”。香港《亞洲周刊》文章認為,歐洲債務危機表明全球金融海嘯并未過去,而是進入一個表面穩定、實際更脆弱的新階段,更大挑戰隨時會出現。眼下的直接影響是,各國宏觀經濟決策難度明顯加大,可能推遲退出政策實施,使未來通脹風險上升。然而綜合分析,歐洲債務危機不致導致全球經濟“二次探底”,原因有五:一是歐洲債務仍是歐洲問題,對其他地區影響可控;二是本輪世界經濟復蘇靠新興市場牽引,其復蘇勢頭依然強勁;三是美國、日本經濟復蘇明顯好于歐洲,且與新興市場互動性增強;四是二十國集團(G20)機制內國際合作能力增強;五是經濟周期性復蘇態勢依舊。結論是,歐洲債務危機使全球發展風險上升,但世界經濟“二次探底”可能性較小。
(三)導致歐盟內部矛盾加深。歐元區成立時,部分成員國并未滿足經濟趨同標準,而是在政治推動下“匆忙上馬”,債務危機使各國分化愈加嚴重,“統一貨幣、不同財政”的經濟模式運行難度加大。為應對債務危機而采取的財政緊縮措施,很可能導致一些國家出現更嚴重的經濟下滑和通貨緊縮風險。由于工資和福利水平的相對剛性,加入歐元區時就資質不佳的國家可能會出現新的社會和政治局勢變化。如果希臘政府迫于民眾壓力,最終無法執行過于嚴格的緊縮計劃而要求對債務進行重新安排,甚至被迫退出歐元區,歐元體系將受重大沖擊,并產生全球性負面影響。此外,危機使南北歐矛盾加深,且社會與政治風險上升,歐元地位受損,歐盟擴大步伐將減緩。近期,歐洲輿論甚至重提上世紀90年代“小歐元區”(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5個經濟較為趨同的國家)的話題,顯示未來內部協調難度加大,結構改革迫在眉睫。
(四)新興市場債權風險上升。與歷次債務危機不同,當前全球主權債務風險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受損方則為新興市場,尤以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東亞為重。風險不僅來自債務國償債能力減弱,更因其償債意愿下降。因為西方貨幣為硬通貨,只要其央行增發鈔票,使債務貨幣化,并借助通脹,即可稀釋債務。債權人面臨兩大風險:一是不能“印鈔”的歐元區國家的債務違約風險,因救助機制建立暫時消失,但未來依然存在;二是可以“印鈔”的美國、英國潛在的“紙幣”風險,即通過大量發行貨幣制造通貨膨脹使債務縮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各國外匯儲備投資不是在好資產與壞資產之間選擇,更多是在壞資產與更壞的資產之間選擇。這為中國外匯儲備的保值與增值提出嚴峻挑戰。
二、危機治理措施出臺,最困難時期已經過去
(一)急推財政緊縮政策。為解決債務危機,增強市場信心,歐洲各國開始大力緊縮財政。希臘:5月6日,議會通過財政緊縮方案,計劃3年內緊縮開支300億歐元,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由2009年的13.6%降至2014的3%以下。法國:5月20日,總統薩科齊宣布將改革財政制度,削減預算赤字,并實施養老金制度改革。法國政府還計劃修改憲法,將實現公共財政平衡作為政府永久性目標列入憲法。薩科齊承諾,3年內將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內。西班牙:5月27日,議會通過政府此前出臺的150億歐元財政緊縮方案。德國:6月7日,總理默克爾宣布,德國將在未來4年內削減財政開支逾800億歐元,以遏制預算赤字急劇增長(今年將超過GDP的5%),并為歐盟其他成員國“樹立榜樣”。英國:6月22日,財政大臣奧斯本公布緊急預算案,宣布將通過削減公共開支和增稅來減少財政赤字,從本年度到2014-2015財年,每年削減政府開支320億英鎊,從明年起將增值稅稅率從17.5%提高到20%,爭取在2015-2016財年實現結構性財政平衡并出現盈余,削減財政赤字的80%將通過緊縮財政實現,20%靠增稅完成。這是二戰后英國最“緊縮”的預算案。意大利:7月15日,參議院通過了政府提出的249億歐元緊縮公共開支預算法案。這項法案設定的目標是將財政赤字占GDP比例今年減少到5%,2011年減到3.9%,2012年減到2.7%。此外,愛爾蘭、葡萄牙等國也公布財政緊縮方案。至此,歐洲正式步入“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艱苦”時代。
另外,日本政府也于6月22日公布了“十年財政戰略”,計劃在2015財年前使財政赤字占GDP比例比2010財年減少一半,2020財年前實現盈余;2021財年后,國家和地方公債余額占GDP比例將穩步下降。6月召開的G20多倫多峰會也要求,發達國家在力求穩定復蘇的同時,2013年前將財政赤字減半,2016年前穩定并減少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
(二)加強內部經濟治理。為防止債務危機升級,歐盟相繼出臺1100億歐元希臘救助方案和7500億歐元歐洲穩定機制,力求希臘不會出現主權債務違約并試圖阻止危機在歐元區擴散。但救助方案被指“治標不治本”。市場信心依然不足。對此,歐盟及其成員國又迅速邁出了加強內部經濟治理改革的步伐,試圖通過強化財政紀律、增進經濟政策協調、消除成員國間經濟失衡和建立一套永久性的危機應對機制來修正歐元區固有的體制性缺陷,避免危機重演。
在6月17日召開的歐盟峰會上,歐盟表示將加強內部經濟治理,強化財政紀律和加強對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監督,以免債務危機重演。歐盟領導人同意,自2011年開始,成員國預算方案接受歐盟委員會評議,對違反財政紀律的成員國實施懲罰。歐盟領導人還要求擬定一套評判體系,以及時發現成員國之間的競爭力差距和經濟失衡狀況。
(三)著手經濟結構改革。面對日益嚴峻的宏觀經濟風險,在削減財政赤字的同時推行結構性經濟改革顯得日益迫切。5月25日,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范龍佩、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和歐盟委員會負責經濟和貨幣事務的委員奧利·雷恩共同呼吁歐盟成員國將鞏固財政和結構性改革并舉,因為只有實現經濟增長才能實現削減赤字的目標,提高未來歐盟經濟增長潛力。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5月31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警告,不應“一味厲行節約”,還要找到“通往繁榮的可持續道路”,應抓住發展中國家增長提供的機遇,避免步入“失落的十年”。
6月17日,歐盟峰會通過未來10年歐盟經濟發展規劃,即“歐洲2020戰略”,要求通過提高歐盟經濟競爭力、生產率、增長潛力、社會融合和經濟趨同,使歐盟經濟走出危機并變得更強大。根據這一戰略,未來歐盟經濟發展目標是:實現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靈巧增長”;以提高資源效率、提倡“綠色”、強化競爭力為內容的“可持續增長”;以擴大就業、促進社會融合為目標的“包容性增長”。為此,歐盟在創造就業、增加科研投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高教育普及率和消除貧困等5個核心領域確立了量化指標。新戰略重在推動結構性改革,消除制約歐盟經濟增長的瓶頸,充分挖掘增長潛力,使歐盟經濟重回可持續增長軌道。
7月21日,IMF發布報告建議,歐元區當前應加強政策協調,制訂有力的中長期調整計劃,建立財政可持續性,實施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增長,要找出銀行體系的薄弱環節,并從根本上進行重組。同時IMF建議,歐元區通過實施完善的財政和結構政策,完成地區范圍的金融穩定框架,來建立有效的經濟和貨幣聯盟。
hjbOuqDGZgk0oYoan3to4uVX+Op5QAaredVb/tB+jNw= (四)進行銀行業壓力測試。為平息市場對歐洲銀行業健康狀況的猜疑及提高透明度,6月17日召開的歐盟峰會宣布對歐洲銀行業進行壓力測試。7月23日,歐洲銀行業監管委員會公布了歐洲銀行業壓力測試結果。結果顯示,歐洲大多數銀行“健康狀況”良好,有能力抵御可能出現的經濟“二次探底”和主權債務危機的雙重打擊。在參加測試20個歐洲國家的91家銀行中,絕大多數都順利過關,只有7家不合格,其中除德國地產融資抵押銀行外,另有1家來自希臘,其余5家均為西班牙地方銀行。7家銀行只需注資35億歐元,即可抵御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英國、荷蘭、意大利和北歐地區的銀行在壓力測試中表現出色。91家接受測試的銀行資產規模占歐洲銀行業的65%。歐洲銀行業監管委員會稱,整體上,這91家銀行在假定的最糟糕情形下,核心資本充足率雖將從2009年的10.3%降至2011年底的9.2%,但仍高于測試所設定的6%的“安全線”,表明歐洲銀行業總體依然健康。
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歐洲銀行業監管委員會發表聯合聲明稱,這次壓力測試公布的信息將確保外界了解歐洲銀行業狀況,對恢復市場信心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聲明強調,這次壓力測試所假定的最糟糕情形實際上不太可能發生,但絕大多數歐洲銀行仍經受住考驗,由此可以證明,歐洲銀行業作為一個整體能夠抵御住可能出現的宏觀經濟風險和金融沖擊。歐盟官方雖對壓力測試結果表示滿意,但分析人士認為,整個壓力測試是一場平復市場擔憂的“政治游戲”,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如愿打消投資者疑慮仍是未知數。
(五)加強金融改革與監管。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打擊金融市場投機、加強金融監管的呼聲就一度高漲,但在過去一兩年,西方國家在這方面進展緩慢。最明顯的例子包括金融衍生品市場仍無序發展,信用評級機構未能得到有效監管,二者成了歐洲債務危機的“加速器”。對此,歐元區國家領導人再次提到金融市場投機以及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問題,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9月2日,歐盟成員國代表和歐洲議會達成協議,同意從明年起成立三個歐洲監管局,分別負責對銀行業、金融交易和保險業進行監管,同時成立一個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進行監管。在此新的監管體系下,三個監管局將有權監督各國監管機構執行歐盟的相關法律法規,并對這些機構發布指令或提出警告。在涉及跨國金融機構管理時,如果各國監管機構之間發生爭議,歐洲監管局可以進行調停,調停結果具有法律約束力,監管局還可直接對相關金融機構下達監管決定。此外,歐洲監管局還將有權對特定類型的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金融活動進行調查,評估其給金融市場帶來的風險。在緊急情況下,歐洲監管局可以臨時禁止或限制某些有害的金融活動或者金融產品,并可提請歐盟委員會提出立法建議,永久性禁止這類產品或活動。
至此,歐盟終于建立起對宏觀經濟政策與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泛歐監管機制。這是從金融危機與債務危機中得出的最大教訓,也是最大收獲。可以預見,未來歐洲一體化發展依然不會一帆風順,但爆發類似如此險峻金融危機的風險應能降低,長期發展可能更健康并趨于相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