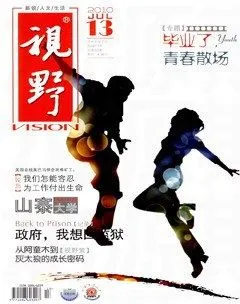可以安放愛情的城市
那一年我和森大學畢業,我不甘心與他回我們故鄉的小城,做一個平庸的文員或是小報編輯。森極力挽留,最終還是沒能用他想像中安穩妥帖的小城生活,將我說服。舍不得與我分手,他便惟有與我一起去北京,尋找我夢想中的城市。
安頓下的第二天,便有一家報社同意與我們面談。欣喜若狂中,竟忘了問清楚,究竟要怎樣才能到達報社所在的大樓。怕報社那邊敏感,這樣一樁小事都想不周到的人,還想當什么記者?只好飛快地買了一張地圖,在風沙肆虐的街頭,兩個人頭抵著頭,慌慌地尋那個與我們的希望相連的地址。
不曾想,地圖上沒有標明公交路線。我是個急性子,看著時間匆匆地溜走,離約定的時間不到半小時,竟然哭了出來。森耐心地哄我,又攔住幾個路人問,他們都紛紛搖頭,說不知道。好不容易等到一個看似在鍛煉的本地人從馬路對面經過,我們很高聲地向他打招呼,請求他停一下,那人卻在我們聲嘶力竭的呼喊聲里,漠然地看我們一眼,便又不停步地走過去了。
許多漂亮又氣派的車,風一樣刮過來,又刮過去。揚起的灰塵,迷了我已經紅腫的眼睛,讓我連不遠處那座米黃色大樓上掛著的廣告牌都看不清楚。森忍不住,沒經過我允許,便打那家報社的電話,想問個明白。我知道他是個說話不怎么流利的人,只好在他按鍵前,自己奪過來打。
風愈加地大,手機的信號,在明顯失了熱情的編輯再一次將到達方式告訴我時,竟突然變得很不清晰。我斷斷續續地只聽見“5路車”、“步行十分鐘”幾個字,鼓足勇氣想再問一遍時,那邊已“啪”地掛斷了。
不知道5路車從哪兒坐,只好拼命地揮手攔出租車。最后,一個大胡子的司機終于漫不經心地將車停下來,載我們去那希望的所在。五分鐘后,車停下來,原來那座米黃色的大樓,就是我們苦苦尋找的且只需步行十分鐘便可以到達的報社地址。知道被這個一臉冷漠的司機騙了,卻來不及像平時那樣討回公道,便付了錢,慌亂不安地坐上電梯,在十二樓的一個辦公室前停下來。匆匆地瞥了一眼手表,離約定的時間,已過了五分鐘。
那個編輯輕描淡寫地看完我們的材料,說:“如果你們愿意,可以先試做一個月,從最低的‘馬路記者’開始干起。干不下去,隨時可以另謀高位。”原本準備好的一番陳辭,在他的“今天到此為止”的逐客令里,終于沒有了絲毫說出來的必要。轉身出門的時候,一直懶得抬頭看我們一眼的編輯,突然站起身來,走到我們面前說:“其實,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來北京的。如果在繁華喧囂的大道上總是迷路,不如在寂寞卻安靜的小路上,踏實安穩地一步步走……”
已是風停,我和森在一個街頭,捧了大大的地瓜,慢慢地啃;直吃得胃不再空虛,心里那個一路狂奔的信念,住了腳,一臉溫柔地朝我們回望。
我們一步步爬上一座數不清有多少層的大樓,從窗戶里往下看,見那蛛網一樣的路,密密麻麻的,在這個我一直覬覦著的城市里,那么高傲地向四面伸展,車和人,在它的上面,原只不過是一只小小的飛蟲,或是螞蟻。
我苦苦支撐著的夢想,終于在這樣的一天里。徹底地破滅。我趴在森的肩頭,卻沒有流一滴淚,祭奠這灰飛煙滅的希望。因為我知道,還有另外一個小而安靜的城市,可以讓我和森,及我們只能用柴米油鹽滋養著的平凡愛情,永遠不會迷失了方向……
(姚小梅摘自《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