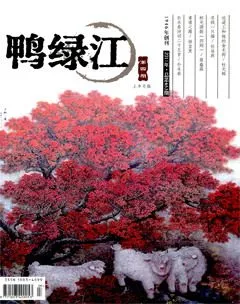馬橋頭
嚴正冬,男,生于1982年。江蘇淮安人。畢業于蘇州大學文學院。曾在《萌芽》《長城》《青春》《作品》《百花洲》《青年文學》等刊物發表作品40余萬字。其中,小說《上海親戚》獲第三屆“四小名旦”青年文學獎。散文《講古的夜晚》于2008年初被收入《大學語文》(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現供職于淮安日報社副刊部。
馬橋頭是一處小集鎮,它依傍著從城里通往鄉村的那條石子路,身側還有一條不窄不寬的灌溉渠。每年夏天發大水的時候,這條河里總會漂著一些來歷不明的雞鴨豬狗,臭烘烘的,臨河人家推門就能聞到,這些肚皮朝上的死貨順著水流一路飛奔,一天半日的工夫便沒了影,所以,沿途仍然有人在碼頭洗菜淘米——這條河的確有了年歲,可它帶走了多少人事,卻改不了庸常日子里的生活習慣。
有河便有橋,此地以馬姓為主,在這里架起的橋自然就叫馬橋。也因這橋大大方便了周圍的鄉親,一年四季,春耕秋收,走親戚的、候車的、過路的、到鎮上趕集的……人來人往都要經過這兒,后來不知什么時候,此處就成了小小的集鎮中心。盡管規模很小,零零落落,但畢竟已是小集鎮的樣子了。
什么樣子呢?早晨有賣豬肉的、賣魚的、豆腐攤子、燒餅爐子、炸油條賣豆腐漿的擔子,還有用柳條筐子裝著地里的青菜來賣的。說實話,生辰婚喪辦宴席的人家根本不會到這里來買菜,這點東西哪拿得上桌面子?家常吃吃了不得了。辦大事的人家大清早或者提前一兩天就會到鎮上去配菜,掏出廚子的菜單一樣一樣地買,蔬菜葷菜冷盤子干貨,鎮上的菜場可是都齊全啊。逢年過節呢,魚肉菜蔬一般人家也不愿意到這兒來買,價錢貴又不好挑,熟人熟事的,有句話怎么說的——鬼挑熟的昧。所以說,馬橋頭在當地人的心目中,也沒有什么地位可言,至多是尋常日子里,大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買兩袋鹽打一斤醬油,應急一下罷了。偶爾有人在此割肉買魚,大概也是家里突然來了親眷,臨近午飯的辰光實在沒有辦法了。當然,這些賣主自身也心明眼亮,他們多是一些不急不躁的老頭老太太,每天很有規律地做著波瀾不驚的生意,其實質更接近于消閑聚會:太陽出來出攤子,坐在隨身攜帶的凳子上一邊擇菜一邊互相拉家常,東家長西家短,說著說著,差不多午飯時間就到了,于是他們不緊不慢地收拾物什,準備打道回府,而雨天雪天呢,他們一律給自己放假。
除去以上這些從四下里匯集至此的攤子擔子,馬橋頭還有十來戶在此建房落戶的人家。房子都不怎么體面,因為地方太擠了,有的人家大門都被夾在狹長的巷子里,有的人家還是泥砌的墻面,屋頂就更簡單了,幾張石棉瓦一蓋,完事。還有的在原先的老屋上新添一層,成了有陽臺的樓房,但顯得很扎眼——下半身的舊房子灰不溜秋,而上頭卻用瓷磚裝飾一新,那種不協調連三歲小孩都看得出來。很快,這些人家的屋子自然而然成了做生意的鋪子。深究起來,他們做生意與那些做豆腐賣菜的又不太一樣,他們是一門心思撲上去,態度堅決,打算一輩子就干這個營生了。剃頭的剃頭,做衣服的做衣服,開診所的開診所,各家都擺出打江山的派頭,用不著摩拳擦掌就上戰場了,說不準這戰場就是一輩子,或者更長,經子子孫孫一直傳承下去。從此,這些人家的生活就與馬橋頭緊緊系到了一塊兒,過日子和做生意變得難解難分——外頭的柜臺上堆放著滿滿的貨物,顧客一腳跨進來,一邊斟酌挑選著,眼睛的余光已經透過旁邊的門洞看見了店主家正在奶孩子的女人,那當兒,女人旁邊還蹲著一只爐子,飄著裊裊的肉香……
雜貨店
緊貼石子馬路的第一間房便是馮瘸子家。門朝東,窗子開在北面,靠近路口。從前他腿還沒有斷的時候,這家雜貨店就開在這里了,但那時的主人是他父母。那會兒,他還是個毛頭小子,正在讀初中,說是成績頂呱呱的很有希望,家里的打算是讓他報考一個中專或師范,將來就是鐵飯碗了。退一步講,就算考不上,回家學個手藝,木匠瓦匠漆匠什么的,也能混一口飯吃。老兩口原本就沒指望讓孩子守著雜貨店,一個小店,賣些零零碎碎的東西,掙不到幾個錢,勉強熬著,要是把孩子一輩子的前途押在上面就更不值了。
其實,值不值,人說了并不算數,人是沒有前后眼的,攤上什么災禍逃也逃不掉,這就是命。那年春天的一個清晨,下著厚厚的大霧,對面望不見人,他出門推著車子準備上學,剛上馬路就遇上了一輛卡車。他在那場大霧中暈死過去,醒過來之后就成了馮瘸子,就是今天這個胳膊里架著一雙拐、褲腿下面空悠悠飄著的馮瘸子。
斷了腿,書也不讀了,馮瘸子慢慢接受了無可挽回的現實,開始跟著父母打理雜貨店。他本來就是向上要強的人,做起事來樣樣不落人后,平時跟別人一塊兒到城里去進貨,他能算能弄,簡直比手腳伶俐的人做事還要活絡周全。后來他父母相繼過世,店里只剩下他一個人,每年到了年終歲末,跟別的生意人一樣,他拿個賬本夾著雙拐挨個去那些欠賬的人家收賬。換了其他人還好找托辭推搪玩花頭,可是,人家一個沒腿的人年關上門要債,看你給不給?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眼看著馮瘸子一年一年大了。離三十不遠的人,橫在面前的難題便是婚姻大事。是呀,腿斷了沒有法子,但不能一輩子就獨和尚一個,終歸要成一戶人家的。旁人也是這么想的,不少同情馮瘸子的婦人都一心想著給他尋個合適的對象。不久之后真的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姑娘,家在北鄉里(當地的地域界定,北鄉里以窮著稱)。那天,兩人在雜貨店里見面,他說了不少話,而自始至終人家半句都沒吭聲,他以為沒戲了,當晚便搶先回絕了人家,事后才曉得原來那女的竟是個啞巴。這門親事沒成他也沒后悔過,只是覺得心里堵得慌,為什么呢?因為別人已把他馮瘸子歸入了另一類,介紹對象的依憑均以殘疾為準,這是他萬萬不能接受的!之后又有人相繼給他介紹了幾個殘疾姑娘,一概都被他否決。漸漸的,就沒什么人再給他說媒了,倒是他自己心里有了新的盤算。這盤算便是后來花錢托人從云南帶來了一個女人,實質是買,買回來后就直截了當地結了婚,一年后喜得大胖兒子。眼看著日子一天比一天明朗,生意也蒸蒸日上,往來的熟人照面時總要打趣地說,馮瘸子,抱兒子啦,恭喜恭喜,散喜煙啦。他聽后樂呵呵的,眼睛瞇作了一條線,趕緊把一支煙恭恭敬敬地遞上前去。
然而,這幸福到底沒有延續下去,孩子兩歲未滿的那年冬天,女人竟不聲不響地跟人跑了。有人說侉子(當地對口音不同的異鄉人的稱呼,此處指馮瘸子的女人)是和到店里買香煙的外地司機一起走的。起初,親眷熟人都幫忙找了好一陣子,但一直沒有任何音訊,時日一長,最后連馮瘸子自己也死心了。不死心也不行,女人沒有了,日子照舊要過。不知不覺中,兒子一天天地長大,馮瘸子的生活又開始有了新一層的盼頭。
那時候,在馬橋頭,來來往往的人經常看見一個虎頭虎腦的男孩子,肉乎乎的,貓眼團臉,他被大伙你抱過來他抱過去,沒有哪個不喜歡,誰見了都要上去親一口擰一把。那當兒,正在屋里屋外忙活不停的馮瘸子心里應該是暖洋洋的吧。
衛羊布店
每天,隔著玻璃窗,人們都能夠看到里頭花花綠綠的布匹,還有坐著踩縫紉機的戴花姑娘。這便是布店。門廊那兒懸著一塊白底紅字招牌,字是紅漆寫上去的,衛羊布店。一清二楚,店主便是叫衛羊的男人。三十出頭,頭發有些自來卷,往后梳起,高高地浮著,使他本來并不太高的個子高出了許多。他皮膚蒼白得厲害,病色的,濃眉瘦臉,整個人看起來像電影里舊時大戶人家的少爺。
在馬橋頭這地方,他委實是與眾不同的一個。一個孤兒,在鄉鄰親眷的相幫下長大成人,吃足了苦受足了罪,十九歲獨自跑到上海去謀生,半年后跟一個能做他娘的女人結了婚,也不叫結婚,駢居吧,鄉人都是這么說的,不久便添了一個女兒……都說他發的是那上海老女人的財,三年后他帶著女兒回鄉,之后就花錢在馬橋頭買了兩間房,打通后成為一大間,開起了裁縫店。店鋪的開張儀式非常隆重,鞭炮響了大半天,又是花籃又是剪彩,還在鎮上的人民飯店擺了飯局,整整十幾桌。這是1992年前后的事情,那時候城里的摩登風氣微微吹到小鎮上來,然后輾轉再吹到馬橋頭。人們的思想開始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許多念頭躍躍欲試的,帶著一點點惶恐。大多數人仍安分地過日子,可心里并不平靜,他們的眼睛驚奇地張望著外面,這一天一個樣的世界啊。隨后小鎮陸續出現了美發廳、臺球室、錄像室、小型商場等。人們的膽子一節節地拔高,心里開始盤算著什么,青年人對這一茬接一茬的變化是欣喜激越且樂于接受的,老人們則實在有些暈——世道怎么了,人心怎么都變成這樣?
布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不單是衛羊的手藝好,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上海待過,做出來的衣裳就是洋氣,穿他這里的衣服就頗有些城市人的味道。青年人最熱衷追趕潮流,這潮流旋風似的刮著,衛羊的名聲漸漸傳開了,打響了。此后經常有不少外鎮的男女成群結伴地到馬橋頭來做衣服,慕名而來的人見到衛羊的模樣就更加篤信不疑。從此,衛羊這個名字就像一個醒目的商標為許多人喜愛著、惦念著,現在的很多廣告是不好比的,人家那才叫實實在在的做工——款式料子樣樣都看得見,半點也不摻假,花錢買的完全是信賴和驚喜。而上了年紀的人對衛羊布店的態度仍舊沒什么改觀,他們喜歡循著老習慣做事,譬如說做衣服,他們大半輩子都在張桂蘭那兒做,也就是馬橋頭過了橋拐一點,人家可是老資格老裁縫啊,不少老人的壽衣都是在那兒提前做好的。也沒什么,張桂蘭和衛羊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無事。能有什么事呢,黃牛角水牛角——各歸各,各做各的生意而已。
過了幾年,衛羊被迫又結了一次婚。事情緣于他用皮尺給一個姑娘量尺寸,量完之后那姑娘便哭嚷著說衛羊的手到處亂摸,過后她家里來了不少人,鬧得不成樣子……鬧了十幾天,后來終于談妥了:人家黃花閨女遇著這種事,以后哪還有臉見人?只能嫁給你了!一開始,他女兒就與這個晚娘水火不容,為這衛羊跟她隔三差五地吵架,兩口子折騰了好幾年,最后實在過不下去,就離了。而后,衛羊就一直獨自帶著女兒過,再沒有結婚。一些喜歡嚼舌根的婦女則在背后說,他結不結婚都一回事,店里那么多姑娘,想睡哪一個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有的還巴望不得呢!
是呀,那時候,布店里確實有了不少學徒,她們都是附近的女孩子,讀了幾年書,小學或初中畢業,之后父母便央熟人讓她們到這兒來學裁縫。說實話,大伙還是挺佩服衛羊的手藝,不然哪來這么多的學徒。而人家結不結婚的說法,也只是旁人瞎議論罷了。
理發室
馮瘸子的對門是一間巴掌大的理發室,兩張大方桌就能把它塞滿。墻上刷著黃影影的石灰,沒有招牌,門是學校教室的那種,淡藍色,暗鎖。屋子委實太小了,里面的東西更加寒磣:一張梳頭桌子,迎面的墻壁上貼著一樽到處是裂痕的鏡子,桌上橫七豎八地躺著剪子、推子、梳子、掏耳爬之類的東西。鏡子前安放著一把可以前后左右旋轉的搖椅,坐墊又松又軟,坐在上面倒是一種享受,只是椅身剝了不少漆,像牛皮癬一樣難看。此外,角落里還有一個鐵制的洗臉架子,上頭卡著一只慘綠色的盆,旁邊的爐子專門燒水給客人洗頭。
這屋子真的很小,三兩個人一進來連轉身都覺得困難了。叫庚成子的矮老頭便是屋子的主人,矮墩墩的一個人,顴骨很高,總穿著不太干凈的大褂子,一直拖到腳底板,且還是個沙眼,動不動就淌眼淚。所有這些均給人一種壓抑感,也因此對這剃頭師傅生出無限的憐憫之情。
其實都是錯覺,原來庚成子一家的生活相當殷實。他本人五十歲不到,白日里在馬橋頭剃頭,生意還說得過去,老主顧不少,常來的孩子他也能叫得上名,甚至連他們上回剃頭的日子還清楚地記得。晚上他不住在這里,天暗了就把工具收起來,取了抽屜里的錢——賊還是要防的,鎖了門回家去。他女人也是個矮子,非常勤快,平時養雞養鴨,還做針線活,地里的活計忙得緊緊當當的,吃得苦,農忙從來不叫幫手。到了臘月里,她還要去夾堆上割蘆葦背回家,編毛窩子(一種御寒的鞋子,由蘆葦編成,既結實又暖和)是她的絕活,大大小小的尺碼她要編上一大籮筐,等到下雪前趕個晴天挑到鎮上去賣,買的人特別多,賣個好價錢絕對不成問題。女兒呢,雖是抱養別人的孩子,但結婚后對老兩口子還說得過去,每年八月半過年呀都要送禮,還塞錢,多少親生兒子還不如呢。如今女兒出嫁已有六七年了,外孫子都那么大了……
還是說他的手藝吧。從前學徒,老師父性子急脾氣犟,庚成子個矮話少,是幾個徒弟中最老實忠厚的一個。那時他眼慢手笨,沒少遭客人的斥責,師兄弟的嘲笑和師父不絕于耳的責罵更是家常便飯。這些都沒什么——老話不是說,手藝不是學出來的,而是罵出來的打出來的。一晃幾十年過去了,那在鎮上的犟師父早已過世,當年的幾個師兄弟,混得都不孬,大家彼此離得不遠,平時碰面的機會很多。就說過去那個小李子,還是最后一個入門的,現在人家已經在鎮上開起了美發廳,風風火火的,里面一大撥人,修剪吹燙,好不熱鬧,跟戲班子差不多。也有不堪的,同是鎮上的劉三,卻是個惹事的主,打架殺了人,末了被逮捕起來,留下老婆和兩三歲大的兒子。記得那年開審判大會的時候,人山人海的,喇叭里言辭洶洶,說是連劉三在內攏共槍斃了十幾個。話說回來,看得自嘆弗如或者驚心動魄,別人的遭際于他庚成子又是無干的,他本是想過安穩日子的人。
也不知從何時起,他打心眼里喜歡上了剃頭這一行,假如有一天不到馬橋頭心里就特別堵得慌,渾身都不自在。對于自己手頭上的功夫,他很有信心,他給幾十年的老主顧推鬢發、剪鼻毛、刮胡子、掏耳朵。修面,現在的理發店里幾乎沒有人會這個了。滿月孩子的頭他也剃,對門馮瘸子兒子的頭就是他剃的,中間留一小撮,旁邊光溜溜的,仙桃似的。有時他也會被人家請到家里去,多是喪事,老人死了,家里的子孫后代都要剃頭,挨個兒地排著隊到他跟前剃,那一天他忙得連喝口水的閑暇都沒有。而平日里,剃的最多的還數學生模樣的孩子,通常,他們被一個個面色蠟黃的婦女領進來,做娘的只說一句話:盡量剃短一些。他知道她們的心思,剃短了才挺得時間長啊。孩子剃個頭才五毛錢,可見過日子都不太容易。于是,他笑道,板寸頭,我曉得的。
想起來,也有遺憾。他一個徒弟都沒有,學徒的全都到鎮上或者更遠的城里去了。碰到人們到鎮上趕集的時候,有許多人從馬橋頭路過,老遠的常聽見有人笑著說,庚成子,你也太落伍了吧,店里火鉗有嗎染頭行嗎?他光笑不答。這時候,他想,剃頭就是剃頭,那些烏七八糟的事情他才懶得去管。
這馬橋頭烏七八糟的事情還真不少。就說鹵肉店的王家和李家吧,算起來還是表親,兩家女人卻常常當街拌嘴吵罵,罵得那個狠勁呀,咬牙切齒的,所謂同行冤家真是一點也不假。吵架時一般雙方的男人都不參與,不插嘴也不制止,躲得遠遠的。兩家的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燈,嘴皮子相當,小手段也都會耍一些。倘若今天李家的生意略微好一些,明天王家女人就會對人講李家賣的都是死豬肉,她繪聲繪色地跟人講,看到了嗎,那肉紅得不正常啊。風聲很快就刮到李家耳邊,這次李家女人不吵不鬧,以牙還牙也玩起了陰毒的招兒,她逢人就嘀咕王家的女人查出來是肝炎,唉呀,傳染病治不清爽的。終于,后來的某一天傍晚,兩個女人竟在門前動起了手,又是食刀又是棍子,兩家的男人恰巧都不在家,等左鄰右舍跑過來拉勸時,兩人已撕打成一團,衣衫沾滿了血跡。可是到了晚上,兩個女人一前一后跑到旁邊的診所里去涂藥包扎,她們見了面當作沒看見,徑直和先生(當地對醫生和老師都叫先生)說話。這還不算什么,第二天天亮了,她們照舊生爐子熬柏油拔豬毛,見了熟人邊嬉笑邊打招呼,好像昨天什么事也沒發生似的。
還有炸油的和修電器那兩家,也是一天到晚不得安生。都說炸油的使詐騙了顧客的菜籽油,可惜誰也找不著證據,但疑心依然很重。也不能怪顧客,半袋子的菜籽連一壺油都炸不滿,當然會懷疑。但附近又沒有別的炸油鋪子,到鎮上去路遠不說,還得排隊,所以只好來此處,因此那里天天發生口角,都是些車轱轆老話題。不過,這家的生意一直做著,且很紅火。那修電器的馬四手腳也不清爽,總是把顧客電視機錄音機里的零件換走,被當場逮住了還死不承認,簡直吵翻了天,后來生意逐漸清冷下來,他又改修手表,結果呢,還是成天跟人吵。文明人說,人品這樣子沒辦法的,也有人很直露地說,狗改不了吃屎。
倒是忘了說,我外婆家老早就住在馬橋頭了。就在馮瘸子家的隔壁,門藏在巷子里頭,巷子真的很窄,勉強夠一個人推著自行車進去,故容易被人忽略,但走進去便豁然開朗。三口鍋的灶頭,一層連一層的蒸籠,幾只不大不小的和面盆,以及成捆的柴禾,堂屋的門后還堆放著雪白雪白的面粉。一目了然,這里專門為人加工饅頭,分扁的和尖的兩種,尖的點了洋紅、洋綠就變成了很好看的壽桃,價格要貴一點,顧客買回去給人祝壽。那時候,我總是管不住自己的手,到處亂摸那些白白胖胖的饅頭。為這,手心手背不知挨了小姨舅舅們多少回痛打,每次連打帶嚇,但就是不長記性。好在后來慢慢長大了,長大了就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了。
這些都是十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住在外婆家。三歲到十三歲,這中間,一個孩子人生中最美好的光陰在這個叫做馬橋頭的小集鎮上駐足停留,他看見這個世界的人來人往和喜怒哀樂,從此刻在記憶里,一輩子也忘不掉了。
責任編輯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