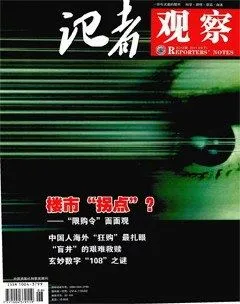父親
父親的身影浮現在我的眼前,父親的聲音縈繞在我的耳畔。清明節,恍惚中,我又來到父親墓前。那松柏更加枝葉繁茂,青翠欲滴,我欣喜地發現老樹周圍長出許多小樹,小樹蔥蔥郁郁,生機勃勃,增添了這片公墓的綠色,構成一道醒目的風景。
我緩緩走近父親的墓邊,父親的身影逾發清晰地呈現在我的眼前,仿佛站在云端,看著今天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臉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父親少年時,祖父母養育7個子女,先后夭折4個,只剩下父親與兩位伯伯,家貧,無錢供讀,父親上山砍柴、田邊放牛,什么苦都吃過。有一天放牛回家,路過私塾先生門前,父親被讀書聲吸引了,站在窗外聽先生講課,用樹枝在地面上寫字,一連好幾天,被先生發現,先生讓父親讀給他聽,寫給他看,由于父親聰慧,先生喜愛,就免費讓父親上學,父親勤奮好學,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縣中學,先生一直資助父親求學。先生晚年時,父親經常去看他,先生去世時,父親悲痛欲絕,以子女的身份為先生安葬。后來父親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廈門大學,這時的父親就開始半工半讀了,夜晚在一家郵政部門做工,常常到半夜12點以后下班,清晨四五點起來上學。尤其是冬天,父親在河邊敲開冰層洗臉,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完成了學業。
父親畢業以后,一生從教,培養了無數的優秀人才,從他存留的學生像冊中可以看到許許多多鮮活的面孔,他們一批批地走出校門,猶如一棵棵小樹,長大成人,成為國家的棟梁。
在父親任職的校園里,每一個角落都留有父親的腳印,校園的每一個教室都灑下了父親辛勤的汗水,三尺講臺留下了他的音容笑貌,三寸粉筆染白了他的雙鬢,晝夜長明的燈火伴著他備課、批改作業。長期伏案工作,父親不幸患了眼疾,眼鏡換了一副又一副,但仍然年復一年不知疲倦地工作。父親教幾何,不用圓規,熟練到用粉筆可在黑板上隨手畫圓,他教的學生個個成績優秀。
父親愛生如子,一次我得了肺炎發高燒,父親正準備帶我去醫院就診,就在這時父親得知他的一位學生突發急病,父親囑咐我幾句,就立即背起他的學生去醫院看病。父親說:“學生家長把孩子交給了老師,老師就是學生的父母,學生就是老師的子女。”當時的我懵懂,為這還流了眼淚。
大荒年時,家中無米下炊,常以野菜充饑。當時父親掌管學生的伙食。有一天,一位學生多交了lO斤糧票,那是一碗稀飯就能救活一條人命的年代啊,何況10斤糧食呢?父親拿著糧票,眉頭皺都沒皺一下,立即把糧票還給了學生,自己仍然天天吃野菜。有人說父親癡,我說父親癡得有價值,心潔無瑕。
在“四人幫”橫行時,父親也沒有逃脫噩運,被打成臭老九、反革命,下放到農場勞動。紅衛兵把百來斤重的麻袋壓在父親的背上,但父親沒有被壓垮,毅然挺起了脊梁,仿佛像一棵松樹,不怕霜打雪壓,依然傲立。父親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仍然給學生解疑答惑,因此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但父親沒有屈服,依然如故,艱難地一路走來,終于迎來了曙光。
父親的晚年,常常拉著二胡,唱著京劇,品茶、讀書、看報、散步,終在1987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此刻,我站在父親的墓前,微風吹過,紙煙揚起,而青翠的松柏更加挺拔、茁壯。我覺得父親的身體雖然像這青煙一樣升上了天空,但他的精神卻像松柏一樣常青,永遠站在我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