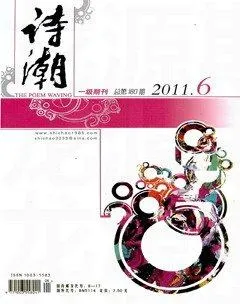要有一種鋒利感
在接受一家媒體的訪談時,劉立云說:“我對好詩的評判標準就是要觸動,有感想,有些寫作的氣息。也就是說如果你去觸碰它,要有一種鋒利感。”
這與他的軍人身份及軍事題材的寫作有關。38年軍事生活給他的浸潤、滲透和滋養,使他過得緊張而充實、綿密而快樂。他試圖用詩歌去“觸摸刀尖上的鋒芒、觸摸烤在鋼鐵上的藍,而這樣的一種藍,是天空的藍,海洋的藍;火焰的藍,刀鋒的藍”。因為軍人這個職業,“與虎狼/為鄰,危險而又兇狠,就像/一只奔跑的缸,我隨時都將/被風打碎,或者我就是風/凌厲并兇猛,我呼嘯/我怒吼/只為打碎另一只奔跑的缸”(《步兵們》)。
這與他的敘述方式有關。在一般人看來,小說是敘述的,詩歌是抒情的,這似乎成了兩種不同體裁的嚴格界限,殊不知詩歌也可以敘述,只不過是以意象為基礎的敘述。由于敘述具有秩序性與邏輯性的特點,這就為詩作提供了形而下與形而上結合的條件,既避免了濫情乃至矯飾的毛病,又可以加強內蘊,提升境界,“抵達人們的內心,人類的核心”。像《軍車馳過麥地》、《閑暇時數數子彈》等,廣闊而深邃,迥異于他人寫的軍旅詩。
這也與他的語言特色有關。劉立云不刻意求奇,不故作“扭斷語法的脖子”的驚人之舉,而是講究詞語的質地和力度,講究詩的整體性和廣延性,從而調動讀者共同參與他的創造。請看這樣的詩句:“而高地永遠不止一座,或幾座/高地只在高地之上/只在我們的血流和呼吸之上/因此我總是對自己說/我注定要死在那座高地”(《高地》)。既是實寫又是虛寫,直接進入人的靈魂。
最能體現“鋒利感”的是《零點歸來》一詩,它涵蓋了上述三個方面的選擇與追求,是情、理、美的成功結合。
此詩記錄了一次軍事行動。妙的是并未具體展開,而是寫其結束之后,將攻防轉換、山呼海嘯、熱血沸騰……均銷蝕于無形,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零點”“在最后一次軍列的最后一節車廂”中的場景。兩個“最后”,呼喚出軍列的雄壯與軍容的威武;“零點”之“零”,既是軍事行動的結束也是休息待命的開始,恰似戰爭與和平的關系,在偌大的世界上,在悠久的歷史中,二者總是交互出現,如同硬幣的兩面,非此即彼,讓人感受到了芒刺和冷氣。
與他的多數詩作一樣,劉立云的審美視角是“在場”和“親歷”,但在這首詩中,他選擇了第二人稱,一種“對話”的敘述方式。就像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一樣,隨著“你劃亮一根火柴”,便“顯影液般地”“顯現出許多人影”。詩人用“山谷的碎石”比喻“人影”,是在“排炮響過之后”的碎石,是經過戰爭洗禮的碎石,是重歸沉寂的碎石,不能不使人聯想到他在詩集《烤藍》自序中的思考:“戰爭與和平囊括了人類所有的生存狀態。”“在軍人的辭典里,和平只不過是戰爭的間隙。他們每天操演、演習、清心寡欲、引而不發,長期忍受與家人分離的痛苦,就是在等待戰爭,演練戰爭,準備在戰爭中一顯身手。”可見劉立云的敘述,也就是對意象的思考!沒有槍聲、炮聲,只有鼾聲、磨牙聲;大家都睡著了(除了放哨的“你”和未點明的“我”),“但所有的眼睛都圓睜著”,如埋藏著風暴的“槍口”,蓄勢待發,一有動靜,“所有的手/都在尋找槍”,立即敲打出“鋼鐵的聲音,馬踏殘虜的聲音”,這便是作者追求的鋒利感。蓄勢愈久,鋒頭愈厲;引而有力,發必中的!
至于這首詩的語言,我將其視為未開刃的劍,相當于金庸小說《神雕俠侶》中獨孤求敗遺下的三柄長劍中的第二把——無鋒重劍,外表樸拙,內質凌厲,貌不起眼,實則驚人。它需要你慢熳閱讀,反復體會,從動(奔馳的列車)到靜(寂靜的車廂),從暗(劃亮火柴)到明(顯現人影),從滅(馬燈的熄滅)到燃(眾眼燃燒),從近(地板上)到遠(漫漫歷程),從粗(點燃一根根火柴)到細(坐成一棵消息樹),從待(長久地等待)到臨(那一刻)……經過如此這般的作者與讀者的互動、打磨,一連三個“你無法不這樣”終于將劍開刃——“那一刻轟響突起驚悸突起/所有的手/都在尋找槍”。這種鋒利感的殺傷力或云震撼力,是十分驚人的。
最后一節——劉立云非常重視開頭與結尾一從內到外,宕開一筆:
“窗外,雪花開始飄落,冬季正在布置新的圍困”既是新的艱難險阻,又是大的戰機戰功,還隱喻戰爭即使結束也會困擾人的一生,一語多關,含蓄且美,余味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