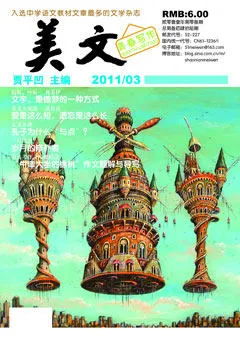孔子為什么“與點”?
張大文:1991年被評為全國模范教師并被授予國家級“人民教師”獎章。1992年被評為上海市特級教師。現為復旦大學附中特級教師,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兼職教授。已發表文學作品1000萬字左右。
在侍坐的過程中,子路、冉有、公西華、曾皙都按孔子的要求,談了自己的理想。而孔子最后表態,只贊同曾皙。
讓我們看看曾皙的理想罷:
暮春時節正同新翻的泥土氣息飄然而至,沂水河畔油菜花鬧得格外燦爛。我們五六個成年人走在后面,六七位青少年已經沖到河邊。脫下新縫的單夾衣,也放下了世俗的顧忌。讓甘甜的春水洗去身上的塵埃,讓青春的年華接受自然的撫愛,啊,舞雩臺上的春風喲,我們迎著你蹦跳上來;啊,回家路上的歌聲喲,我們帶著你相伴到明天。
上面這個講法,是我讀了曾皙的原話,一時興起,想象中改編而為一幅圖畫。我覺得,這樣一描述,便對曾皙的理解和盤托出了。
他的理想是用禮樂教化熏陶大眾,不斷完善自我。這個儀式看起來僅僅洗滌自己,親近自然,實則是給了內心一個充實的安排,與天地合一,去感知四時,感知山水風月,做到了孔子說過的“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之”的教導。孔子的意思是,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人際關系應該是里有仁厚之俗才是美的,擇里而不居美地,則無是非之心,安得為知?——而曾皙的理想便為“里仁”之內涵作了形象的注解。
相反,子路、冉有、公西華的理想,孔子在回答孟武伯的提問時,認為子路“可使治其賦(軍)”,冉有“可使為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至于他們是否達到“仁”的境界,孔子一律回答“不知其仁也”。
這是因為,他們都只做了一時、一地、一職之計較,停留在個體對社會的作用;而曾皙的理想卻體現出社會群體的價值認同,反映了整個社會的信仰目標。
當然,孔子的“與點”并不是無視于曾皙的問題,盡管只是出露端倪。這表現在杏壇問志結束后,曾皙獨自在后試探底細道:“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孔子立即敏感到他雖受表揚,已暗滋浮躁自滿之氣,便冷淡地答:“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這就是說,今天還只是“言”而已,遠遠沒有看到行動哩,任重道遠,好自為之!
這就是一個教育家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