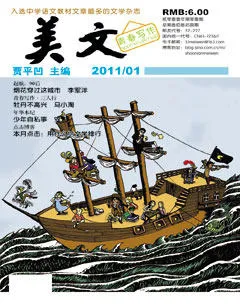時光村落里的往事
這是一個不大的村落,依山傍水。有著淳樸的民風,唱著淳樸的歌。
有人說:“村子富不富,看戲臺闊不闊。”我們村里有附近最寬闊的戲臺,這曾一度成了我們的驕傲。或許正因為如此,我才喜歡上了社戲,進而又喜歡上了鼓詞。
記得那些年年底的時候,父親總會牽著我肉乎乎的小手,穿過大半個村子,擠進那所不知道多大歲數的小學,對那座和村子一起長大的戲臺踮腳張望。擠在一起的都是村子里的熟人。牽著孩子,或是幾個結伙相認一笑,抑或閑侃幾句,遂又伸出腦袋,拼命向戲臺上張望。
小小的我被淹沒在涌動的人潮里。高高仰起的腦袋,竭力踮起的腳尖,目之所及也無非只有拔地而起的人影,再上面就是星空了。拉了拉父親的衣角,還有被人氣焐熱的紅撲撲的臉頰,一副隨時要哭出來的架勢。父親低頭一笑,摸了摸我的腦袋,隨后蹲下身來拍了拍肩:“來,上來!爸爸背你。”我興奮得直點頭,破涕為笑。兩步跨上了他厚實的肩,雙手緊緊勒住他的脖頸。
村民大都愛看老戲。興起時,也可以跟著咿咿呀呀地唱上幾句。評判哪個唱的好,哪個腔太嫩,哪里又唱錯了,卻也不排斥新戲、外戲,只不過這些都來得少了。
記得那年入冬,捎著秸稈燃盡的嗆味,馭風而來的秦腔使村子萬人空巷。人群里突然爆發出一陣掌聲,只見旦角背朝觀眾,從后臺款款而來。于是便有這樣的耳語傳開:“瞧那身段——從頭到腳搖頭晃腦,帽翅搖——一會兒雙搖,一會兒單搖。那可真叫絕了!”左邊的帽翅快活地轉動,右邊卻紋絲不動。或是右動,左不動。頓時,掌聲雷動,叫好聲不絕于耳。繼而猛地一抬頭,隨即一聲大吼。像是天邊炸開的一道驚雷,從頭上一個個地碾了過去,令人每根發梢都麻酥酥的。又是一陣喝彩。
這出戲我至今還記得,叫《救張生》,不過旦角的名字卻記不真切了。只曉得當她慢慢、慢慢蹲下去時,人頭也隨之慢慢、慢慢地矮了下去;當她緩緩立起身時,人頭也跟著緩緩抬高,如此反復,恰似起伏的潮水一般。我看著有趣,騎在父親的脖頸上,高興得直拍手,卻不知早已尿了他熱熱的一脖子。
祠堂里的唱詞(村里習慣稱鼓詞為唱詞)也分外有趣。
每天下午一放學,還來不及回家,我便往祠堂里跑。只見敲鼓、打板、唱詞的藝人面前已是密密地坐滿了人。我一路小跑到那個熟悉的位置,書包一甩,一屁股坐在爺爺的腿上。靠在他懷里,將他搭在膝上的手引至身前,圈著腰。然而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依舊硌得我生疼。爺爺渾然不覺,搖頭擺腦地哼著曲兒。枯瘦的臉上,微開的眼縫里透出渾濁的光,卻清亮地顯出滿足的樣子。我撇撇嘴,閉起眼睛,也開始搖頭晃腦。
后來,我搭上了遠行求學的公車。在那些我所失落的歲月里,曾經熟悉的曲調,從祠堂里絕跡,曾經令萬人空巷的戲臺,漸漸荒蕪。
去年年末的時候,我又路過新建的戲臺。那個粉白高大的、琉璃瓦蓋的新戲臺。它對著百余名青年歡暢地高歌,巨大的音響唱出重金屬音樂的跳動質感。而我卻默默地轉頭,穿過大半個村落,爬上掉漆的,灰瓦的古舊戲臺。
木質的地板嘎嗒作響,驚起一群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