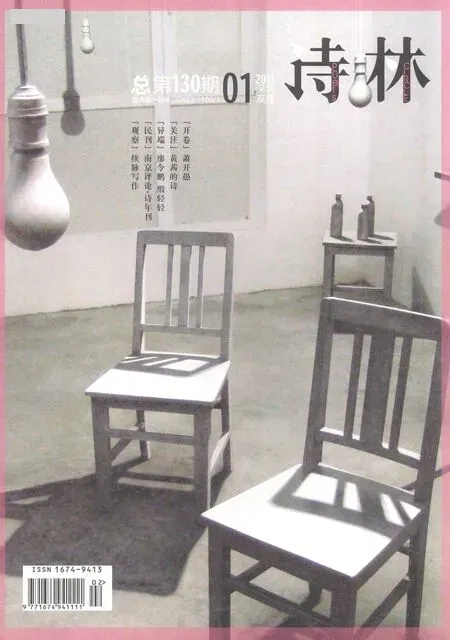蕭開愚詩選
蕭開愚詩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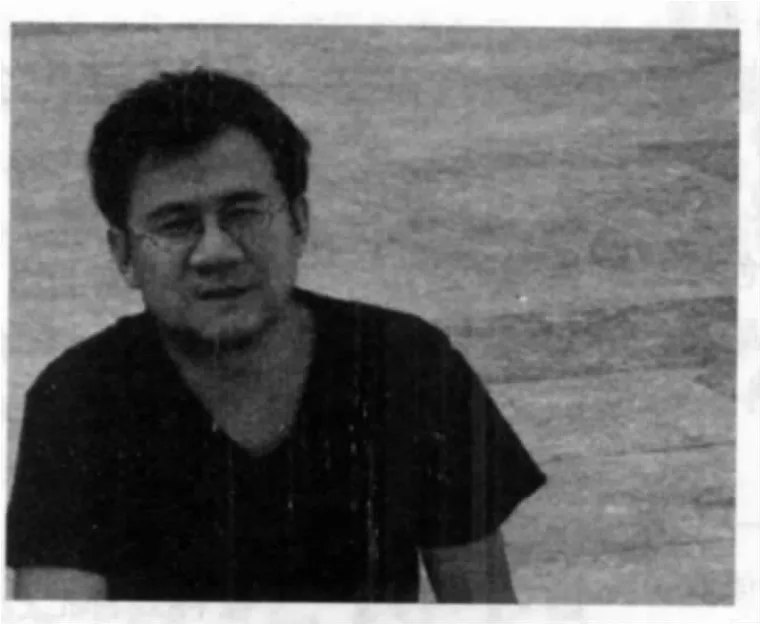
清明
當兩腿騎住木馬,
公園就旋轉,
都像木、像馬、像奔騰,
你夾緊,抽打。
午后,你腿已縮短,
木馬卻已激活,
狂奔、嘶叫而且咬人,
再也爬不上去。
怎么老練了下崗呢,
怎么才三十歲,
今年春來早,從胯下,
忽閃過暖夾寒。
1998.4.16 于上海
就近談致詩友
昨夜,知事的鳥兒來發動我,
旋即回到它應有的收斂。
從那邊消失而在這邊等著,
在兩邊的曙色中同時退場。
久違的催促,
這結滿露珠的起點。
這舊組織的愈合,
把未來約束為兩個星期。
我朝向間隔,
流動的硫酸留在基層,
擴建的缺陷吸收資金,
我在山區,發條在響。
友人,解體固需體諒,
惹禍的未必蒙昧,
趕在脫發前削發,
我們反它一次蒙昧。
發電不是原則,
共同不是原則,
單獨更加不是。
是從真實到事實。
我泡在浴缸里,鼓脹著,安詳著,
那反對的哲學比贊成更邋遢。
啊,友人,瑞士的鐘表偏慢,
我聽著鳥叫,我系好了鞋帶。
2008.10.19 海德克城堡
注:最近住在瑞士格爾芬根的海德克城堡(SchlossHeidegg),多思多睡,這兩天常想到近來交談頗多的席亞兵、姜濤、冷霜、余 、張偉棟、成嬰、張曙光、朱永良和耿占春等幾位詩友。叔孫穆子答叔向說,“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因有寄。
第一頌詩
1
我查找不出,建國初三十年中,邊界以內,
另有比監獄更配得上三個青年的設施。
各自鼓勁于常態,而那里,是檢查異端的
手術臺,持續散發帷幄的味道。
三個前后隔絕,男的比女的,或者相反,
女的比男的,多出一件遭遇不堪的記錄。
某個活躍部位被減去,反應與表現的狼狽
極其污染語言,竟被奉為英姿。
與鞭尸癖反調,我反對設身逆旅到那里,
去點頭和搖頭,周圍掛起停止的人,
當時,應該徹夜致動的人,未婚,低著頭,
無須強制,想到,說了,離開了。
各種實現都未必對,語言構成各種真相,
說話歷來犯禁,被阻止了就動聽了,
被否決的就是硬性愉快的,這個純潔優于
那個純潔,同樣果斷地抱著武器。
我尊敬說話的器官權利,三位難看地犧牲——
2008.10.21
2
她證實年紀的無益。
她日益增加暴雨的氣質。包含了臉蛋兒塌陷的分量的
眼眶強忍著。
她忽略客觀,淡漠對應,決不
斜視裹脅著的地平線的放晴。
她甄別性質和實質,
她在江南分了岔,
她鐘愛聞過的石梯。
她稚氣,天真,被污的肉,
獨當一個國家。
她斷交,萎縮,
沉靜,
脈管里貯滿墨水。
她缺席的同代的沉落很多,
她嗓音清潔[為此,靈魂(她有)
連續二十年割破],她隔著墻壁。
實為污點,使現代蒙羞,
犧牲以證明劣跡——不,不止于此。
追認吧,她登錯臺了嗎?
她的編織再普通不過。
處理她的方案沒有比死刑更配得上她的。
2008.10.23
3
為我國罕見的政治的春天,
作上街的一員,作在人叢中
使勁叫的、不分彼此的小將,
這不顧,針對著一個劃分。
他分析的血統的血液鼎沸,
燙手;核對過血腥的刻度,
但他不是判官;血液冰涼
而有血性,他是他的父親。
時代也是一場單獨的考試,
他沒有通過。答對,等于
答錯,對沖不相干的債務,
交納族譜稅,造誰的反呢?
權力是爭取到的,尖端的
連片之瓜分了概括的格局,
需要尖銳的尖端在它的底
部,刺破它,最終扭轉它。
他的英氣,他用腦的程度,
和他簡陋的理論與我們的
檢討成正比,他不屑于攻擊
他的對立面,他倒是寧愿
被忘記的。他知道他在主
張云彩嗎,他胡同里的與
眾不同的由衷,他知道嗎,
描繪了一個褒獎他的儀式。
他包攬的那個階段和這個
階段,說這說那和沉默的,
甘為時光沖刷不掉的遺孽,
真實比事實更缺乏真實性。
沒他,我的階級更加疏闊,
但他不是搶救地位的英雄,
他是正當的,勇敢的,不
愜意的,中斷了所謂生活。
2008.10.29 于海德克城堡
4
聽的人到處不多,說的本事難學;
就挺尸又怎樣,不必給活活憋死吧。
她說話好聽?她的觀點重要?
她的主張已沒人記得;
她沒有說出的是個禁忌:不是沒有
和被禁止的沒有,
是最節省的,被省略的沒有。
當我奉獻很臭的艱辛,
開放竅門,保證口腔衛生(嘴內外除嚼和咽
所必須外的多余部位為為公節約切除費用
而保留),她不得不是全人類。
說的內容模糊,音質刺耳。
我看過雞和鵝的喉管,不漂亮,
他們為了她的喉嚨好看嗎?
感謝她成全了他們的審美。
我企圖給她的喉嚨里補一截,象征性的,
一次性的,耐用又不花錢,
像負疚的人向她賠禮。
她無法用她佩戴的裝飾反駁我。
過去,動物般的我們怎樣動作,
現在,仍然怎樣動作。
不過,很多年前,她的頭肩間出現的中斷
并不新鮮和切題。
為她按破壞的面貌塑一尊雕像,
在北京,在人嘮叨而不限于嘮叨的地方。
2008.11.2
5
她,她,和他,把死讓渡給了梅花。
我培土,土又不平。
2008.11.3 于溫特土爾,拉斐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