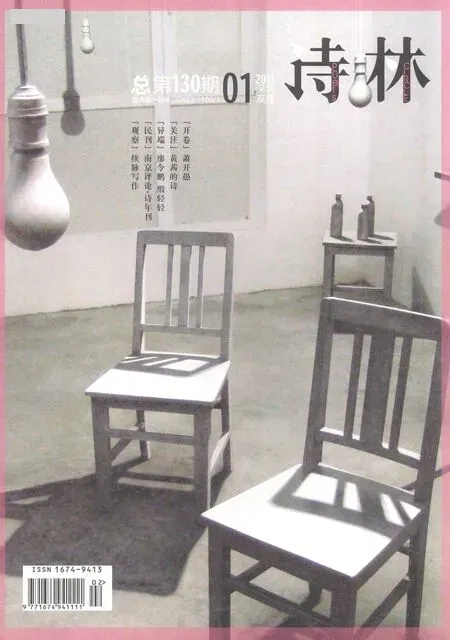茱萸詩選
茱萸詩選
茱萸檔案
簡介:茱萸,生于1987年秋。2003年開始詩歌創作,2007年起兼事隨筆與批評寫作。詩歌、隨筆與評論散見《人民文學》、《山花》等期刊。現居上海。
詩觀:在我看來,所謂詩歌,該如法國大詩人伊夫·博納富瓦那般所言:“詩和愛情一樣必須對那些存在的存在加以抉擇。詩應該忠實于黑格爾曾經自豪地以語言的名譽憶及的此時此地,應該將來自于事物的詞語創造成一種向自身回歸的深蘊和反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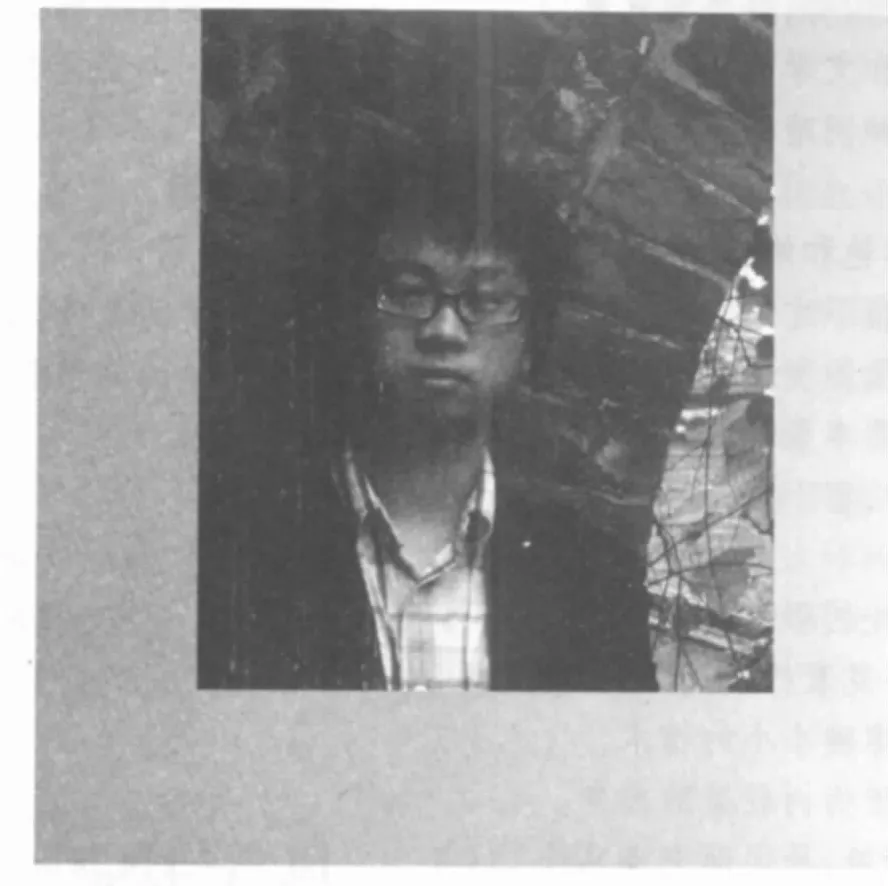
分湖午夢:葉小鸞
記同里、分湖之游,兼呈蘇野
枝葉繁茂,季節豐腴。避暑的心思
抵不過對一場沉酣之夢的迷戀。
粗暴地打斷美,又開啟奔赴美的暗門,
汽車的舌頭分娩得漫不經心,它制造
話語的棄嬰,黏著傲慢的現代腔調。
盛夏盤踞在途中,終結了花粉的暮年,
余下的葳蕤,卻教人襲用草木柔弱的名字
以驅趕初踏陌生之地的隱秘驚惶。
我的雙眼,被如今的屋舍灼傷,
而女性永恒,不理會時序變遷的煙幕。
仆倒的字碑如何測試肉身腐朽的限度,
至于墓志銘,是未曾謀面的憂郁情人。
用午夢和疏香換取傳奇,那個早慧者
逃過了婚姻、衰老和文學的暴政,
躲在暗處,貼上死神陰晴不定的嘴唇。
它被裝扮得如此鮮艷和嬌嫩,及時地
吐出誘惑的果核,留下才華的殘骸,
它種植各種猜測、無知和偏見混雜的幼苗:
死亡的自留地上,要豐盈地收獲
首先必須削減枝葉,留下漫長的虛無。
作為供奉,請用另外的形式享用青春。
靈魂蟬蛻使容顏不復衰朽,逃離塵世的人
依舊在長的軀體,撐破小小的棺木,
一年數寸,如那株臘梅樹輕盈的肉身。
結局不再如當年那般,局促而充滿悲愴,
這里的蚊蟲,卻執著于遠來者血管中的
甜腥,它們或許更適合那一場午夢:
口針上是否長著撕開黑暗的燈盞,
在流動的液體里,用以辨識回返之途,
如這位必然長著明亮眼眸的早慧者那樣?
在猜透了人世存在的倉皇和潦草之后,
要如何,才能留開這么一片小小的廢園
供遠足人見證本不存在的哀悼。
這些舉動如此黯淡:撿拾舊物,帶走泥土,
瓦片上的新鮮苔蘚,我們的閃爍言辭。
2010.7.28一稿
2010.8.9改定
深夜食堂
風聲里,筍尖辛辣的密謀胎死腹中,
咸菜正試圖掙脫湯碗,回到布滿青苔的齒縫。
請挑選一種逃離的方式:油炸、清蒸或爆炒,
鍋底遍布淋漓香汗,照出另一個春曦深藏的
竹葉青和魚肚白。
2010年04月28日
鳳梨劫
內心甜蜜的較量,含混而親密,
你明晃晃的卸甲歸田的心思,裸露在早春的空氣里。
剃去鱗片,喉的天險如何飛度?
紅得深入骨髓的證明,在唇齒間,作銷魂的一吻。
2010年04月29日
風雪與遠游
若覺得這會是一次更深的失敗,那么你便錯了。
它們只是一樣的模具,在沒有差別的四季,
給我一個無能為力的開始,
于午夜聚嘯,出產類似的影子。
如今,我們在漢語內部遭遇芳草、流水和暖紅,
無處不在的現代性,那非同一般的號叫。
你不知道,有些生動的植物以及
值得道說的枯燥細節仍在左右著我們的步子。
部分人在場,另一部分人抽身,
你從來都不是風雪背后假想的敵人,
能夠見證時間的下墜。
一枚橙的汁液中我們懷念漢語,身體的
隱秘部分浸沒其中。小腿的光滑弧線癡了,
還有骨骼、關節、血肉和毛發,它們
左右著詞與詞的相逢和零落,它們斷言:
“不生長植物的季節,是干枯的”,
但是這殘缺之上的完整可以被觸摸,
是所有的光輝,讓我們激動。
可設計一場情節顯豁的遠游又能如何?
你能在二月的陽光之淺里提煉出湛藍?你能在赭石色的花朵里取消比喻?
你道不明這樣的午夜之輕、風雪之面具,
它們具有虛構的全部特征。掌握它就意味著,
為造物而生的機竅,在你我的掌心靜泊。
2008年2月1日
池上飲
憶昔西池池上飲,年年多少歡娛。——[北宋]晁沖之
我們濕漉漉的對話,要保持恒溫且鮮綠,
如剛剛過去的春晝般冗長,卻并不乏味。
說的話題細碎而干枯,哦,這真不是什么壞事情,
南方的三月細膩到了極點,她隨時可以
制造新的腐爛,天氣的變化更令人無從談起。
夜色只是淺,無法溶解你我嘴角的間歇性緘默。
是的,它們近乎微笑,近乎苛刻。
對酌,不明液體的爬行導致話題偏移,
多么有趣!它們已被抽象成一套虛構的動作,
承擔著符號賦予的強大指涉權。
在暗處,我們的聲音扭曲成形而上的尖叫,
你能否立即意識到這個世界的混亂,它
像極了田園里的稗草,硬的端頂迅速
刺破時間的這塊美學傷疤,耀眼而疼痛。
該承認的是,我向來缺乏言說的耐心。
我不清楚每一株植物、每個細節的名字,
卻偏要用形容詞堆積出大量的煙幕。
它們晦暗、偏執、寒冷,沾染著密室政治的
惡習,它們不干凈。
池上飲,決不能效仿干枯的古人們
沾染著吳越一帶的甜腥來談論
治服、習技或房中術。
我僅僅試圖拗斷鏈條中的任何一環,
你看,飯桌上便立馬多出了
幾道古怪的菜肴。
哲學家的菜園里,櫻桃紅還沒成為流行色,
春天卻貶值了不少。
幾只呆瓜足以修飾人群的寥落,
早在落座之初,我們便擱置爭議,
跨過點菜環節:新疆烤羊肉、冰鎮思想史,
外加全民造句運動的余緒——
打折年代里,不知道這樣的優惠套餐,
能否適應我們國家那副巨大的陰性脾胃。
2008年3月3日
白蔓郎
荼蘼之歌,或植物的別名演繹
這是場盛大的悲劇,我注定要退居幕后。
相對于韶光里湮沒不聞的秘密而言,
“白蔓郎”,作為某種植物的別稱,
只是多此一舉的命名和安慰。
灰褐色莖干的重疊部分,并不能被轉喻,
一如當年種入土壤的先人骨殖。
它們是否完好已然不重要了,
劫后余生的枝蔓,終于長成。
有細小的呢喃開始將暮春里
攢集的所有酸楚催發成半句囈語,
而我,作為所有事件的見證者和回憶者,
終將與你們,相互失蹤于陌路。
縱使這枝頭花開,陷入失語的
杜撰者的臉部輪廓同樣難以描畫。
你過于執著了,這是一個香艷的騙局,
是歧途,是孤芳自賞者的悖謬。
讓我們一起開始這種柔弱的編纂吧,
體例天成,獨獨少了清減的儀容。
刪削多余的形容詞,把荊棘除去——
“它們遍地都是,只會讓我膽寒。”
圈定特效的動詞和關鍵字,鎖住暗香,
你要傾囊相授的又豈止是這銷魂術?
而我試圖拐騙的也不僅是此一干絕技,
如此險惡的用心啊,囤積了多少年?
試圖辯解的,怎會單單是你我呢。
黃白色的綢布衣裳只穿一季也就罷了,
卸下,交給茫茫煙水,
那場悲劇里的唯一主角,終將缺席于觀眾席。
2008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