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深處的憂郁
——讀燕趙齊霽詩集《凡響·啟蒙詩篇》
□徐敬亞
一座城市深處的憂郁
——讀燕趙齊霽詩集《凡響·啟蒙詩篇》
□徐敬亞
那一瞬我一定是某部分魂兒出了竅。我推開高樓大廈,分開眾人,在字縫人叢中一眼就認出了那張憂郁的臉——是那張哀傷的嘴臉使我對一座城市忽然產生了畏意。突然來臨的、仿佛能噎住喉嚨的凝重,竟降臨在輕松的酒席。幾分鐘內,我會見了無數游走幽靈。我突然發現:在我多年熟悉的城市中,竟深藏著一本沉重的詩集,藏著一位哀傷的詩人,藏著一股凌駕于世俗時空之上的宿命咒語。
我說的——城,是深圳。詩,是《凡響·啟蒙詩篇》。人,是燕趙齊霽。
2010年夏天,在深圳特區報乘長風餐廳。正當酒席乘風馭浪之際,我卻莫名地翻開了這本詩集——它頁碼很薄,像個窮人。它裝禎黑白分明,像個法官。它無序無跋,除了詩不多余一個漢字,像街上走過一個自言自語的乞丐。
那是一次神奇的閱讀。只略略幾眼,讀得我心驚肉跳。在這個輕浮的城市里,還有如此橫槍立馬之人嗎?我合上詩集,像關閉了字字霹靂。重新回到酒宴,心還停在那些匆匆的字上,聽著人世紅塵談話,像一個心懷鬼胎的潛伏者。
越是匆匆一瞥,越能一眼識出遠近疏離。越是不經意偷窺,越讓人莫測背后暗藏的殺機。對于某些詩人、某些詩,說出一瞬間感覺其實已經說出了作為詞語同謀者的全部。
憂郁,人類內心永遠無法撫平的精神絲綢
文明史上,幾乎沒有一處山川被人類這么飛快地堆滿了連天的沙石磚瓦。30年,這座城市制造樓房的速度比神的降臨還要快。繁華與財富早已成為它暗中的代名。它的寫字間辦公室里坐滿了意氣洋洋自若的人。30年,它從漁村躍升為中國財富金字塔最尖利的部分。它的上空飄蕩著堂而皇之的旋律。它的印刷機上寫滿了好詞好句。然而,詩人往往選擇與財富相反的方向,與感覺良好相反的方向——他并沒有仇恨,他只是滿懷憂郁,只是向一種“快馬跑成骷骨”的速度與“唯我獨尊”的模式提出置疑:
當水泥變得堅硬當堅硬變得愚蠢當愚蠢唯我獨尊
當大海成為墻壁當道路成為阻礙當神明不再
當靈魂冒煙當靈魂被點燃當靈魂學會尖叫
當你我成為看客當看客背對窗子當窗子已經堵死
當水泥四分五裂當云層紛紛剝落當快馬跑成骷骨
當我沒有來過當我沒有看過當我沒有說過吧
——《懺悔十:封建的水泥》
以“神明不再”為由,對現實發出哀怨,對理想國予以呼喚,這是古今詩人們一貫的套路與手法。這種悲憫的情懷顯然不符合高歌猛進者們的視角。有錢勢的人總是祈禱神靈護佑人間繁華,但是誰能永葆富足呢。就連神也不能確定每一瞬間都是快樂的。堆積財富的動作不管多么優雅,良苦用心的背后,怎么能不隱藏人類貪婪的嘴臉和耿耿內心。那正是人類憂郁的根源。
真正的詩人都是憂郁的,甚至是全面悲觀。他們太了解文明強大的慣性和力量,也太了解自我的渺小。因此他們太知道理想與信念在現實的失敗必將多么必然。于是詩人便自我品嘗更大的精神痛苦,于是燕趙齊霽仿佛預占山頭一樣主動交待般地搶先說:當我沒有來過當我沒有看過當我沒有說過吧……
憂郁并不是詩人的專屬品。塵世間也會有世俗的憂愁與哀傷,但這些糾結的精神迷津,不但具體,而且臨時。正如病,病因清晰,對癥下藥,常人的精神傷痛總會結痂總會痊愈。而到了詩人這兒,情況嚴重得多:
啊,我的哀歌,在人間尋找錯誤
有些錯誤是原創,有些錯誤是摹仿
——《哀歌二十二》
我的同胞沉迷于人前的虛假
或者直奔金錢和榮譽的
昏頭脹腦的忙碌之中
——《哀歌十》
當詩人將自己憂憤的標的物指認為“人間”與“同胞”時,他的憂傷顯然超越了個人生存的私怨而進入了倫理與社會學范疇。而當思想與理性又時時提醒出絕望結局時,他的憂傷便進入了古老思想史的悲劇行列。幾千年來,與文明對抗的思想似乎都閃著光,但人們卻忽略了這光芒最初刺傷的卻必定是發出光芒者本身。啟蒙者的精神與肉體關系往往尷尬:他的思想代替著整個人類良知承受光榮,而他的肉身卻時刻代替靈魂蒙難。再光榮的苦難也不會令人愉悅。再深沉的憂郁也絕不快樂。人類心中那塊永難撫平的精神絲綢不停地疼痛起伏,摧毀過多少優秀詩人、智者的美好生活與平凡肉身。
我們是當代的老蜜蜂釀造狗日的苦水
我聽到了大慈大悲的菩薩說
他們雖然不幸卻習慣了不幸
——《哀歌十二》
從自己身上找不到罪過
這就是一種罪過
——《哀歌十五》
詩,一定是一個陰暗的咒語。詩人不但總能在生存中找到悲傷的理由,更善于給任何幸福生活披上一層憂郁外衣。“雖然不幸卻習慣了不幸……找不到罪過就是一種罪過”——天啊,以此之眼看來,世上還有幸福,紅塵還存歡樂嗎?這,已經不是思想,而是一種詛咒、一類宿命、一項悖論。與其說詩人借菩薩之口道出箴言,勿寧說是內心永無安寧的詩人向世界發出的自白、困惑與哀嘆。
寫詩,是一種可怕的習慣。詩人是一個積郁難返的角色。
世俗的歡樂,常常變得遙遠而淺薄——更準確地說,致命的不是遙遠,而是淺薄,是自己也無法逃離的、自我鑒定式的淺薄。那些世人們完全可以忽略與忍受的人類過錯,以一種不可饒恕的方式折磨著詩人。是誰給了詩人以先知與受難者的雙重權力,誰就同時賦予了他永無安寧的內心苦難。一整套貫穿生命的不愉快通道,就是這樣被安裝在詩人的生命直覺系統。他先是用憂郁折磨自己,然后用憂郁的詩折磨全世界。他的憂郁由于沒有理由,因此沒有起點。由于沒有方向,所以也消失了終點。像每天含著一枚純白苦澀的茶堿片,他煞有介事地代表著全人類在純白色的精神疼痛中日夜翻滾,并煞有介事地寫書以宣示后人。
憂郁,深圳白領剛剛學會的煩惱
對于詩人與國家的關系,于堅有一個漂亮表述:“在我們的時代,詩人由于被市場社會放逐而成為一種國家污點。”在我看,這一惡毒命名,顯然屬于詩歌圈子內部的一種自我嘲諷。但它卻無奈地正視了詩人社會地位的窘迫。詩人之所以成為工商秩序中不受歡迎者,不是由于他們不聰明,而恰恰過于聰明。對詩的過度沉溺而帶來的工作消怠,使他們至少成為國家勞動效率領域的間諜。沒有人懷疑詩人的智慧,人們懷疑的是他們智慧的箭頭方向。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雖然一批又一批詩人慘遭上司白眼并由此顛沛流離的故事此起彼伏,但詩人離經叛道的傳說卻從未停止。其實,準確地說,早在他們被工商社會放逐之前,詩人早已在內心里自我放逐。
顯然,燕趙齊霽不屬于那些裝瘋賣傻的流浪詩人。他在一座忙碌城市光怪陸離的生活角色中,把自己隱藏得很好,很安穩。但他的詩,還是泄露了這個深圳白領內心的隱秘:
呵白領,從他們走路的姿勢我就知道
他們在鳥瞰這個世界的時候駝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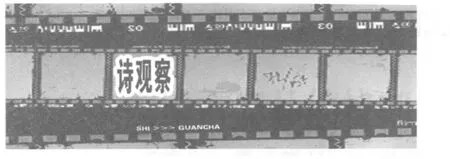
請把白領寫進小說吧
他們除了上班這點事還有什么事
——《哀歌十一》
在為白領書寫日常生活自白時,燕趙齊霽使用了一個漂亮而虛幻的肢體姿勢——因過于頻繁鳥瞰世界而幾乎致殘——“鳥瞰”與“駝背”的對比,勾畫了白領心懷天下卻又佝僂負重的勞累窘像。后兩行,看似純口語白話,卻詩意盎然。辛酸戲謔中充滿了一個文學先知對白領生活的自我蔑視。
“白領”,作為具有知識背景的腦力勞動階層,在中國尚屬新潮生活形態概念。在我看,白領是現代社會中最承重的群體,也是一個最躁動、分裂的群體。幾乎每一天,都有向上與向下這兩股方向完全相反的力,在暗中撕扯著這一表面穩定的人群。白領階層無疑最具野心。年齡與學識的雙重優勢,使他們中未來工商領袖的因子力在不斷涌動、攀爬。而作為現代消費意識最強、職場消耗卻最大的青春部落,白領階層也是消積怠工、應付了事、內心波動失衡的代名詞。在經過了人口遷移后的短暫得意之后,深圳白領終于學會了西方現代與后現代的不盡煩惱。
細心品讀燕趙齊霽的詩,我同時在定位深圳白領的生活經緯。在這位比一般白領嚴重憂傷的詩人作品中,我讀出了兩個刺眼的名詞:“房奴”與“紙匠”。
四季的回廊里,為了金錢
讓我放慢脂肪的燃燒,我是一個紙作的房奴
有木柴有火焰。我欲望的骨骼已經傾斜在金錢余暉中
……
我們成了金錢的苦役犯……我的靈魂
在一場商業炒作中被自己低價賣掉
——《懺悔三:房奴》
房奴,這是白領在國家金融體系內的另一個銀行代號。由于無法克制的生活需求與尊嚴欲望,他們提前預支了晚年的空間幸福,以出賣人生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報酬為時間代價,成為了自己生命債權的人質。在房奴遍地的今天,燕趙齊霽這段飽含辛酸意象的詩句,說出了多少青春公眾的半世辛酸:四季回廊……金錢……燃燒的脂肪……紙作的房奴……木柴……火焰……欲望骨骼……金錢余暉……苦役犯,那不是詩化的意象,那是千千萬萬人的呻吟。而最精彩的、我更看重的,是他對職場的身份剖析,那是中國當代少見的、有廉恥感的自我認定——燕趙齊霽對紙人的自殺式剖析,是這部詩集中最高貴、稀有、獨價的部分:
我內心穿著苦役犯的囚衣,坐兩平米的格子
讓我的思維站好角度,我與紙約定了今生
……我穿過夏天,我出汗,我被空調降溫
我喝著茶,我把報紙編排,紙媒呻吟的年代
我有紙的脆弱和柔韌的性格
……我是疼痛的紙
我被……投入造紙廠火堿池,帶著所有人的口水
和這個時代丑惡的眼神
——《懺悔一:紙》
紙匠,這是我的偶然命名。中國自古有木匠、鐵匠、皮匠。他們并非造木造鐵造皮者,只是削柴鍛金革毛,即以其為原料或道具顯示技藝的匠人:“我活在水泥里卻像一根兒脆弱的蘆葦/我活在語言里卻像一堆沒用的紙屑”。于是我把寫字為生的人稱為紙匠。
進行簡化推導吧——以紙為生,即以字為生。以字為生,即以話為生。以話為生,即以心為生。以心為生,即以真為生——以真為生,嗚呼,豈不即以痛苦為生以口水為生以白眼為生!
至此,燕趙齊霽的第一類憂郁已真相大白。職場的四季,到處都是文學的疼痛——表面明亮、溫暖、豪華而秩序井然的現代社會,每天都暗中揮舞著陽光般的屠刀,無情切割著一個白領的血肉與心靈。他的憂郁,怎么可能僅僅是代替人類蒙難,怎么可能是藝人們裝出來的矯情。
憂郁,比哭泣更平靜更持久更陰暗
像一滴混濁的眼淚,燕趙齊霽把他和他的詩深含在深圳高樓大廈陰沉的眼框中。
我曾在中國北方民間
逃離,又從南方民間浮現
——《哀歌十五》
我的過去是石頭,我的未來是廢墟
——《懺悔四:順從的水泥》
是什么給了詩人如此幽暗的口氣與險惡詞語。仿佛一束寒冷追光,把他捕獲的全部詞語粉刷了一層不安氣息。在燕趙齊霽另一些詩中,我讀到了比哭泣更悲傷更持久的沉郁。它,不是白領無奈的現代迷津,而是那沉重得無法逃脫的個人記憶。是的,是那些由持久的日常經驗所積累出來的記憶,一切根源正是那永無法抹去的歷史。
說到歷史、記憶,我要議論幾十字的黃昏。
直到這些年,也就是說直到晚年,我才懂得黃昏是一件無比漫長的事。2005年夏天在呼倫貝爾,我一分一秒地眼看著天空緩慢地變黑,看著白晝一點點地被黑夜絞殺,足足歷時六、七個小時。相似的是,歷史事件之退出舞臺,正如這幕自然界背景更換一樣柔韌漫遠。任何一個殘酷事件的結束,僅僅表明它再不能發展。而對于苦難,其實它才剛剛誕生。最容易被史學家們忽略的是,苦難一旦停止,僅僅意味著它立即成為當事者痛苦記憶的開端,剛剛成為后世永恒追討的命題。
我注意到,飽嘗記憶之痛的燕趙齊霽,在詩中多次提及他死灰色的童年:
我暗淡的童年的圍欄是連綿的山,石頭嶙峋
如雞骨的柴扉,那些餓殍在原野間穿行
……口吃的蟋蟀或者朗誦的紡織娘
潛藏在以水泥花朵崛起的城市
——《哀歌四》
一種廉價在喧嘩里放歌。幾十年前
童年的背上烙下的貧瘠,是乾坤
在扭轉時間。蘿卜、白菜還有豆莢的成長
——《哀歌五》
我苦澀的童年穿不破雨幕,瓜棚外的蛙鳴
兩只被撕掉翅膀的蜻蜓,心愿的爬行
讓我想起十里鋪夏天的無助
——《哀歌七》
對于童年,燕趙齊霽的詩中的名言是:“人生最好的典藏應從童年開始”。可惜,這個“出生的一刻就有一個問題要問”的敏感詩人記憶中有太多悲傷、憤慨。過去,我一直以為只有我們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才對往事耿耿于懷,我驚奇燕趙齊霽竟也對那些陳年往事憂心忡忡。他寫顧準,寫林昭,寫錢老爺子……我忽然覺得他得了病,我們民族得過病。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種族,惡毒的記憶永不會消失,它早已化為內心淤傷。在潛意識范疇,它無時無刻不影響著每一個日常經驗。而從心理學角度,凡屬不能化解的刻痕,都屬心理毒瘤,它阻擋營養,任何新鮮感覺無不接受著它的浸襲而使人反常不寧。
然而,下一代人的憤怒畢竟已經轉化。誕生幾十年的燕趙齊霽可能已經憤怒了幾十年,他反倒以一種極平靜口吻,敘述離他那么遙遠的無可奈何故事。越平靜,越無可奈何:
中原上沒有人在做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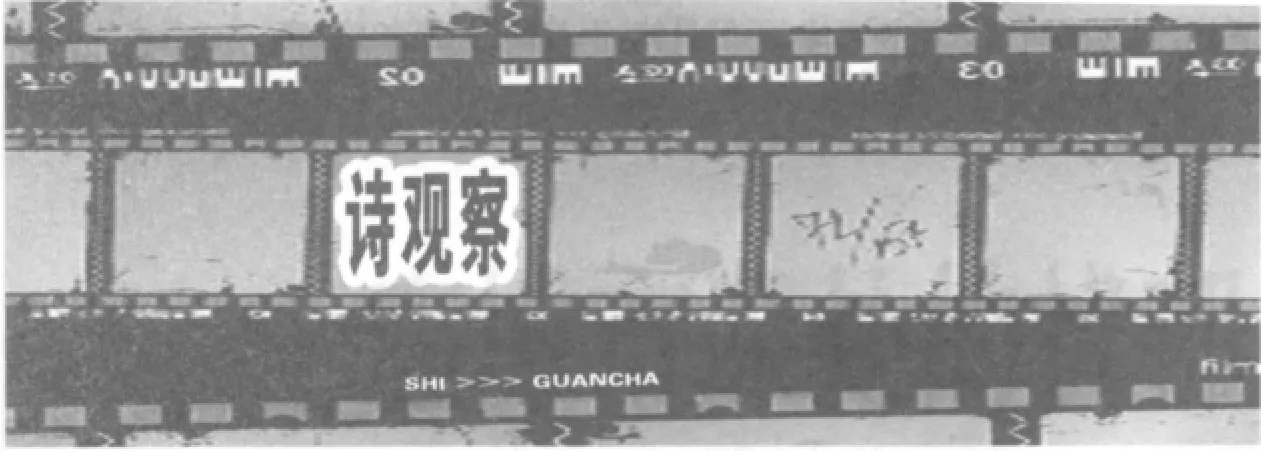
中原上找不到顧準的家
十月菜地落下白霜
星星長出了青色火苗
顧準在澆水站崗和發燒
——《懷顧準之一》
平靜。死一樣荒涼。沒有。沒有。有的只是白霜、青火。
發燒,僅僅兩個字,立刻把站崗與澆水變成煉獄,把中原燒成一片大火。
他寫林昭的死,寫得輕盈、靈巧。用快馬、黎明、鐵窗、子彈等精確流轉的意象,完成了一次無可挽回的跨時空追悼。
乘著快馬我想逆時間而上
要在黎明前敲響她的鐵窗
但我沒有子彈那么快
子彈已經穿過了她的胸膛
——《念林昭之五》
半個多世紀的風云,早已從容地清洗了無法遮掩的血痕。而往事殘淡的余光卻在一個幾乎與它無關的后生身上回光返照。只是這種回光以一種自我戕害的精神方式映射。這回憶,注定無法平衡,其結局只能是一個人飽受靈魂的每天煎熬。詩人的憂郁顯然已超越了個人恩怨,成為種族內悲的抽搐。雖然,這種藝術悲情充滿了灰暗,甚至不乏惡毒,但詩歌之箭卻總是沒有固定的靶向,哪怕它與某些政治家道德家們恰巧站在了一邊。
我無法更深入地評價往是與今非,我只是為詩中那些遲受追悼的受難者感嘆與慶幸。當歷史的債務不能支付現金時,它會以一種折磨后世的方式,為當年不屈的血液支付無盡的利息。
當憂郁大于技巧
對一部憂郁詩集進行技巧性評頭品足,是不人道的。這正如對一位無聲哭泣者的姿勢進行舞美評估或對其眼淚進行無聊的化學分析。
在這部詩集的封面,作者不是已經書寫了“凡響”與“啟蒙”兩個巨大的詞語嗎。對此我還能有什么細話可說。且詩人在署名處印上了“燕趙齊霽”四個大字,這更使我陡增了莫名悲憤。燕趙,那不是古老的中原大部疆土嗎。那不是壯士一去不返之岸嗎,那不是產生由于憤怒而把眼框瞪裂者的山河嗎。
我個人一貫傾心于宏大的人文情懷,一貫贊賞詩人的情緒力度與理性寬度。燕趙齊霽的詩顯然歸屬于此種雄性意識。史詩般的從容、開闊、簡煉:
北天有云,南天有雨,人民在煉鋼
北天有云,南天有雨,人民在逃荒
……
人民在哪里?人民沒回答
人民在哪里?人民各自忙
——《人民在哪里》
任何詩人作品,都是包含多種手法的復方制劑。燕趙齊霽之武庫亦是十八多般。如:“四季的回廊里,讓我放慢脂肪的燃燒”。脂肪怎樣燃燒?那燃燒又怎樣自我調控怎樣放慢?如:“欲望的骨骼傾斜在金錢余暉”……這些具備了西方批評模式觀照的復雜手法,在本部詩集中并不多見,它們不是燕趙齊霽的主要美學手段。他更善于用沉重的句子擊打讀者,或者說擊打自己。
于是,我只負責認定它的憂郁。
他,是本時代越來越稀少的知恥者。也許是童年的貧困經歷與記憶拯救了他。也許是遙遠時代的蒙昧與恥辱激怒了他。也許是現代社會道貌岸然的異化與無奈暗中戲弄了他。這一切,使《凡響·啟蒙詩篇》的內在美學原則具有濃重悲劇成份。這悲劇超越了個人命運,它更多屬于公眾全民,甚至全種族。雄渾而略顯粗糙的詩歌操作,恰暗中吻合了“凡響·啟蒙”這一闊大人文命題。正如鷹的美只能高顯于空曠藍天,如匍匐刨食于雜草中比雞還丑笨一樣,詩人的憂郁在這種重錘手法下反而表現得清晰、明了、震撼。
這個人的這些詩,我反復看。也許,它們本不是為了發表。他把它們寫出來,只是為了排遣那些無法排遣的內心苦悶。他更不是為了證明一座什么城市。是我硬把它與城市相連,是我忽然為這座城市在想像中增加了無數的同謀者。
2004年底,像認識燕趙齊霽一樣,我認識了深圳的路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詩人。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與稱謂:“朋友是一些愛熱鬧的人,以致我常常走進某一個生活圈子。當他們面對政客、有錢的人、或者同樣的一個小職員、司機、牙科醫生,或者某個來歷不明卻有幾分姿色的女人時,他們找不到體面的詞語,往往會大聲說:他是一個詩人……詩人,在這里是一個讓雙方都不致于尷尬的稱謂。”路云16歲開始寫詩,但很久以來,誰也不知道他是詩人。但他有一個“沉默的抽屜”,里面裝著幾部詩集的稿子。用時尚的話說,在公開的詩人名單中,他們并不“在場”。但他們卻實實在在活在自己真實的詩歌經歷中,活于默默抽屜。顯然,燕趙齊霽比路云離世俗更遠,他把自己埋藏得更深更靜。他的詩即使放在抽屜,也在抽屜最深處。
沒人能回答,深圳還有多少像燕趙齊霽和路云這樣的“沉默抽屜”。但生存的膩風柔雨中,失途羔羊的無助中,一定有暗中高人在精神迷津中徜徉并為我們暗中指點迷津。正如燕趙齊霽那些紙上的憂郁——他被思想捕獲,又被憂郁浸泡,他在逃離掙扎中獲得了靈魂的安寧,也由此獲得了自我拯救。
我想說,紙也是好的。通過文字在紙上的書寫與傳播,他的詩也同時救贖了我們每個人生命中的一小部分。
2011-1-18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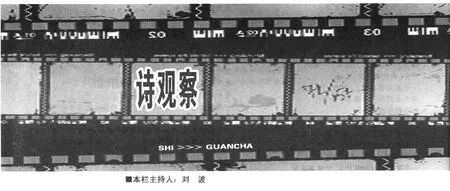
(本期封面用圖選自《藝術與設計》2010年總第23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