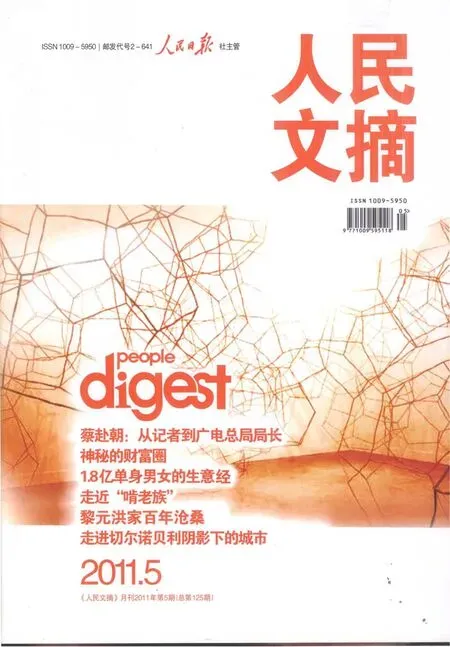張學思將軍的最后歲月
◎劉永路

風浪初現
1966年5月,海軍參謀長張學思結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海軍司令部,正好趕上了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在此之前,林彪集團把羅瑞卿打成了“反黨分子”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他們以“肅清羅瑞卿在海軍的影響”為名,掀起了奪權的險風惡浪。
張學思一向以作風嚴謹而聞名于海軍內外,而會議的操縱者們除了批他執行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外,還要他交代莫須有的“房產不清”問題,企圖“從經濟上到政治上徹底挖出資產階級在海軍的代理人”。張學思氣憤地寫了一份關于自己房產問題的說明材料,拿到會議上散發……
海軍會議情況通過簡報反映到黨中央。擔任書記處書記、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親自來到會場,傳達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的指示,指出這個會議不正常,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非組織活動是第一位的!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立即發生180度的大轉向。
陰謀逮捕
“文革”開始后,海軍的領導大權完全落到林彪集團的手里,李作鵬當上了海軍黨委第一書記、海軍政治委員,罷免了張學思海軍司令部黨委書記的職務。
“運動不讓我管,我可以專管作戰。”張學思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戰備值班、處理海軍部隊一些日常工作中去。
1967年7月21日,由葉群出面,向海軍的李作鵬打招呼。她在電話中說:“張學思在東北時是反林彪的,以前他和國民黨有勾結。”要他們盡快送張學思的材料。
接到這個信號,李作鵬一伙搞出了一份“關于張學思的嚴重問題”的材料,給張學思羅織了兩條“罪狀”。一是說“張學思在東北工作時,與彭真、林楓等關系很好;來海軍后,忠實地執行了以蘇振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他在海軍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斗爭中,是完全站在蘇振華一邊的。”二是說“張學思有特務嫌疑”,“蔣匪特務機關長期以來策反張學思”,“張學思自己寫的自傳中也交代接觸過很多國民黨上層人物,蔣匪大特務戴笠還請他吃過飯。”
1967年9月11日,張學思被秘密逮捕。
寧折不彎
曾與張學思同期受迫害,就關押在他隔壁房間里的呂正操將軍,生前曾告訴筆者這樣一段情節:我們每頓吃的飯,是一碗發了霉的大米飯或一個又干又硬的饅頭,我們都不夠吃,可是張學思的精神壓力大,經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許倒,要留著下頓吃,他就拿張報紙蓋著。報紙上有毛澤東的像,看守的戰士就批他蔑視偉大領袖,他反駁,和戰士吵,便受到圍攻。每天晚上提審他時,他都據理反駁,和他們爭吵得非常厲害……
呂正操將軍認為,一是由于張學思對黨內斗爭認識上的單純,缺乏接受這場空前嚴酷斗爭的思想準備;二是他從母親那里繼承了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關押期間,所受到的心理傷害、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比其他人嚴重得多……
張學思的所謂問題,經過多次內查外調,搞了幾年也無任何證據,連“專案組”也泄了氣。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折磨之下,張學思本來很健壯的身體漸漸垮了下來。到1970年2月,專案組又派人前來“提審”時,張學思已走不動路。上下樓梯都要有人架著,哮喘非常嚴重,耳朵也幾乎聾了。專案組的人這才“發現”張學思確實病得嚴重,只得向上報告,將他送進醫院。
即使在醫院里,對他的迫害也沒有停止。筆者查到了張學思申訴的原始記錄:“我現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對犯人也要給一些寬大吧!等我病好了,怎么罰我都行,給我加罪也行,現在我不是來醫院治罪的!”
“我想從吃的方面來配合治療,所以我提出買東西。我也不是想吃什么貴重的東西。就是想吃點香腸、酸菜,他們說沒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馬鈴薯,這個不會沒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說沒有。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想把我的病治好,恢復成一個健康的人。即使給我加罪,你們也要等到我病好了再加呀!”
“這里這么好的山林空氣,對我這樣的病人是多么需要呀!可是這里幾個月不開門窗,還用鐵絲把窗子擰起來。我這樣的人還能跳樓自殺嗎?能不能給我點寬大?!難道飯不給我吃,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還不行嗎?……”
這是一個身臨絕境的人發出的求生呼喚!
1970年4月1日,周恩來的辦公桌上,放著中央軍委轉來的《關于張學思病情惡化的報告》。周恩來看完這份材料立即提筆批示道:“要告訴醫院,設法進行搶救。如果他們力量不夠,可以請301或其他醫院一塊兒進行搶救。”
李作鵬一伙對周恩來的指示置之不理。張學思的病情繼續惡化,5月初,張學思已完全靠輸液輸氧來維持生命。
據一位目擊者講述:張學思去世前的一天下午,長時間處于昏迷狀態中的他神志一下清醒了,他仰臥在病床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他寫完一遍,又寫了第二遍。身旁人員抓緊問他“惡魔纏身”是什么意思?張學思面部表情憤恨已極!他沒有回答。
1970年5月29日,張學思含恨離世,終年54歲。
平反昭雪
“九·一三”事件后,張學思的妻子謝雪萍意識到,為丈夫申冤的日子到了。她直接上書毛澤東,終于贏得對“張學思專案”的復查機會。1975年4月8日,海軍召開了給張學思同志平反、恢復名譽大會。
1980年12月,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批準了為張學思同志進一步平反昭雪的報告,對張學思同志作出了全面高度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