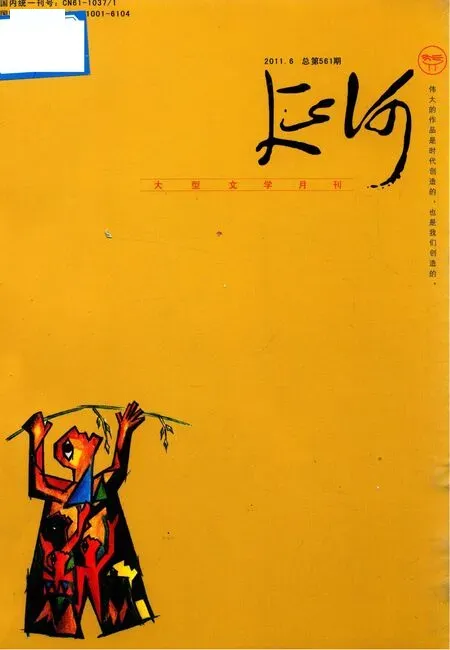沿著腳手架上升
常勝國
發生在當地的地產商人打人致死案已經過去了兩個月時間。事情平息以后我去訪問他,他說他還想起一些事情,這些事在他腦子里一再出現,都是一瞬間的事情,因為跟案件絲毫沒有關系,他就沒跟辦案人員提起。
就說戲樓灘那件事吧,他說,已經過去了20多年了,出事那天我肯定也想過那件事,不是有意要想,是它隨時都可能蹦出來。
那些年村里的戲樓灘總是聚集著很多閑人,那一天人就很多,有七八個。接著人又多了,有十來個。都裹緊了衣裳,一邊在戲樓灘避風的地方曬太陽,一邊等著什么事情發生。
冬天了嘛,這些人不種地就都成了閑人。他們沒處去,也走不遠,許多人一輩子都沒穿過襯衣襯褲,夏天單襖單褲,冬天棉襖棉褲。夏天還好說,冬天呢?北風像刀子一樣在褲管里袖管里攪,在外面站一會就得回家去取暖,他走得遠嗎?走遠了凍死他!
王旦到了戲樓灘,于是這一天的事情就發生了。戲樓灘今天多了一個挑擔賣熱豆腐的大男人,他棉衣里面還穿著襯衣襯褲,所以他冬天也能從一個村子走到另一個村子趕小集市賣熱豆腐。人們瞅著賣豆腐的男人,豆腐的香味讓人嘴里流哈喇子。王旦走到賣豆腐的跟前,想把這香噴噴的東西看個仔細,他緊緊地兜住嘴巴,不讓哈喇子流出來。
“吃哩?”賣豆腐的問王旦。
“吃……”
賣豆腐的坐著小板凳,面前放著裹著棉毯的木桶,木桶上橫放著一塊小案板,聽到王旦說了一個“吃”,他便從木桶里撈出一塊豆腐,放在小案板上切,把切好的豆腐攬在一只碗里,撒了一點家常的調料,桶里取了一雙筷子,一碗熱豆腐便推到了王旦跟前。
動作真快呀,一切都是眨眼的功夫。
“吃……吃不起。”王旦繼續說。
“你是誰的兒啊!”賣豆腐的大叫,把碗重重地放在案板上。
賣豆腐的從板凳上站起來,揪住王旦的領子要抽他,眾人搶過來攔擋,但賣豆腐的還是在王旦腦袋上抽了一巴掌。眾人七嘴八舌對賣豆腐的說:“不能怨他,是你手腳太麻利了,也該問清楚。”
“問清楚了,他明明說‘吃’。”
“什么你就問清楚了,他說‘吃不起’!他是個結巴。”
晦氣呀,賣豆腐的把一碗切好的豆腐放在桶里,用羅布蓋起來,挑上擔子罵罵咧咧奔大路去了,這大概要損失他幾毛錢了。
就這事兒,那天的戲樓灘就跟以往不同,人們離開的時候心里都懷著滿足。
“我當兵的時候結巴的毛病就要好了,但一不注意這毛病就容易犯……現在這毛病更厲害了。”王旦繼續說。“部隊里有一個小個子連長,他以前在我們這個地方當兵,挖防空洞。他喜歡喝一點小酒,每次喝完酒,他就會跟我聊起我們這個地方,他說我們這個城市很小,撒一泡尿就從這頭流到那頭。我當兵回來以后發現村子里的閑人還是聚集戲樓灘,許多人在冬天還是不穿襯衣襯褲。”
王旦從部隊復員回來,穿著嶄新的軍衣,冬天的時候不光在棉衣里面有襯衣穿,還有棉軍帽、棉軍鞋和一件軍大衣,還有絨線衣褲,可以在春秋季節換季穿衣裳了。經過部隊的鍛煉,他的身板是村子里最筆挺的一個,他的頭腦也是村子里最靈醒的一個。他很快就想到自己必須再從村子里走出去,從戲樓灘走出去,走出去,才有出息。當地人把出去工作的人叫“出門人”,出門人是富裕、有身份的代名詞。王旦出門以后最初在建筑工地上當小工,后來跟一個人販賣經過翻新的舊拖拉機,再后來這個人在城里托關系包到了建筑工程,仍然帶著王旦一起干。幾年以后,王旦結了婚,這個人成了王旦的岳丈。
“我最佩服我丈人會推銷東西,把不值當的東西當值當的東西賣,不動聲色。”
因為結巴的緣故,這個詞在王旦嘴里更令人回味。不值當……值當。
“我岳丈有一句有名的話,‘多少錢買的就值多少錢,’誰都知道這是用來安慰那些在買賣方面吃了虧的人,這很管用。在這方面我不及我岳丈……我有我的強項……我是個結巴。”
當王旦發現自己結巴的毛病不僅沒有給自己的發展帶來實質性的影響,而且給自己帶來很多便當,王旦偷偷地樂了。這個事最初在和自己的岳丈打交道的時候王旦就有發現,但他不能確定,后來他獨當一面,開始在房地產方面發展,這個認識又得到了加強。他第一次參與工程競標,把自己的資質材料遞送給一個行政領導,那個領導看了以后說:“無論是資歷還是實力,你都是最差的。”王旦已經不抱多少希望了。過了兩天,那個領導在一個宴會上打電話讓他來陪酒,他自然要忙不迭趕過去。他給領導敬酒,端著酒杯說:“啊就……啊就……”酒過數巡,領導指著他說:“啊就,啊就,請喝我一杯酒。”看著王旦喝完了酒,領導又指著他說:“啊就,那個工程就是你的啦!”幾乎是一瞬間,一個新的地產大王和億萬富翁誕生了。無論王旦怎么分析其中的原因,都無法得出確切的結論。后來有當地的風水先生試圖在王家的祖墳里找到王旦發跡的答案,王旦根本不信那個,我王家都窮了幾輩子了,咋就不見祖宗顯靈呢!王旦自己仍然在尋找答案,他的不同就在于他是一個結巴。他也在領導眼里看到了領導對一個結巴的特殊興趣。王旦悄悄觀察了別的結巴,得出結論:由于語言的障礙,結巴不會為了得到好處而更多地去言說自己,不會因利害關系讓謊言隨口而出,這是口齒伶俐的人們最致命的弱點。結巴看上去有點木訥,有點傻。人們更愿意與一個結巴,一個有點木訥,有點傻的人打交道,并愿意結成伙伴關系。

李巖素描作品No.4 1997年 圓珠筆、紙 31cm×24cm
一天夜里,王旦從睡夢中笑醒,媳婦問他笑什么,他說:我不該笑嗎?媳婦說:該。兩個人一起笑了半夜。王旦鄭重對媳婦說:“以后你的穿戴盡量要簡單一點,家里也不能置家當,越簡單越好……不要讓人看出咱有多少的資產。”怕媳婦不知道穿戴要簡單到什么程度,王旦回想了半天,想起一個人來:“咱村里保富不是在工地跟小工嗎,他家里的就在巷口菜市場賣菜,她穿什么,你就穿什么,只能比她穿得差,不能比她穿的好。”媳婦也識得好壞,說:“那我干脆跟保富家的一起賣菜去。”王旦說:“那倒不必,家里也有好多事要做哩!”
其后發生了一些事情,使媳婦看到丈夫的過人之處。這一年,城鎮周邊地區一個村子因為耕地被過多地廉價出讓而引起村民的不滿,在多次上訪無果的情況下,村民們組織起來重新丈量了被廉價出讓的土地,發現自己珍貴的土地不僅被少數負責人賤賣,而且被貼出去許多。“二百斤的東西當二十斤賣了。”村民們說。在隨后各級組織漫長的調查之中,村民們都等得有些不耐煩了,他們列出了一份曾經購買過本村土地的地產商人的名單,開始自發組織找地產商人取證,王旦第一個被列入名單。這時的村民都有點頭腦發熱,幾十號人憤怒地擺出要找“王八蛋”算賬的架勢在一天早上撞開了王旦的房門,王旦已經來不及報警和做出其他反應就被頭腦發熱的農民擠得不能動彈。其中沖在最前面的幾個村民思想更為簡單,也更為激進,私下里已經商量好這次行動要給大資本家王旦一點厲害瞧瞧,至少要讓他臉上掛花,再砸他幾件貴重的家具,總之要把事情鬧大,好引起上面的重視。但他們看到這個不足100平米的房子里根本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有一組一高一低的柜子,可以明顯地看出是20年前當地木匠的手藝;墻上掛著的相框里貼著老老小小的相片,完全是偏遠鄉村的風格;在自來水龍頭下面甚至還置放了一尊蓄水的大甕,甕沿兒上掛了一只銅馬勺;就連電視機都還是木殼的,古董級別。這個家顯然要比興師問罪的農民差了很多。在王旦結結巴巴戰戰兢兢的應對當中,他的起得很早的媳婦也從外面回來了。這天早上,她到菜市口去買菜,順便幫寶富家的賣了會子菜,回家時寶富家的揀了一顆蔫白菜讓她提在手里。她看到自己家門口和樓道里擠滿了氣勢洶洶的人就知道大事不好,她的臉也被嚇白了。人們給這個土頭土腦、穿著廉價舊衣服的家庭主婦讓開一條縫,讓她在熱騰騰的體溫冷冰冰的面孔和能嗅得見沸騰血液的仇視中走進自己的家門,她盡管還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但她明白眼下的事情非常嚴重,情況十分危急。她懷里抱著一顆蔫里吧唧的大白菜已經站不穩腳跟了,她跌倒在地上哭了起來和蹲在地上的同樣穿著老舊衣裳的王旦構成無比協調的夫妻圖畫。最先沖進來的幾個思想激進的村民簡單地問了王旦幾句話就都耷拉著腦袋轉身出了屋門。他們沒想到王旦結巴得如此厲害連一句簡單的話都說不清楚也沒想到一個大名鼎鼎的地產商人的家會是如此的寒酸。擠在樓道里的人見前面進去的人一言不發就退了出來,有點看不明白,像參觀一個向往已久的古董作坊一樣,他們抓住時機把這個家參觀了一下,有幾個婆娘甚至還對懷里抱著一顆大白菜癱在地上抽抽搭搭的王旦媳婦說了幾句安慰話。對王旦的造訪改變了村民們的固執和對整個“貼地”事件的看法他們不想再追究“貼地”背后的深層次問題而只把問題追究到個別負責人工作馬虎不負責任為止。正像他們預期的那樣,對“貼地”事件的調查最后以個別負責人工作馬虎責任心不強而收場。
那位行政領導從一開始就對王旦另眼相看,在發生了“貼地”事件以后,領導又做東辦了一個宴席,犒勞在“貼地”事件中忙前忙后的相關人員。宴席上,王旦急成一個大紅臉,試圖向眾人還原那天早上的情形,卻根本不知道要從哪里說起。“行了。”領導忍俊不禁,“大家就不要難為他了。我來替你說吧,什么事都沒有,對吧?”“……對。”
“看不出來……”領導繼續說,“你還是個蠻有政治頭腦的人。看來做生意也要講政治。”
王旦的臉更紅了。“要……政治。”語言表達有困難的王旦試圖說服在座的地產商人,應當成立一個“同盟會”,維護地產商人的合法權益,房地產價格要漲一起漲,要跌一起跌,并且根據當前的市場行情只漲不跌。
在杯盞交錯之時,他們議定了同盟會的幾條基本草案。領導對一切都很滿意。
“政治!”領導讓服務生給每只酒杯都斟滿了酒,并率先端起酒杯。
“政治!”每個人都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由于王旦的語言障礙,使我對任何細節的追問都極其困難,加上他有一個敘述習慣,凡事都要從他所認為的根源談起,因此我對他的訪問也變得極其緩慢,直到對他進行第三次造訪,他才談起出事那天的某些細節,這也影響到了我對整個事件的表達和行文的方式。
房地產商人們會在每年的九、十月間推出自己更多的成型產品,這是房地產的銷售旺季,房價會在這個季節呈現出最理想的價格。據說許多房地產商人對明顯帶著農業化特質的房地產銷售行情多少有些急躁,而王旦是農民出身,深知同樣是農民出身的工人在秋收季節都會提出回家參加秋收的請求,這時,王旦就把工人每天的工資提高一倍,讓工人們覺得劃算而繼續留在工地上干活,使自己的產品能夠在旺季如期推出——把雙方的損失都降到最低,這是王旦自己想出的應對之策。今年王旦推出的是一個占地超過25畝的高層樓盤。出事這天早上,王旦來到工地,在中秋早晨的霧靄之中,黑黝黝的建筑物極像是幾個蓄勢待發嗜血成性的龐然大物,樓層腳手架和防護網會一直維持到裝飾工程結束,那時,撤掉腳手架和防護網的樓層會是這個城市最漂亮的建筑物之一。王旦乘升降梯上了樓頂,查看這棟樓主體工程最后部分的進展情況,工人們也會因為老板的出現而加快手腳干活。王旦站在樓頂向遠處眺望,晨霧的消散使城市有一種瞬間膨脹的感覺;王旦也是在瞬間想起在部隊時那個喝一點小酒便要找自己聊天的小個子連長:“你們那個城市很小,撒一泡尿就從這頭流到那頭。”王旦知道自己多少有點留戀部隊生活,常常會想起戰友和小個子連長。但眼下這個城市最不好找的便是撒尿的地方。當一個又一個億萬富翁在這里誕生,找地方撒尿就顯得更加困難并且更需小心翼翼。“天曉得這是怎么回事,”王旦想問問小個子連長,“這里怎么會冒出那么多的富人?”
在樓下的一間大廳里,王旦的老岳丈正在開始這一天的售樓營生。這個老頭一年四季嘴里叼著幾毛錢一包的“工”字牌雪茄煙,而且他每天吸煙常常不會超過一支。他總是讓寬大的上衣敞開,喜怒不形于色,把最可靠的一面充分展示給眾人。無論從穿著上還是從行為習性上人們都能夠驚奇地看出他和他女兒以及女婿之間共同的家族特性。為了讓樓盤按照既定的價格盡快售出,這個精明的老頭把自己的那句名言作了一些修改。較熟稔的人從他手上接過定單總會用那句名言和他開一句玩笑:“多少錢賣的就值多少錢。”這時老頭的嘴里多半還叼著香煙,仍然不動聲色:“今天買了,明天就會升值,如果不是這樣,你把東西給我退回來,我說話算數!”沒有人把東西給他退回來,大家都看到啦,樓市百分之百被他言中。
因為中秋節就快要到了,王旦想起要和岳丈商量給各個部門的頭頭腦腦送禮以及中秋節會餐的事,通常這些事老岳丈早有安排,王旦只需問一聲,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他乘升降梯從樓頂上來,向售樓大廳走去,這時有一個人正從不遠處朝自己走來,這個人正是本文要談到的死者。
“你怎么抽起十塊錢的煙了!一天兩包煙夠幾天的生活費!”妻子質問。
“抽好一點的煙對身體危害小……是八塊錢的。”丈夫回答。
“那你咋不把煙戒掉!又省錢又沒有危害。”妻子說。
了解高來有的人從點點滴滴向我談起高來有的生平。他從高來有因為抽煙的事和妻子鬧別扭談起(他們夫妻總是鬧別扭)。這是一個讓所有煙民普遍為難的問題。高來有后來把煙戒掉了。但事情的發展出乎人的想象。
“你這是糟踐錢呢!你會糟踐,我也會糟踐!從今天開始我也抽煙,咱都抽十塊錢一包的,看這個家怎么爛包!”
“那你就抽,誰攔你了。”
妻子果然就開始抽煙,這個別扭鬧了很長時間,每天總有那么一會兒工夫,夫妻間互相惡狠狠的盯著對方,大口大口地抽煙,并把煙吐到對方臉上。別扭過后,高來有把煙戒了,但妻子卻抽上了癮,只是把每包煙的標準降到了五塊錢以下。真是罪過啊!妻子因為當時的情形覺得對不起丈夫,她想再引誘丈夫抽煙,她幾次有點難為情地把香煙給丈夫遞過去,都被丈夫拒絕了,丈夫實實在在把煙戒了。從這時開始,妻子為人做事越來越像一個男人,把一切事情都包攬到自己身上,也許她要高調證明自己吸煙上癮的理由。而丈夫卻愈發縮頭縮腦起來。
這一切都是從他們夫妻經營一個賣早點的地攤開始的。他們所在的單位政策性倒閉,他們失業了,除了要把一雙兒女撫養成人,他們還想比別人過得更好一點,還想從兩間破破爛爛的老祖屋里搬到好一點的地方去居住。于是,妻子提出要經營一個早點攤子,丈夫卻首先想到這個早點攤子過不了幾天倒塌的時候是多么令人難堪。在一番爭吵之后,丈夫未能提出更好的謀生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和妻子去練攤。一天早上,他們在街角找了一個位置點起了爐灶,妻子讓丈夫看著爐灶,自己回去取一些必要的東西。過不了一會,來了稅務人員向他收稅,“我這還沒開張呢!”他這個人一定是天性有點毛病,一旦遇到他極不情愿的事,言語就十分沖撞。“我這還沒開張呢,”在稅務人員聽來就好像是“我這就要操你媽了!”他們發生了爭吵,幾個稅務人員一怒之下放翻了他的爐灶。事情過去以后,他無論如何都不肯出去看爐灶了。“這有什么!你就不像個男人!”妻子只好自己一個人經營早點生意。這時她的嘴上就開始叼起了香煙,并且嗓子變得越來越有磁性的味道。她慢慢和包片的稅務人員處好了關系,他們不再主動收她的稅,見了她還跟她直客氣,等她想起要交一點的時候就交一點。后來她發現夜排擋比早點更紅火。夜排擋在這個地方興起比較晚,但勢頭迅猛,夜排檔消費者不光人數眾多而且出手也大方。她將自己的食譜作了一些改動改賣夜排檔了。她學會了陪客人喝酒,每當她喝酒的時候,生意就出奇地好。這時候,高來有還在跟她慪氣,為了排遣怨氣,他開始迷上了書法,因為自己以前在單位是個文職人員,自認為有書法的功底。他一天到晚躲在家里練書法,并且在和當地的幾個書法家接觸后得到書法家的表揚因而沾沾自喜,按照書法家的口氣,他把自己寫的字叫“作品”,在家里墻上掛滿了自己的作品。“這個家里死了人了嗎?鬼符似的掛了這么多白紙!”盛怒之下,妻子把他的作品一把火燒了個干凈,連筆墨都沒有留下。他的理想被現實瞬間粉碎,不留一點痕跡。之后妻子的夜排檔更忙了,她把自己能夠動員的家人都動員到夜排檔來幫忙,只有高來有還不肯在夜市上露面,妻子也打消了讓他幫忙的念頭,因為他一開口就要操人家媽,只能幫倒忙。
“我不會就這么窩囊下去的……我會讓你看到……”在隱忍和怒火之中,高來有思索著自己的出路。
日子就這樣過去,如果不是股票和樓市突然在一夜之間成為這個城市最熱門的話題繼而成為快速致富的神話,也許高來有家艱辛的日子會在妻子辛勤的操持下得到改變,誰知道呢。妻子得知通過銀行購買一種叫“基金”的東西可以得到比自己賣夜排檔高幾倍的利潤,她抱怨自己只會下死苦掙小錢。她和幾個下死苦掙小錢的姐妹在一起就投資基金的事情開了幾次碰頭會,經過一番今是而昨非的論證之后恍然大悟:“不懂得投資就永遠翻不了身,永遠改變不了貧窮的命運。”她們互相打著氣,在銀行里托了關系,在權衡了風險和效益之后,各人把自己可以調動的資金委托給銀行購買了投資基金,想著這樣的好事居然也輪到了自己頭上。大家都看到啦,命運始終在和人開玩笑,僅僅過了幾天,股市就開始暴跌,她們委托銀行投資出去的基金全部被套牢。而投資熱沒有因為股票的暴跌而消解,她們中間的一個姐妹偶然投資了一套房又把房子賣了出去,從中得了幾萬元的利潤,這個消息一公布,她們就開始想辦法籌集資金,決意要在房地產領域打彩碰命。經過調查以后,她們選擇了在社會上享有較好聲譽的房地產公司,她們知道了王旦的名字。“如果投資不值,你們可以把房子給我退回來。”她們在那個老頭的信誓旦旦的承諾下拿到了房子的訂單。事實上,許多購買者的房子根據本人意愿在這個老頭手里得到了二次出售,這時房地產商人宣布房子已銷售罄盡,在二次出售的過程中,老頭和購房者都獲得了利潤,房子就是在這樣的倒騰之中從現象上變得越來越緊缺。
當一種投資變得非常急迫,無論投資的前景如何被看好,這種投資都有一些鋌而走險的味道。她們遇到的最要害的問題是始終不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加上對風險意識的模糊認識,使她們的投資運動始終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突然有一天她們聽到有風聲說房子要降價了,她們嚇壞了,她們很清楚,無論是家庭還是她們自己,這都是她們最后的本錢。她們在一起碰頭,都喝了一點酒,有一種末日來臨的感覺。很快有人做出假設,如果投資虧了本,翻本的資本就剩下她們的身體。她們這時都有三十來歲,這個資本也要稍縱即逝了。高來有的妻子被大家推選為“在身體投資方面最有資本的女人”,既然她是房地產投資的積極倡導者,她也要首當其沖為大家在身體翻本方面做出表率。
“至于嗎!咱們別關起門裝鬼自己嚇自己。”她點了一只煙抽,即使她沒有把“身體翻本”當一回事,她也真的想了自己有沒有身體方面的本錢。
她們的投資心理在一會兒可能漲一會兒可能跌一會兒可能不漲也不跌的風聲中忍受著煎熬。她慢慢有點疲沓了。“看著吧,我們也許不會那么倒霉!”她給姐妹們打氣,“行了,真要用身體翻本,我先來,我先來探水……”
高來有過了很多日子才知道妻子背著自己搞起了投資,她在七姑八姨那已經拐來很多錢,他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背了幾十萬元的債務。他簡直要瘋掉了。除了和妻子爭吵以外,他一天到晚在翻看關于房地產行情的電視節目,越看越覺得房地產行業簡直就是一個騙局,少數人占據了原本屬于大家的土地資源,回過頭來憑借手中的資源掠奪大家的財產,這本質上跟過去的地主階級剝削貧雇農有什么區別!而且他們的方法之卑鄙手段之惡劣比之過去的地主階級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可惡的騙子,該死的剝削階級,根本就是我高來有的敵人。
“你不是我的老婆,你是我的敵人!敵人!”
這天夜里,當妻子收拾了夜排檔的家什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里,發現高來有又開始在抽煙,地上足足扔了一包煙的煙蒂。她試圖向他解釋事情的經過以及投資改變生活的可能性,他卻根本聽不進去,在一陣咆哮之后,他說:“你別指望我跟你一起背一輩子也還不完的債務,我要跟你離婚!”又是互相惡狠狠地盯著對方,大口大口地抽煙,并把煙吐到對方臉上。高來有在很多情況下說話就仿佛是在“操娘”,她在很多情況下把他的話當作放屁,又在更多無奈的情況下把他的話按照相反的意思來理解,“我要跟你離婚”可以理解為“我們要更加親密”。
“嘿!”她冷笑著說,“也不看看自己,你有什么資本跟我談離婚的事!要談也該我來談!”
當天晚上,他的話很少,不知因為什么原因,妻子突然發現丈夫說話時變成了一個大結巴,連屁話都說不了了。
第二天她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天氣在一夜之間突然轉冷,她渾身冰涼,看到一夜未眠的高來有臉色蒼白,瑟瑟發抖,在一陣翻找之后走出門去。她打了一個冷戰,想到他也許要弄出點什么事來。
“他大概在翻找衣裳。”像往常一樣,她開始了一天的生計,要備好夜排檔的材料,不長時間,有人向她通知了高來有死在建筑工地上的消息。
“他一開始就跟我拉開罵陣的架勢……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他頭發蓬亂,衣衫不整,連扣子都扣錯了,當時怎么看怎么覺得他像是一個小混混,像一個吸毒的人。”王旦說。
“吵完之后,有一陣子我和他都歇下來了,各自坐在幾步遠的地方喘氣,可是突然間他又向我撲過來。”
這一次,他們幾乎一言不發,高來有氣洶洶向王旦撲過來,王旦怎么甩都甩不開,他怒火滿腔,用力!用力!最后用瞬間的力量把高來有摔了出去。
高來有躺在地上不動彈了,最初王旦以為他這種人就有這種本事,動不動就躺在地上訛人。后來有工人走過去摸了摸他,發現他已經死了。
“真是倒霉透了……”王旦說,“你知道當時怎么回事?我突然發現他也是個結巴,我們互相都以為對方在嘲笑自己,這就是火藥桶,兩個結巴在一起沒法吵架,只……能打……打!”
在工地上的工人想討好他們的老板,出主意要把高來有的尸體抬到別的地方去,被王旦的老岳丈罵了回去。也是他第一個接觸了死者的妻子,開始商談民事賠償的事情。這時他們都知道,他們彼此投資的房地產行情又連連看漲,這也許是告慰死者的最好的禮物。他看到她神情木訥,嘴上叼著煙,也許還喝了一點酒,他急忙就把自己嘴上的雪茄煙掐了。“你開個價吧……事情不該是這個樣子,他不該對你的投資不滿意,投資天天都在升值……中間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都很難過!”
她不曾想到,她的投資會是這樣一個結果,無論回報有多么豐厚,代價都顯得太大。看著眼前那個喋喋不休的黑洞洞的出口,她忽然朦朦朧朧意識到:她,他們,已經被某種力量推向了另一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