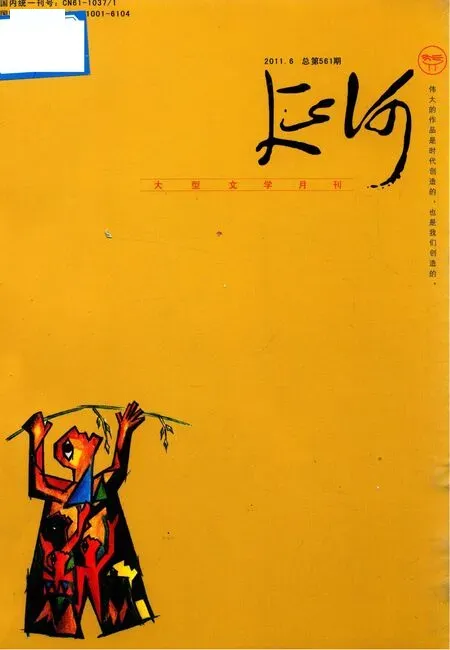勝算在握
李丹萍
事情有些荒唐。人人都說,老公偷情,當老婆的最后知曉。這種事,只要沒捉奸在床,當老公的,說不認贓就不認贓。偷情么,既然偷,哪個聲張?但何海就聲張。而且在外邊聲張不過癮了,回家聲張到杜晶晶跟前。要不怎么說事情荒唐呢。
杜晶晶不信。
雖然,杜晶晶早就發現何海某些不正常的舉止,比如說他動不動就站在洗手間里剪鼻毛,比如他出門前愛往嘴里扔個口香糖。這些講究,他以前都不曾有過。再比如說他動不動就微笑著恍惚起來……這些,傻瓜女人都知道是危險信號,特別是“動不動就微笑著恍惚起來”,可是男人真心愛上女人的標志性表情。這些信號在杜晶晶眼皮子底下發射已經有兩個多月了,作為女人,作為人之妻,她不可能感覺不到。不是感覺不到,是不信,是鄙夷:就他,憑什么!
就是,他何海憑什么?
憑長相?拉倒吧。黑黃膚色,倒八字眉,一口煙熏火燎的碎米牙。身高,滿打滿算一米七,又胖。這些都不說了,關于男女的定論是:女人愛上男人,不是因為他們的外在,而是因為他們的能力。男人的能力拿什么衡量?錢呀,事業呀。再歪瓜裂棗的男人,只要有錢,只要事業有成,就性感,就招人。可何海事業有成個屁呀,說起來都丟人。他先在鄉下的獸醫站上班,才上班不久,因一把手整他,他把一把手打得住了院,他人逃了。避過風頭后,他回來了,經人介紹,他們兩個陌生男女就閃電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時候杜晶晶的伯父還在市上任著一官半職。由伯父從中斡旋,何海得以重回獸醫站,繼續當他的獸醫。他干了幾年,不想干了,膩著杜晶晶的伯父要調走,但因為打領導一事弄得聲名狼藉,沒單位肯要他。
這么三搞兩不弄的,直到杜晶晶伯父退休,他才徹底沒了搞頭。頹廢了好幾年,然后開始寫小說。偶有作品見報。小豆腐塊兒,還是倚著杜晶晶伯父的老臉。何海的偉大理想是當李白。不需太多醞釀,啪嗒,下一個蛋,啪嗒,又下一個蛋。個個是金蛋。杜晶晶心里明鏡似的,他做夢呢,這哪是正常人思維呢。作為有著正常思維的杜晶晶,當然不準他脫離實際。她的意思是他就在獸醫站干著,忍,只要有耐心,一步一步往前挪,總能等到屬于他自己的那個坑位。急什么?他哪里肯聽,把她當攔路虎,恨得武松的勁頭都使出來了。到底沒牛過他,單位每個月扣去他工資二分之一的錢請來代理替他,他成了有業卻自由的撰稿人——幸虧有伯父,不然,他將被直接削為貧民。
鄉獸醫站的工資,用腳趾頭想,都能想出它的多少,不要說又被生生削去二分之一。
他自由了。自由就得付出自由的代價,總不能老賴在獸醫站寫他的小說吧。天底下,沒這么一說,就算再有她的伯父,她杜晶晶的臉皮也不能厚到令人發指的地步。第一要務:往后住哪走?第二要務:以后怎么個活?
何海氣定神閑,他早就思謀好了:辦補課學校。只辦初三、高三的復習班。
你想,現在的家長多重視孩子的學習啊,復習再讀一年的學生家長更是急得眼冒金星。縣城一共有三所初中,兩所高中,每所學校,每門課,都有一兩個硬頂硬的老師,聲名遠播。好,就盯住他們,雇用他們。要來他們的課程表,仔細研究過,那個老師那堂課有空閑,直接拉來補課學校,上完課,立馬送走,絕不耽擱人家正式教學。這么著穿插編網,密而不亂,按節計費,絕對是高效益高報酬。
事實證明,除了極少數幾個不肯折腰的外,絕大部分被何海他們看中的老師,都愿意掙這份并不辛苦的意外錢。
杜晶晶依著何海的計,從伯父處借錢買來三輛二手車,雇來三個司機,這三個人專門在幾個學校門口守株待兔,下課鈴一響,迅速發動車,只見那些平時鵝行的老師便像兔子一樣躥進面包車,車像劫持人質一般,絕塵而去。
由于每個老師在縣城里都響當當的,杜晶晶辦的高費補課學校,學生爆棚,兩口子賺了個盆缽溢出。
這錢掙得容易啊,兩口子彈冠相慶。其實,這件事里最關鍵的人物,不是何海,也不是杜晶晶,而是杜晶晶的伯父。不說借錢給他們,就說沒有老人家倚老賣老地在上邊活動,各個學校固若金湯的大門怎么會像被施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樣,隨意為他們開合?學校校長憑什么允許他們挖這樣的墻角?
伯父伯父,像陽光一樣照耀大地的伯父。
何海譜大,趴在家里寫小說的時候,左手隨手撈著鹵牛肉,右手隨時啤酒侍候,嘴里抽著軟中華。進得多,出得少。他整個就是一負數。男人正五正六的都在家乖乖地守著自己的老婆,他一個負數男人,居然偷腥?!——老天要是允許這么干,就太不像話了。
沒天理的事,杜晶晶不信。
然而由不得她不信,是何海自己跟她說的。
先是試探著說。
早晨,杜晶晶照例拾掇房子。她討厭何海亂扔水果皮煙頭的惡習,況且煙灰缸垃圾桶就放在他手邊身邊。跟豬似的,走那拉那,她一邊拖地,一邊嘟囔。通常情況下,他不吭氣,也不改,甚至會當她的面,再扔一個蘋果核,以示抗議。但那天,他轉過臉,認真地對她說,勸你好好些。你不待見我,自有人待見。杜晶晶聽了,呵呵一笑。何海大聲說,好!一把拉過她,指給她看他正在看的一封郵件,像是一首詩:
我喜歡牛奶,更喜歡奶牛,
請問,我何時能把奶牛牽回家?
我會把它照顧得溜光水滑,
從而讓它產出更優質的牛奶。
看不懂。懶得弄懂。在杜晶晶直起腰欲走之際,何海給她解釋,牛奶是指我寫的小說,奶牛是說我這個人,她的意思是說,她很喜歡我寫的小說,更喜歡我這個人。她想跟我過,好讓我這個懷才不遇的作家寫出更好的小說。
于是,一個叫上官絳珠的女人,浮出水面。
據何海講,上官絳珠的父母,雙雙是大學生,有文化,喜歡讀《紅樓夢》。為什么給女兒取名叫上官絳珠呢?絳珠,絳珠草之意也,林黛玉的化身是也——你瞅瞅人家的境界。
杜晶晶聽來,啞然失笑:絳珠,嗬嗬,犟豬。
杜晶晶對何海的話是這么理解的:比如是一盤子菜,餿了,馬上要被倒掉了,菜有危機感,自己吆喝,我好香呀,誰誰誰都想吃我了,人家可是大人物——怎么,你還不寶貝我?杜晶晶懶怠搭理他,她才不著他的套兒,他肚子里裝些什么牛黃狗寶,這么多年夫妻當下來,她最清楚。
在這之后,何海每逢杜晶晶對他態度不好,就拉出上官絳珠說話。有一次兩人在床上,何海指責杜晶晶大腿太粗,指責她乳房上有皺紋,說她太老。你看看人家絳珠,何海舔嘴咂巴舌地說,人家奶大,屁股圓,腰細,三圍好得不得了,人家一點皺紋都沒有,人家到底是年輕。
就這,杜晶晶都沒太當回事兒,她只想一腳把他踹床底下。什么玩意兒,還越說越來了。真是寫小說人的天性,愛編。
事情突然像一記重拳打過來把她打得暈頭轉向,是在夏日的一個燠熱的下午。
那天,一回家,她就發現不對勁。她看見他掛在院子曬衣繩上的衣服,剛洗過。他居然主動干家務,稀罕。走進房子,只見何海穿著睡衣倚坐在床頭,緊皺著眉頭在抽煙。
家里是不是藏著你的上官絳珠?無聊吧,這么表現?杜晶晶環顧四周,跟何海開玩笑。
我讓上官絳珠給陷害了,何海狠狠吐出一口煙霧,嘶啞著聲音說。
看他的樣子,不像是說笑,好像很嚴重。
杜晶晶臉上的笑意還未退盡,人不由得緊張起來了。
何海說,我今天上街,正走著,上官絳珠給我打電話,說她想見我。不知道為什么,一聽她那么說,我就覺得有種危機四伏的感覺,我就一直小心著。她說她在蓮湖公園等我,我就去了。我跟她在湖邊說著話,正說著,見上官絳珠的老公從湖邊站起來,手里提著棍子,胳膊粗,一腿長,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上。
杜晶晶狐疑地看著他,猶自笑著,問,那么,那會兒,你的上官絳珠呢?
我挨打了,她解恨了,早跑沒影了。我再說一遍,這是陷阱!是陷害!
真的不像是開玩笑。是真的。看來真有一個叫上官絳珠的女人?真有女人看上何海,跟他搞婚外戀?不對呀,就算因為外邊的女人挨打,也應該被堵在房子里打吧?大白天的,公園里,只是說說話,就挨打?
杜晶晶把她的疑問一個一個說出來,何海暴躁起來,啊呀道,不信你查去,我的摩托車還在公園擱著呢。
不管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當務之急,是趕緊把摩托弄回來。別的,秋后算帳。
老公讓情人的老公打了,當老婆的去推車,這種事兒,杜晶晶干不來。臊得慌。遂打電話給她最好的朋友于小鳳,讓她幫忙去推車。
于小鳳招之即來,杜晶晶不做解釋,只說讓她去哪哪推車。杜晶晶嚴防死守的樣子,于小鳳馬上意會,眼睛先把何海看了個透徹,抓過鑰匙,滿臉意味深長的笑,小跑著去執行任務。
到晚上,于小鳳才把車推回來,臉上的笑意更濃。從杜晶晶跟何海結婚到現在,于小鳳的臉上時常露出這種意味深長的笑。一看到她這種笑,杜晶晶就有種四處漏風的感覺。
本來想好,要對何海來個嚴刑逼供,但是,何海說他頭疼得去醫院拍片兒。杜晶晶忍著氣,陪他去醫院拍CT。看完片子,醫生說沒事,何海很不樂意,說什么叫沒事?是不是人死了才叫有事?跟醫生吵,吵一肚子氣回來。杜晶晶看他身上連片青都沒有,憑直覺,她認為他是小題大做,又怕萬一有內傷,少不得按下氣惱,時不時地給他按兩把,不一會兒,他呼嚕連天,睡著了。
她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沒等她問,何海掙扎著起身,讓杜晶晶把拍CT的票根,抓的藥的憑證歸攏一處,他說,得找他們去,讓他們賠償,這事不能這么便宜。
杜晶晶不去,她必須得知道事情的真相。
事情的真相就是,何海厲聲說,你老公,我,被陷害了!上官絳珠想訛咱們的錢,設套兒讓我鉆,我鉆進去了,現在出不來了,你要是不幫我,咱們就蝕大了。
也就是說,你們真的有一腿?杜晶晶慌了,喘不過氣兒。
何海低下頭,不吭氣,算是默認。
杜晶晶頓時氣促,呼呼大喘幾口,極聲尖叫,胳膊掄圓了,瞄準他的頭,掄過去。不解恨,咬緊槽牙,又掄一家伙,像打在冬瓜上,發出的不是脆響,是悶聲。聽聲音都知道,打重了。
何海硬挨了這兩下,一臉的小不忍則亂大謀。
打完,杜晶晶就后悔了。那兩胳膊,像是交接儀式。現在,他輕松了,因為交接儀式已經完成,沒他的什么事了。他該負的,都通過那兩胳膊卸到她這邊來了。剩下的,就是她的事了。
杜晶晶像被抽了筋似的癱軟無力。
等她情緒平穩后,何海坐起來,推心置腹地對她說,上官絳珠那女人,長的一般,還沒你好看,不過仗著身材好、氣質好、出身好。她居然跟一個農民愛了十幾年——你想想,能跟一個農民愛得死去活來,而且一愛就是十幾年,這個女人能是個什么好東西?
這話杜晶晶不愛聽。特反感。什么叫“居然跟一個農民”?你何海難道離“農民”十萬八千里?去你媽的,你也不過一在鄉獸醫站上班的獸醫。
她哼哼冷笑,說:她能跟你好上,確實可能不是個好東西!
杜晶晶對上官絳珠的老公充滿好奇,想不出什么樣的男人,能被老婆戴如此大的一頂綠帽子。何海說,就是。那個男人很瘦,很黑,樣子很猥瑣,是單位的小司機。
是么——我就不明白,上官絳珠圖你什么?
一,她愛我的小說。二,性,她是性亢奮,誰都滿足不了她。就我能。
對于第一點,杜晶晶認為簡直是胡扯,她不相信有哪個女人會弱智到分不來什么是水泥蛋什么是銀蛋的地步。也許,后一點,倒是合理的解釋。何海在性上確實行,很行,像騾馬一樣行。但是,男人再好的床上功夫,也像夜光杯,只有在暗室里才看得清楚。杜晶晶也是女人,她不太相信真有女人肯單純為了性跟男人好的。
她想起于小鳳意味深長的笑,渾身不自在。何海點撥她:上官絳珠不會善罷甘休的,她會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最有可能的可能是,她攻上門來,把他搶到手。
杜晶晶一聲長嘆。是的,她不能讓上官絳珠攻上門來。何海說得對,最好的防御是進攻,他們得化被動為主動。
她按何海的策劃到上官絳珠單位找上官絳珠。但上官絳珠的同事說,上官絳珠請了一個月的長假。至于原因,對不起,不知道。
何海又在電話里的指示,杜晶晶可以去找上官絳珠的老公——
見到上官絳珠的老公,杜晶晶暗暗吃驚。
眼前的男人是瘦,是黑,但瘦得清爽,黑得洋氣,穿著打扮很有品味,看不到一絲何海所謂的“猥瑣氣”。而且,人家也不是什么“小司機”。人家確實開車,不過車呢,是公家配的。人家是單位領導,一把手,所長。
弄得杜晶晶直眨巴眼睛。她硬撐著,用下巴報上家門,說我是何海的老婆。
上官絳珠的老公盯著看了她好大一會兒,一副我不找你,你倒找我來了的詫異。
請問大姐您有什么事?請她落座后,他客氣地問。
杜晶晶尖聲說你憑什么打人!話一出口,她就在心里皺眉,她覺得她說話的聲音像是賣菜的大嫂們的聲氣。
他平著臉,低聲說,對不起,這是上班時間,不方便談私事。
噎得杜晶晶說不出話。略加沉吟,她只好直接進入何海策劃中的第二步:把一沓票據掏出來,展平,放到他辦公桌上。
他瞄了一眼,一愣,不相信似的,伸長脖子仔細地看了看,一張張地翻過去,嘴慢慢地張開來,驚異地看著杜晶晶,突然間就笑了,拿筆在票據上啪、啪、啪敲打著,一臉的意味深長。
哦,該死的,跟于小鳳一模一樣的表情。
一瞬間,杜晶晶把何海周密的計劃全忘光了。她意識到她在丟人。她想,我已經在丟人了,我不能再丟人了。她調整坐姿,力圖讓自己顯得優雅些,斯文地說,我想你是誤會了。我來,一是告訴你,管好你老婆。二呢,你把我老公打得拍片子,花了不少錢——但是這錢,毛毛雨,我們出得起。我們不差錢。就是讓你知道而已。
他依舊看著票據微笑,但已經笑得不是讓她那么難堪了。
他頓了頓,斟酌著用詞:我不想過多地解釋。如果您一定要解釋,那么只好等絳珠本人回來,問確切了,再說。
她怎么……?杜晶晶心懸起來,問得有些結巴。
她目前么,沒在家,上官絳珠的老公不肯再說。沉默中,他從肚子深處吸出一口氣,緩緩地呼出來。
他失神地望向窗外。
窗外空調主機上,放著個青花大瓷碗,碗里種著花。碗華貴,但種的花卻不怎么華貴,居然是太陽花。各種顏色的太陽花開得像傻子一樣單純。這應該是上官絳珠的手筆吧?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杜晶晶不敢往下問了。
你老那么笑來笑去的,今天你說,你什么意思?坐在超市休閑區里,杜晶晶惱火地問于小鳳。
那好,于小鳳笑嘻嘻地說,說了,同志,你可得給咱頂住啊。
神經,說!
好好。你老公,啊,聽好——于小鳳拖著長音兒,用吸管攪動杯底的珍珠粒兒,賣關子,看杜晶晶真惱了,才舉手投降說:咱就說那天蓮湖公園的事兒。那天我一去,就見何海的車在湖邊倒著,我嘛,就過去扶,亭子里打麻將的老頭兒一看,就問我,你誰呀?我就說我是誰誰誰,是誰誰誰讓我來推車的。說完了,看他們挺感慨的樣子,我就坐下來,跟他們閑聊。據他們說,你老公何海,那天運氣很不好,“奸夫和淫婦”——對不起,是老頭兒們這么說的,你瞪我也沒用——在湖邊站著沒說上幾句話,“淫婦”的正夫就看見了。人家那正夫,那天偏不偏,就蹲在他們身后不遠的地方看別人釣魚。正看在興頭上,看見他們,想都沒想,低頭撈根棍子就沖上去了。可笑吧?更可笑的還在后邊。“淫婦”眼尖,一眼瞥見,啊一聲,沒等“奸夫”反應過來,好家伙,她先沖上去了,死命抱住正夫的腰,不讓往前走,一邊大聲喊著,讓“奸夫”快跑。“奸夫”嚇傻了,像被膠水粘在地上似的,一動不動。正夫怕他跑,甩“淫婦”又甩不開,讓她松手又不松,急得沒辦法,一咬牙,狠命拿棍子在“淫婦”腿上打。好在是根糟木頭,要不然,恁粗的棍子,她的腿怕得瘸上半年。棍子一下子就斷為幾截,眼看著“奸夫”反應過來了,要跑,正夫就地把棍子扔過去。不知道究竟打沒打著你家何海,據那些老頭們說壓根兒就沒挨上,反正是只見何海抱住頭,像個球,滴溜溜往地上一團,滾來滾去。正夫拖著“淫婦”奔過去,抬腿要踢。戲劇性的一幕再次出現,“淫婦”一看不好,英勇地返身一趴,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把“奸夫”覆蓋了個嚴嚴實實,正夫的拳腳每一下都中在她的身上。
于小鳳不說了,嘬著嘴兒笑。看她的樣子,顯然是沒說完。
然后呢?杜晶晶緊張萬分。
然后嘛,正夫一腳,于小鳳連說帶比劃,一腳把“奸夫淫婦”蹬湖里去了。聽老頭兒們形容,就像“沿著鍋邊把疊在一起的兩根面條下進鍋里一樣”。
呵呵,于小鳳再也忍不住了,捂嘴大笑起來。
從來從來,杜晶晶都沒像今天這樣,如此這般地討厭于小鳳。
看著杜晶晶鐵青的臉,于小鳳有所收斂,她擦著笑出的淚花說,也就是你,要是我,跟何海這樣的,我可過不下去。你為啥不離婚?
這個問題杜晶晶沒辦法回答,也不想回答。她想于小鳳真不是個好鳥,居然巴不得好朋友離婚。于小鳳的說法和何海說得大相徑庭,和她的直覺也有出入。看來那天何海的一系列表現不是“小題大做”,而是“無中生有”。如果真是“無中生有”的話,她可真是丟人丟到家了,怪不得那天上官絳珠的老公那副表情呢。他媽的。
信誰?
杜晶晶最后決定,信何海。他們兩口子之間,此時此刻絕對不能內斗,不能被外人趁虛而入。
接下來的日子,過得撲朔迷離,鬼影幢幢。
先是很快聽何海說上官絳珠離婚了,凈身出戶,搬回娘家住。杜晶晶覺得一股前所未有的壓力撲面而來。她掰開了跟何海講,主題只有一個,何海和她的婚,離不得。何海讓她放心,他說我沒那么傻,一次教訓足矣,我再也不會染指那個騷娘們兒啦。他說什么都過去了,老婆老婆你放心。

云朵、人體習作 李巖1997年 圓珠筆、紙 19.5m×13.5cm
杜晶晶能放心嗎?你想嘛,“農民”跟她的差距有多懸殊,她能深愛十幾年,義無反顧的性格可見一斑。雖然何海一再聲稱他絕不愛她,玩玩罷了,是她自己傻,入戲了,他立場堅定得很,絕不會假戲真做。但這不重要,有句俗話不是說嘛:不怕賊偷,就怕賊掂著。
她問何海要上官絳珠手機號碼,她要打電話罵她。何海略加思忖,就把號碼給了她,只是叮囑她:說話“抻活”些,別讓人抓住把柄。
接到她的電話,上官絳珠仿佛在意料之中,略一沉吟,就用標準的普通話向她問好。她的聲音蒼涼、衰老,聽起來,像五六十歲的老女人發出來的。杜晶晶簡直不能相信這樣的聲音出自一個三十三歲的小三兒之口。太意外了,她還以為能聽到像傳說中的狐貍精那樣騷嗒嗒的聲音呢,心里咯噔一愣。
兩個女人的談話很不順暢。
原因在杜晶晶身上。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杜晶晶竟也說起了普通話。她平時只說方言,偶爾說普通話,充滿醋溜味兒。電話那頭兒的上官絳珠對杜晶晶的醋溜普通話顯然很不適應,她輕輕地清了幾遍嗓子,暗示杜晶晶正常下來。無效后,她試著改用方言配合。就像杜晶晶說不了普通話一樣,她也說不了方言,結果也說得磕磕絆絆。意識到這一點后,上官絳珠輕輕嘆了口氣,無奈中改回她的普通話。而杜晶晶呢,固執地繼續著她的磕磕絆絆——對著電話那頭兒的小三兒。
形勢完全失控。不應該是這樣的。她打電話,本意是想給上官絳珠難看,讓她知難而退。這是客氣的。不客氣的呢,罵她,讓她滾遠。但她卻在上官絳珠蒼涼衰老的聲音下動了惻隱之心,她身不由己地被一種怪異的混合感情裹著往前走,她用磕磕絆絆的普通話指責、詛咒、命令、要求、請求、懇求,一直到哀求。電話那頭的上官絳珠不辯解,不發怒,偶爾輕輕地說一句“怎么會這樣呢?大姐,對不起。”
然后,忽然間,杜晶晶聽到她自己的哭聲。
她聽到她的哭聲很醋溜,就像她醋溜的普通話一樣。
嫂子,您保重,在她高低不平的哭聲里,上官絳珠禮貌地掛斷電話。
真丟人。
她是自取其辱。
晚上躺床上,杜晶晶病人似的,有氣無力地跟何海學說電話經過。何海好像早就預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抿嘴兒撲撲笑。他的鼻毛好久沒修剪過了,這么一笑,鼻毛聳出多長,看著可惡心。
知道厲害了吧?那破貨最擅長的,就是讓人對她我見猶憐。你那里是她的對手。
杜晶晶苦笑著承認,唉,是不行。
何海脫吧脫吧,脫成光身子,往她懷里拱。
杜晶晶厭惡地推開他。
他再拱,她再推。
他仰臉兒刁頑地看她。
看半天,再拱。
你小是吧?乏味不乏味?杜晶晶不想讓步,她已經傻了,不想傻到讓自己都覺得惡心的地步。
是小。姐,好好的,愛愛我。
何海確實比杜晶晶小。小半歲。
唉,我是上輩子欠你的,杜晶晶嘆口氣,把他摟進懷里。
日子好像恢復了以往的平靜。
上官絳珠離婚半年后,杜晶晶那個像陽光一樣的伯父去世了,她和何海住在伯父家幫忙料理后事。恰恰在那幾天的某一天,于小鳳告訴她,上官絳珠的前夫將再次走入婚姻殿堂。杜晶晶知道這一消息,先是心里一驚,然后是解恨。這下好了,犟豬,你就作吧,看以后誰還要你!
在那幾天里,杜晶晶意外地發現何海口袋里的錢挺多,陪奔喪的客人打麻將時,他居然敢上五十一百的場子。
自從知道上官絳珠的事后,杜晶晶在財政上迅速做出反應。男人沒錢,就是翻了蓋兒的王八。她對何海收緊銀根。何海為此沒少抗議。對不起,抗議無效。
那么,他的錢,從何處來?
她的直覺是:來自上官絳珠。
也就是說,他們根本沒斷,而是一直來往著。以某種秘密的方式。
喪期結束后,一回到家,杜晶晶就逼問何海錢的來處。見她一副你不說真話我就撒潑放野的架勢,何海沒敢說錢是從朋友處借的。杜晶晶手里拿著手機,隨時準備問過去,明顯表明防著他這招兒。看繞不過,他只得胡應付。
這就是承認了。
我就知道你們沒斷,你們到底想怎么樣啊,杜晶晶野貓子一樣躥到他身上,叉開五指,抓他的面皮。
他淡定地用胳膊一格,淡定地說,勸你好好的。
他且格且退,退到門內,大力推她出來,啪,反鎖上門。
有高人向杜晶晶指點:你笨。對何海這種情況,柔為上。
于是,就柔。
怎么柔呢?睡前,只洗一個蘋果,咔咔咬著吃,聽著都讓人饞。
何海伸脖兒瞅瞅,見沒他的份兒,欲惱,杜晶晶已將蘋果咬出一個圖釘形,笑意盈盈兒地遞他嘴邊,只消他咔嚓一口,毫不費力。
何海哎呀一聲,喜出望外。
他倒成功臣了!杜晶晶氣悶悶地想。真他媽亂了套了。
問題是,她做的所有的這一切,好像起不到預期的效果。
上官絳珠像霧一樣滲進來。杜晶晶把籬笆扎得再緊,都奈何不了霧的滲入。在吃飯的時候,在洗澡的時候,在睡覺的時候——有一次,她聽見何海在夢里喃喃叫著上官絳珠的名字。叫的是“珠珠”,親著呢。
那是一個什么樣的狐貍精啊,有恁大的魔力?
上官絳珠長什么樣子?杜晶晶問何海。
何海審視著她,看她并沒惡意,遂撅屁股趴床底下找出一雙棉鞋,抽出鞋墊兒,從里面拿出一個紙包,打開來,里面赫然是一張上官絳珠的照片。哦,好你個王八蛋,杜晶晶嘟嚕著,把照片接過去仔細看:的確不算太好看,中游略偏上。主要是身材出彩,還有就是氣質——朦朧記得聽人說過,女人只有一樣東西能和高貴的男人相匹配。不是她的美貌,也不是她的青春,而是氣質。長頭發,穿旗袍,扶樹站立,一臉的跟旗袍相沖突的冷傲和倔強。有點像電影里的軍統女特務。
看畢,杜晶晶癟癟嘴把照片丟還給他,表示一不咋地,二我大度,不制裁。
何海想了想,嘿嘿笑著,當著她的面把照片撕碎,扔進煙灰缸里。
算他聰明。
她并不為所動。心里想,哪天,趁你不在,我要把家里包括老鼠洞在內的所有的角角落落,來個徹底搜查。指不定能搜出什么好的來呢。
搜查的結果是沒再翻出照片,卻翻出一本日記。那本日記混跡于電腦桌下面厚厚幾沓書里,裝得像普通老百姓。其實這本日記早在多年前,杜晶晶就看見過。她偷偷地從這本日記里了解到何海的很多心事。比如他對她的評價:“一個賢淑的女人,一個把整個世界放到她手心里都可以放心的女人,一個可以終生相守的女人”,她清楚地記得當年看到這樣的評價時,她的感動和喜悅。沒人這么說過她。比如他說他是怎樣的憤世嫉俗,以至不被世人所容,被獸醫站頭兒暗算,等等。這些又勾起了她的痛惜的情緒。她能那么快地嫁給他,可以說這本日記功不可沒。結婚后,沒再見過何海寫日記。他把它當摘抄本用。有時是名人格言,有時候粘張剪報。這會子看見它,杜晶晶心里一動,順手拿起。
翻到后面,她看到上官絳珠的名字出現,大量的出現。
夸的,罵的,懷疑的,依賴的,愛的,恨的,什么都有,比他告訴她的那些豐富得多,可謂五味雜陳。他們經常見面。在超市,在書店,在路上,哪怕是驚鴻一瞥,也要見上一面。時常在杜晶晶家座機上響起的那一聲振鈴,也不是像何海說的是哪家小孩兒的惡作劇,而是他們在實在不能見面時相互約定的一聲“我想你!”。在日記夾層里,杜晶晶又發現一張手機卡。她把它安進她的手機里,調出通話記錄,上面全是上官絳珠的號碼。打過來的,打過去的。異常頻繁。無疑,他們平常就靠這張卡聯系。怪不得呢。多高的聰明才智啊。
在初秋依舊悶熱的房子里,杜晶晶感到脊背上一陣陣發瘆。
冬天說到就到了。
一天杜晶晶開著車,在縣街道正游蕩,看見前邊有個女人,披肩長發,穿著銀灰色大衣,一根腰帶恰到好處地勾勒出她的細腰。女人大踏步地走著。杜晶晶被她的背影所吸引,下意識地盯著看,心里暗笑:還說男人呢,其實女人也挺好色的。美的東西,誰都愿意欣賞。經過女人身邊時,杜晶晶忽然間有種不祥的預感,她覺得這個女人很可能就是上官絳珠。心馬上咚咚大跳。她感到口干舌燥。
透過后望鏡,她看得清楚,確實是上官絳珠那張冷傲倔強的臉。
一定是鬼附身。杜晶晶在一剎那間理解了劉邦的老婆呂后把劉邦的寵妃戚妃砍掉四肢、薰聾耳朵、弄瞎眼睛裝在壇子里置于廁所的心情了。因為是敵人。敵人就得剁成肉泥,就得除之而后快,甚至死后挫骨揚灰。她杜晶晶居然可憐她的情敵。上官絳珠可從來沒可憐過她。她想起她的屈辱。她憑什么屈辱呢?她住著自己掙來的五間兩層子的洋樓,開著自己掙來的私家車,穿著自己掙來的價格不菲的大衣……
哦,上官絳珠。
近在咫尺。
她飛快地將車開出百余米遠,戛然而止。打開車門,她站在車門邊,掏出手機,做出跟別人通話的姿勢,她開始了高聲大嗓的謾罵。從小三兒、狐貍精、騷貨、潘金蓮、淫婦、公共汽車到抽水馬桶。街上行人紛紛側目,有人指點,有人駐足。暫時無人圍觀。
都來圍觀啊,杜晶晶惡毒地祈盼。
上官絳珠聽到她賣菜大嫂式的叫罵,皺著眉看了她一眼,顯然是沒意識到這種謾罵跟她有關,她只是反感這樣的不文明行為。然后,她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接著,她全明白了——她并沒有像杜晶晶希望看到的那樣滿臉羞慚、落荒而逃,而是眉尖一揚,臉上彌漫開來憐憫的、輕蔑的、譏誚的笑意。
她目不斜視地從杜晶晶身邊掠過,帶起一股空谷幽蘭般的香氣。
杜晶晶張口結舌。
何海最近神態安詳,坐在電腦前寫小說的時間越來越長,看起來超然物外。仿佛,由他引起的兩個女人之間的戰爭,跟他毫無關系了似的。走進書房后,打開電腦,為圖坐著舒服,他把兩條后腿——看錯了,他一共只有兩條腿,沒前后之分——擎在電腦桌上夾住電腦,把鍵盤放在他的襠部。他左手摸在鹵牛肉上,時不時地往嘴里撕進一條,右手夾煙,時不時飛快地敲打鍵盤。
杜晶晶盯著他的后背琢磨他,越琢磨越覺得何海像只長滿了腿的、勝算在握的、盤踞在網中心的巨大的蜘蛛。
她想,除了上官絳珠,以后無論哪個女人要這個男人,我都雙手奉送,外加陪嫁——不,就是上官絳珠要,我也馬上給。背個輸名就背個輸名。我認了。這是他媽的什么鱉羔操的破玩意兒啊。
杜晶晶對何海的后背說,于小鳳曾經問過我,為什么不跟你離婚。
何海很警覺,馬上回頭,露出十分感興趣的樣子問她,她還說什么了?
你認為她還能說什么?杜晶晶緊盯著他的眼珠子問。
沒說什么,最好,何海陰森森地說完,扭過頭繼續敲他的字。
接下來的好長一段時間里,于小鳳沒跟杜晶晶聯系。奇怪。她以前隔三差五總要打個電話的。杜晶晶給她打過去,電話通著,那邊不接。有時干脆摁斷。路上偶遇,于小鳳一副活見鬼的樣子,一溜兒小跑,避著走。
肯定發生了什么事情。
杜晶晶到于小鳳家里找她。
于小鳳打開門,見是她,不好把她拒之門外,可也不想讓她進去。倚著門,愁苦著臉說,娘呀,你放過我吧。
杜晶晶估計得不錯,果然是何海找過于小鳳。
于小鳳說,那天,何海來了,問他不理,不用人讓,他直接進廚房開櫥柜找飯吃,弄得我們莫名其妙。吃完了他抹抹嘴,倒沙發上就睡。我老公肯定覺得不對么,這是尋事的架勢么,是耍死狗的架勢么,就問何海何海你咋了?咱有話好好說么。何海說,哥吔,好說不成,我都快沒家咧。兄弟可憐。你家小鳳挑撥我老婆跟我鬧離婚,那位現在正在家里殺雞抹脖子地鬧騰。兄弟以后沒家了,只好在你家吃,只好在你家睡。——你想想,這陣仗,我老公能不罵我嗎?罵了,何海還是不起來。我老公沒辦法,拉住我,扇了我一嘴巴。扇得不響,何海哼了一聲,還是躺著。我老公沒辦法,只好又扇了我一下。這下響,何海滿意了,這才晃晃悠悠走人。
于小鳳說得聲音哽咽,眼淚長淌。
杜晶晶氣得直往地上吐唾沫。
最近一段日子,何海露出狂躁不安的樣子,連鹵牛肉都不太吃了,煙頭兒扔得滿地都是。人漸漸消瘦下去,馬瘦毛長,胡子就長得分外旺勢,他不刮,弄得胡子與鼻毛共處。
杜晶晶冷著眼看,懶怠問。
不消問,“失戀了”唄,讓人家上官絳珠給踹了唄。
杜晶晶打疊起千百樣兒的軟語溫言,賭咒發誓再也不把于小鳳說的每一個字向何海透露之后,于小鳳相當不情愿地被杜晶晶拉進超市。杜晶晶請老朋友吃“焦太郎”下菜。
于小鳳當然明白她的意思,吃完后,抹抹嘴,主動把在坊間聽到的傳聞往外倒。她說,上官絳珠這次徹底跟何海斷絕了關系,據可靠人士說,就算“何海這次給人家跪下,人家上官絳珠也不可能跟他再好了”。
又說,蓮湖公園的事出來后,上官絳珠的老公確實覺得可丟人,但是,提出離婚的,不是他,是上官絳珠。上官絳珠的老公想不通,拖著不離。上官絳珠說,這么著過下去,對誰都不人道。非離不可。上官絳珠的老公很生氣,罵她說,何海那是個什么東西,那就是個地痞流氓無賴么,你居然當個寶。你跟誰都行,就是不能跟他。上官絳珠哭著說我全知道,我離婚不是因為他,我是因為我自己的心。我以后誰也不跟了,我就跟我的心過。上官絳珠離婚的時候,什么都不要,只要孩子。她老公是什么都可以給她,就是不給她孩子。她老公的說法很冷靜,很客觀:你的性子不適合帶孩子,把孩子交給你我不放心。
你的何海——見杜晶晶皺眉,于小鳳吐著舌頭改口道,何海在外邊到處跟人說上官絳珠的三圍多好多好,性需求多大多大,說上官絳珠無論以后嫁給誰,他都有本事給攪黃,還說上官絳珠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就算縣長對上官絳珠下手,他都要把縣長拉下馬。
他?杜晶晶眼睛瞇成一條縫,滿是鄙夷。她想像得來,要是上官絳珠真的跟哪個縣長好了,何海會如何做事。他確實有本事給攪黃。當然,他絕不會真槍實彈地上場。他會鬼鬼祟祟地踅摸到縣長跟前,掏心掏肺地說,那個女人么,我都看不上,扔了,您這大的人物,您撿我的狗剩兒?……那女人有性病呢,咋治都治不好,您防著些……那女人瘋狂得很,可怕得很,會攪得您家無寧日……
于小鳳嘆氣道,上官絳珠受不了何海的騷擾,把手機號兒換了。聽說何海沒轍了,就總往上官絳珠父母家座機上打電話,把人家老父老母嚇得惶惶不安。上官絳珠沒辦法,把座機號也換了。何海到處打聽人家的座機號,逢人就說,說是你在要,說你要找上官絳珠那個騷貨算總賬。
杜晶晶坐了起來。
——她確實那么干過。
那是在上官絳珠剛離婚那會兒,何海攛掇她給上官絳珠父母家打電話跟老人“溝通溝通”。溝通的主要內容是上官絳珠的離婚是她個人的決定,跟何海無關。杜晶晶當時雖然猶豫,覺得那么做對人家老父老母太缺德,但形勢嚴峻,何海在側又一直催逼,由不得她猶豫——于是就打了。
杜晶晶想,我得找到上官絳珠本人,好好坐下來聊聊。
沒等杜晶晶找上官絳珠,杜晶晶先收到了一封來自上官絳珠寄往她補課學校的手寫信。
正文如下:
請原諒我曾經帶給您的困擾。無論何海在我面前怎樣詆毀您,您在我心里都是一個不錯的女人。錯的不是您,是我。我承認曾對這個世界有過絕望,絕望使我憤怒,我只有通過墮落才能化解這份憤怒。在墮落的路上,我遇見了何海。不瞞您說,曾經有個時期,我對何海的感情很深。他苦難的人生經歷讓我下不了離開的決心。我視他為孩子,一個被世界無情拋棄苦苦掙扎的孩子。然而,何海只視我為敵人。何海似乎把一切人都視為敵人。他時時刻刻想著的,是克敵制勝的法寶。他對我全封閉式的控制,也讓我感到窒息。
您怎樣地不原諒我都行,怎樣找我算總賬都可以。老天推我了一把,我還過去了一把。結果呢,還過了。現在,我得承擔再被推一把的報應了。老天確實在以因果報應的形式維持著某種平衡。我的意思是,一切皆是我為,與我親人無關,與我朋友無關。要推,請您直接來推我好了。我認。還一分,了一分,我會平靜地接受。
請您轉告何海,他真的很聰明。如果他肯把全部精力用在正事上,而不是整天戰天斗地上,他也許會成功的。但是,像他那樣的男人,就算成功了,我擔心,他的成功果實,怕不會讓您和他來共享的吧?我想自然也不會是我。他對我和農民的事一直暴跳如雷——杜姐,我想我是幸運的,我可以轉身離開。可您呢?假如他成功了,沒您的什么,如果他不成功,他會寄居在您的體內吮吸您。日日、月月、年年,至死方休。
各人承擔各人的命運吧。
杜晶晶驅車來到郊外的一座橋上。她憋得慌,想散散心。
憑欄遠望。即使在汛期也不曾寬闊過的河面,在干燥的秋季,更加萎縮成窄窄的一溜兒。
她瞇縫著眼睛靜靜地站著,從中午一直站到夕陽西下。她想,我是不會離婚的。離了就不好玩兒了。那多沒意思啊。為了有意思,她必須得長長久久地跟他生活在一起。有句粗話說得真他媽好:屌毛比眉毛生得晚,但屌毛比眉毛生得長。她嫵媚地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