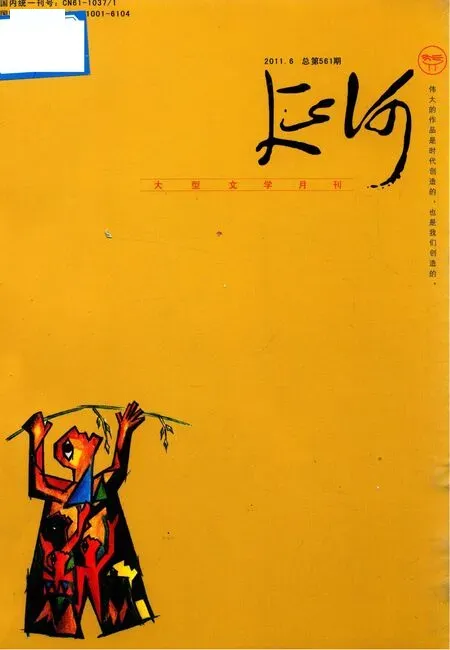和 解
孫曉杰
某夜
我在黎明未醒時醒來
我在黑暗中洗臉
我看不見自己的手,看不見
自己的臉,我摸索著
擰開水龍頭,也看不見水
只聽見小心翼翼的水聲
只摸到水:在黎明未醒時
被我弄醒的水
惺忪而口齒囁嚅的水
但我看不見水,水是黑的
我的手是黑的,臉也是黑的
在小心翼翼的水聲里,它們像
一場黑色的游戲
天色這時還沒有放亮,好像
我洗的不是自己的臉
而是臉上的夜色
三江源
這是三列火車的始發車站
一列黃河,裝滿了黃銅
一列長江,裝滿了玻璃
一列瀾滄江,也裝滿了玻璃
玻璃是生活用品,更多的是被
鑲嵌在窗戶上
我們可以從透綠的南方
看到黃銅閃耀的北方
大明宮遺址公園
我不寫大,只寫
一只小鳥,從離亂的柳霧燈塵
穿飛回來,身上有一片
唐朝的羽毛
也不寫明,只寫
夜色暗出城外,不及一樹李白
弦月倚在丹鳳樓上
不見一個豐腴的宮女
更不寫宮闕,只寫
一株野草驚夢于這奢侈的空曠
一塊拆遷留下的紅磚
深埋在地下

號啕與喜悅之三·悲憫與驚恐 李巖 1996年 鋼筆、紙 26cm×19cm
和解
一把刀常常跳起來咬破
我的手,這是容易的
源自它的鋒利我的粗心
但一個桌子的棱角一張睡床的底架
也常常像一輛黑車
撞傷我的腳趾和腿骨
但是為什么——
我阻止了我的慍怒
拒絕用報復的踢打證明自己
是一個強悍而軟弱的人
我常常用擦拭表達和解的意愿
你知道這些經歷過斧砍
鋸割的器物,在我死后還將活著
我不想讓它們忌恨我
詛咒我投下的身影
并且傷及我的孩子
一個人總要找到自救的辦法
我是一個膽怯的孩子。我需要
被肯定。如果我被推進
否定的沼澤,我會找到自救的辦法
我想得到陽光,我就說
陰暗的日子即將來臨
我想得到雪,雪的潔白,我就說
冬天的云,拋棄了我們
如果我恨,我就說愛。反之亦然
我像玩一場我并不想玩的游戲
一次次得到我要的結果
我遲早會被識破,從而得到錯誤的肯定
但在離開否定的沼澤之前
我仍須抓緊濕滑的樹根
我想奔跑,我就說:我想一個人
呆在這里。我想活,我就說
我今天必死無疑
捏泥人
我的孩子模仿上帝要用泥土捏
人
我為他取來浮土和雨水看他捏
什么
取來土豆和紅薯身邊的肥土和渠水看他捏
什么
取來鋼藍色鐵屑下面的油土看他捏
什么
取來養育花朵的泥土和泉水
(摻了幾粒蝴蝶翅膀上的香粉)看他捏
什么
取來含著石粉和細沙的泥土和雪水看他捏
什么
取來樹林里的腐殖土和松脂看他捏
什么
我拿來鐵鍬取出大地
沉埋的泥土和葉片上的露珠看他捏
什么
我甚至取來垃圾和污水但他要我
取來幼兒園
滑梯下的泥土和眼淚他要捏
什么
結束
我們降生或許只是為了逃避
從孕育開始我們躲進
水母般的子宮
我們一生像十根火柴
尋找帶磷片的盒子給家
鍍上宮殿的金箔
燈成為閃爍其辭的借口。因為躲避
風雨我們縮短了
陽光的時間
我們手扶靈柩在黃昏出現
為了安息眼淚
選擇了墓坑與墳塋
我們繼續逃避
但亡靈比我們前進了一步
用顱骨上的野花擎起一朵星光
在大雨里像一條沉睡的魚
在結束一切逃避之前
我們還無法擁有
更廣大的靈魂
夜話
來世。下輩子。一位無神論者
喃喃自語。假如。他內心
反對的聲音說。你是否與我
相愛。他懷里的聲音說
當然。他克服了一顆蟲牙
對一只蘋果的厭倦
下輩子。來世。他背叛了他的
內心,信仰
帶一把手槍上街
我帶著一把手槍上街
我是左撇子,我把手槍別在左腹部
我有隱私的亢奮和囂張的喜悅
脾臟如果善于言辭,這會兒肯定
全是硬話。我帶槍上街并不是
想殺人。身在持槍違法的國度
有一支不為人知的手槍,相當刺激
如見密友,街角處撩衣一現,嚇他一跳
如遇歹徒,拔槍,射擊
雖然違法,但可逃過死劫
鳥瞰
登上百層塔樓,鳥瞰——
積木般的樓群和未加掩飾的屋頂
道路如蛇,車如甲蟲,人如蟻
蔥蘢山丘如靜臥不動的綠毛烏龜
這些圖景,早就裝在
一只飛鳥的瞳孔里
鳥兒天天如此
登上紐約世貿大樓
留下驚鴻一瞥。現在雙子大樓
不復存在。曾經的俯望
宛若一只飛鳥在高空
突然斃命,墜落在地
再論游泳
一個詩人在他祖國的甜蜜河流
以自語的單調
游泳 他采用蛙泳姿勢
手掌合起又分開
一如祈禱
當沉重的太陽向西漂游
帶來 織物般的寂靜
他換成自由泳姿
雙臂交替拍打
閃電
閃電再一次降臨黃昏的大地
再一次激起河流的疑問
“誰熱愛并且保存了閃電?”
閃電照亮草叢里行進的游蛇
照亮青草——閃電
在它們身上找到自己的姿態
閃電再一次躍起!緊追一個人
這個人類的影子
只保存了閃電的速度
卻丟失了閃電的光芒
閃電攜著驚雷劈向一棵大樹
它愛那棵大樹只是因為
大樹下坐著一個人
他在等待迷失方向的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