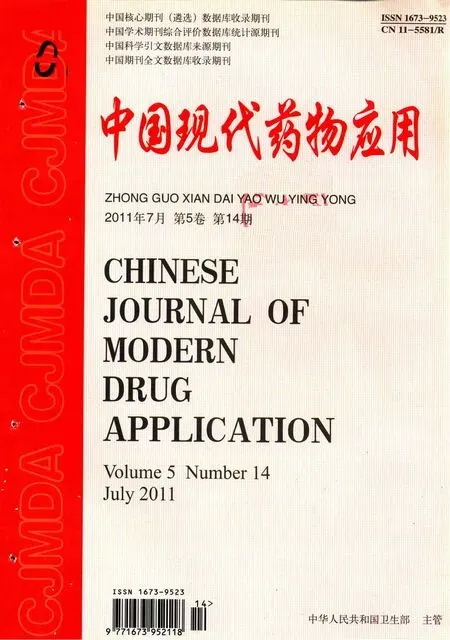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圍手術期麻醉處理
陳衛東
高血壓和冠心病圍手術期易發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或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因其手術死亡率較一般患者高,故應加強圍術期處理,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發生。本文總結170例合并心血管疾病圍手術期麻醉處理體會,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170例中,男99例,女61例,年齡42~80歲,平均60.7歲。其中合并高血壓病97例(I期20例,Ⅱ期59例,Ⅲ期18例),9例術前應用了抗高血壓藥至術前;心肌缺血63例,有心絞痛發作史32例,ECG表現心肌缺血50例,有心肌梗死病史1例。手術種類:擇期手術136例,包括食道癌、胃腸道腫瘤、膽囊切除、腎膀胱癌,子宮附件切除,宮頸癌等。急診手術34例,包括開放性骨折、胃穿孔、急性膽囊炎、急性腸梗阻、肝脾破裂及急性闌尾炎。
1.2 麻醉 高血壓患者47例術前積極治療,控制血壓至正常水平,心肌缺血經消心痛、硝酸甘油、阿斯匹林等藥物治療,ST段<0.05 mV 26例,ST段壓低程度有所好轉27例。心肌梗死患者6個月內不宜實施擇期手術。對急診血壓高于180/110 mm Hg如推遲手術給患者帶來的風險超過高血壓時,麻醉前用壓寧定或烏拉地爾速效降壓藥物,控制血壓在140/90 mm Hg左右為宜。術中持續監測心電圖、脈搏、血氧飽和度、血壓,部分患者監測CVP和尿量等。本組選擇硬膜外阻滯116例,全麻32例,硬膜外加全麻17例,神經阻滯5例。
2 結果
術前應用抗高血壓藥物者和未用藥者術中出現血壓劇烈波動的例數分別為9例(9/47,19.1%)和33例(33/50,66.0%),兩者相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前未進行治療,術中因血壓劇烈升高超過180/110 mm Hg,應用降壓藥39例次(每次烏拉地爾25~50 mg或壓寧定20~30 mg),26發生在麻醉誘導或蘇醒期,13例次發生在術中,因血壓過低,收縮壓低于80 mm Hg,或心率低于50次/min,用血管活性藥(每次麻黃堿10~15 mg或阿托品0.20~0.5 mg靜注)37次。并用降壓藥和升壓藥8例次。
3 討論
研究證明術前經過系統抗高血壓治療者,其術中血壓波動及心肌缺血的發生率明顯減低[1],本組術前應用抗高血壓藥者,術中發生血壓波動的次數明顯低于未用藥者。因此如果患者屬輕中度高血壓,服用降壓藥者應繼續服藥至術晨,以防心率、血壓的反跳升高。對嚴重的高血壓患者舒張壓高于110 mm Hg,應適當推遲手術,接受幾天或幾周抗高血壓治療,從而降低術中心肌缺血的發生率,本組急診手術,術前合并嚴重高血壓,經加深麻醉血壓仍未下降,應用壓寧定或烏拉地爾,效果確切安全,伴有明顯心率增快,可靜注艾斯洛爾10~30 mg/次。術前有過頻繁心絞痛發作的患者,應推遲手術,給予適當治療。
麻醉選擇原則要保持心肌供氧與需氧平衡和血流動力學平穩,既要減輕心肌抑制,又要使麻醉足以抑制手術操作的應激反應,避免心臟事件的發生[2]。對于下腹部及四肢、會陰部手術,采取硬膜外麻醉,術中注意防止麻醉平面過高引起低血壓和心動過緩;對于手術廣泛、創傷大采用全麻,對于上腹部大手術,采用硬膜外麻醉加全麻,一旦出現低血壓和心動過緩,用小劑量血管活性藥麻黃堿和阿托品處理,不要盲目快速輸血補液[3]。硬膜外麻醉可阻滯交感神經,改善冠狀循環,減低心臟的前后負荷,此項技術已應用于高血壓和冠心病治療[4]。全麻以其氧供充分,增加冠狀循環的攜氧能力,較適合于缺血性心臟病的患者手術。術前脫水和術中失血較多的患者,根據CVP指導補液、輸血。本組硬膜外麻醉引起術中血壓下降和心率減慢,給予麻黃堿和阿托品糾正后好轉,血壓劇烈波動者用多巴胺泵入維持循環穩定。全麻誘導和氣管插管是麻醉的關鍵,盡量避免使用興奮心血管的藥物氯胺酮和對心肌抑制較大的硫噴妥鈉和異丙酚,使用對心肌抑制較小的安定、芬太尼、依托咪酯。對圍手術期出現的嚴重高血壓首先選用起效快、作用時間短的新型降壓藥烏拉地爾和尼卡地平,可有效降壓而不發生低血壓。高血壓仍然難以控制可選擇血管擴張藥硝酸甘油或硝普鈉靜脈滴注,將血壓控制在合適水平。
[1]盛卓人.提高心血管病人圍手術期處理水平.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000,20(4):195.
[2]張麗華.圍手術期高血壓的認識與麻醉體會.寧學院學報(醫學版),2005,19(2):142-143.
[3]李雅蘭,彭雪梅,段善娥,等.合并心血管疾病的非心臟手術患者圍手術期處理.廣東醫學,2003,24(4):400-403.
[4]孟照杰.冠心病非心臟手術患者圍手術期風險評估預測和麻醉實施.醫學綜述,2006,12(7):413-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