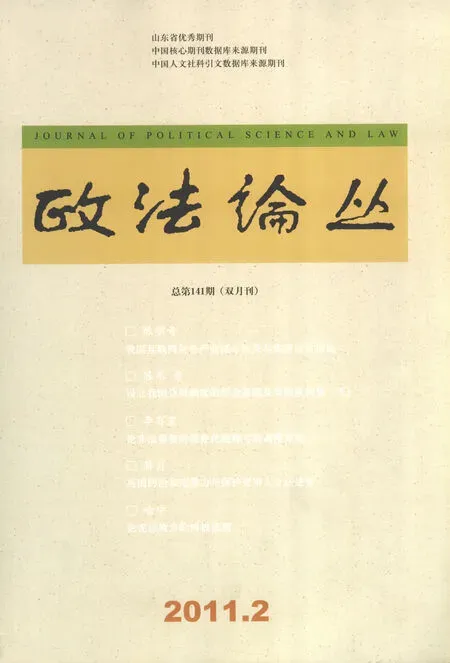論清末商法的實(shí)施及其效果
許世英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北京 100088)
論清末商法的實(shí)施及其效果
許世英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北京 100088)
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并不存在獨(dú)立的商法制度。制定私法性質(zhì)的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務(wù)之一。清末商法作為中國(guó)近代最早的商事立法,在近代法制史上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對(duì)清末商法的實(shí)施機(jī)構(gòu)、清政府對(duì)商法的貫徹施行、民間對(duì)商法的遵守等方面給予必要的研究。清末商法的制定與實(shí)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dòng)了清末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
清末 商事立法 法律實(shí)施 法律效果
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一直推行重農(nóng)抑商的政策,商業(yè)被當(dāng)作士農(nóng)工商之“末”,處于被忽視的地位。因此,在我國(guó)古代封建法制中,并不存在獨(dú)立或集中的商事法制度。刑民不分、諸法合體法制形態(tài)反映了我國(guó)封建社會(huì)長(zhǎng)期處于商品經(jīng)濟(jì)極度不發(fā)展的實(shí)際狀況。制定私法性質(zhì)的商法是晚清修律的重要任務(wù)之一。中國(guó)近現(xiàn)代意義上的商法起始于清末大規(guī)模的商事立法,期間完成了包括《欽定大清商律》(1903,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破產(chǎn)律》(1906)、《大清商律草案》(1908)、《改訂大清商律草案》以及《銀行通行則例》(1908)、《公司注冊(cè)試辦章程》(1906)等等一系列商事法規(guī)。清末商事立法,是中國(guó)近代商事立法的第一次實(shí)踐,是清末法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法律從形式、體例到內(nèi)容都具有創(chuàng)新性,符合中國(guó)法制近代化的需要。它完備了中國(guó)近代的法制體系,有助于中外法律文明的相互融匯。清末商事立法這段歷史不應(yīng)該被遺忘,雖然有著許多的缺憾,但留給后人大量商事法制實(shí)踐的珍貴遺產(chǎn)。這些立法成果是此后中國(guó)商事立法的基礎(chǔ),在中國(guó)商事法制近代化的歷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研究清末商法及其實(shí)施效果,有助于今天的商事法制建設(shè)。清末商事法規(guī)是法制的靜態(tài)形式,商事立法的具體運(yùn)作就是當(dāng)時(shí)法制的動(dòng)態(tài)形式。只有充分了解動(dòng)、靜兩種形態(tài)的商事立法,才能更好地了解商事立法的整體施行情況。
一、清末商法實(shí)施的機(jī)構(gòu)
關(guān)于商法的實(shí)施機(jī)構(gòu),近代各國(guó)其職能大多由法院承擔(dān)。中國(guó)古代民事法律不發(fā)達(dá),從來(lái)沒(méi)有專門(mén)的民事或商事審判機(jī)關(guān)。商法頒布后由什么機(jī)構(gòu)來(lái)實(shí)施,是清政府必須加以解決的問(wèn)題。從有關(guān)材料看,作為長(zhǎng)期實(shí)行的正式制度,清政府采取的是各國(guó)家通行的作法,以法院為商事審判機(jī)關(guān)。根據(jù)宣統(tǒng)元年12月(1910年1月)頒布的《法院編制法》及其附屬法,規(guī)定各級(jí)審判衙門(mén)中只實(shí)行民刑分理,將一般商事案件歸入民事訴訟。但商業(yè)登記應(yīng)采取什么制度,開(kāi)始時(shí)并不明確。《法院編制法》只規(guī)定審判衙門(mén)按照法令所定管轄登記及非訟事件,商業(yè)登記是否歸審判機(jī)關(guān)管轄,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后來(lái)法部會(huì)同農(nóng)工商部起草《商業(yè)登記章程》,才正式明確下來(lái),該章程草案第14條規(guī)定商業(yè)登記歸地方初級(jí)審判廳管轄,未設(shè)審判廳之處由地方行政官署管轄。①清政府設(shè)立和確定的商法實(shí)施機(jī)構(gòu)主要有:
(一) 商部
商部創(chuàng)設(shè)與商律編訂,是清末新政初期推行的兩項(xiàng)要政。商部是法制改革開(kāi)始后,清政府出于振興實(shí)業(yè)、挽回利權(quán)的需要,在決定制定商事法律的同時(shí),于光緒29年7月(1903年8月)設(shè)立的,是中國(guó)第一個(gè)近代工商管理機(jī)構(gòu)。商律最初是作為商部則例制定的。商部的設(shè)立突破了傳統(tǒng)中央六部行政體制,并引導(dǎo)了此后官制改革的全面展開(kāi),商律編訂則是修律的發(fā)端,表達(dá)了清政府引入新式法律振興商務(wù),挽回利權(quán)的最初嘗試。光緒29年3月(1903年4月)清廷在關(guān)于制訂商律、籌設(shè)商部的上諭中說(shuō):“茲著派載振、袁世凱、伍廷芳先訂商律,作為則例。俟商律編成奏定后,即行特簡(jiǎn)大員,開(kāi)辦商部。”②商律既為商部則例,當(dāng)然要為商部負(fù)責(zé)實(shí)施。光緒29年8月(1903年9月)商部奏準(zhǔn)的章程規(guī)定,該部會(huì)計(jì)司“專司稅務(wù)、銀行、貨幣、各業(yè)賽會(huì)、禁令、會(huì)審詞訟、考取律師……”。③光緒32年(1906年)商部改為農(nóng)工商部,該部在厘定執(zhí)掌事宜及員司各缺的奏摺中又重申:“商務(wù)司掌事物如左:……農(nóng)工商礦各公司暨一切提倡、保護(hù)、獎(jiǎng)勵(lì)、調(diào)查、報(bào)告、訴訟、禁令事宜……”④為實(shí)施《公司注冊(cè)試辦章程》,商部還于光緒30年設(shè)立了注冊(cè)局,主管公司注冊(cè)事宜。總之,有關(guān)公司成立和重大商案的處理,均由商部負(fù)責(zé),商法實(shí)施中遇到的問(wèn)題也主要由商部負(fù)責(zé)解釋。⑤
(二) 各地商會(huì)
商會(huì)本為商界自治團(tuán)體,歐洲中世紀(jì)就已出現(xiàn),主要為調(diào)整內(nèi)部關(guān)系,對(duì)抗外來(lái)競(jìng)爭(zhēng)而設(shè)。以后隨著各民族國(guó)家的形成和商事法律的發(fā)達(dá),商會(huì)的性質(zhì)逐漸發(fā)生變化。近代各國(guó)商會(huì)主要分為兩類,一是英美國(guó)家,實(shí)行私設(shè)組合制,視商會(huì)為民間自由組織;一是大陸法國(guó)家,實(shí)行私設(shè)官認(rèn)制度,將商會(huì)作為商政咨詢機(jī)關(guān)。中國(guó)商會(huì)的發(fā)展與歐美國(guó)家大致相同。清末商法頒布前,商界就有了一些商業(yè)公所或商務(wù)公會(huì)一類的組織,為民間私設(shè)。光緒29年11月(1903年12月)商部頒布了《商會(huì)簡(jiǎn)明章程》,確定了劃一之制。從該章程的規(guī)定看,清末商會(huì)采取大陸各國(guó)的制度,為民設(shè)官認(rèn)的政府咨詢機(jī)關(guān)。商會(huì)的職責(zé)之一就是協(xié)助政府實(shí)施商法。其章程第15款規(guī)定:“凡華商遇有糾葛,可赴商會(huì)告知總理定期邀集各董秉公理論,從眾公斷。如兩造尚不折服,準(zhǔn)其具稟地方官核辦”。第16款規(guī)定:“華洋商人遇有交涉齟齬,商會(huì)應(yīng)令兩造各舉公正一人秉公理處,即酌行剖斷。如未允洽,再由兩造公正人合舉眾望夙著者一人從中裁判。其有兩造情事商會(huì)未及周悉,業(yè)經(jīng)具控該地方官或該管領(lǐng)事者,即聽(tīng)兩造自便。設(shè)該地方官、領(lǐng)事等判斷未盡公允,仍準(zhǔn)被屈人告知商會(huì)代為申理,案情較重者由總理秉呈本部,當(dāng)會(huì)同外務(wù)部辦理。”第18款規(guī)定:“商會(huì)應(yīng)由各董事刊發(fā)傳單,按照本部嗣后奏定公司條例,令商家先辦注冊(cè)一項(xiàng),使就地各商家會(huì)內(nèi)可分門(mén)別類縮列成冊(cè),而后總協(xié)理與各會(huì)董隨時(shí)便于按籍考酌,施切實(shí)保護(hù)之方,力行整頓提倡之法……”。⑥
此外,商部《公司注冊(cè)試辦章程》還規(guī)定:“凡公司設(shè)立之處業(yè)經(jīng)舉行商會(huì)者,須先將注冊(cè)之呈,由商會(huì)總董蓋用圖記,呈寄到部,以憑核辦。其未經(jīng)設(shè)有商會(huì)之處,可暫由附近之商會(huì)或就地著名之商立公所加蓋圖記,呈部核辦”。⑦可見(jiàn),調(diào)解和處理商事糾紛,依法保護(hù)監(jiān)督各商,審核公司注冊(cè)呈式,為商會(huì)的重要職責(zé),商會(huì)是政府實(shí)施商法的輔助機(jī)關(guān)。
(三) 地方政府
中國(guó)古代社會(huì)行政、司法不分,向來(lái)以地方衙門(mén)為審理訟案的機(jī)關(guān)。至清末商法頒布時(shí),新的審判機(jī)關(guān)尚未建立,故仍沿舊制,凡商會(huì)調(diào)解無(wú)效或處理后當(dāng)事人不服之商事案件,由地方官處理,這從上引商會(huì)章程中已可以看出。另外,凡在商部札飭地方官加以保護(hù),地方官負(fù)有使各商免遭不法侵害之責(zé),此亦為貫徹商法中有關(guān)商人和公司權(quán)利的一種方式。
至宣統(tǒng)2年年底以前,清政府所頒布商法主要由以上機(jī)構(gòu)和組織負(fù)責(zé)實(shí)施。此外,還有一些政府機(jī)構(gòu)也間或參與這方面的,如郵傳部對(duì)涉及鐵路等交通公司的案件,鹽務(wù)部門(mén)對(duì)發(fā)生于鹽業(yè)的案件,都有辦理之責(zé)。因而這一時(shí)期商法實(shí)施機(jī)構(gòu)方面的情況是較為復(fù)雜的。到宣統(tǒng)2年年底,隨著各省省城和商埠各級(jí)審判廳的建立,商事審判開(kāi)始向?qū)徟袡C(jī)關(guān)轉(zhuǎn)移。據(jù)法部宣統(tǒng)3年3月(1911年4月)向朝廷呈奏的前一年下半期籌辦新政成績(jī)摺記載,到宣統(tǒng)2年年底,各地共設(shè)各級(jí)審判廳173所,設(shè)員2149人,除湖南、廣東兩省和吉林濱江、綏芬,黑龍江呼蘭府等商埠因故延期外,其余省城、商埠各級(jí)審判廳一律開(kāi)設(shè),受理民刑案件。⑧在此之前,憲政編查館在核定《法院編制法》的奏摺中曾規(guī)定,凡各地已設(shè)審判廳的地方,按照該法無(wú)審判權(quán)者概不得違法收受民刑訴訟案件。⑨宣統(tǒng)3年正月,農(nóng)工商部向法部提出,據(jù)山東勸業(yè)道電稱,山東省城、商埠各級(jí)審判廳均已按期設(shè)立,商事訴訟自應(yīng)一概歸審判廳辦理。其未設(shè)審判廳之各府州縣應(yīng)如何辦理,請(qǐng)法部批示。法部回復(fù):司法獨(dú)立,民刑分庭,其已設(shè)審判廳地方之商事訴訟,一概歸并審判廳審理;未設(shè)審判廳地方仍沿舊制,由府州縣衙門(mén)受理,但不服府州縣衙門(mén)裁決的上訴案件,可由以前的上訴至主管本省商政的勸業(yè)道,改為上訴于省城高等審判廳,以便既可使人民權(quán)利得到保護(hù),而司法、行政機(jī)關(guān)又不至混淆。⑩至此,由法院辦理商事審判,已作為一種新制度在部分地區(qū)付諸實(shí)施。
二、清政府對(duì)商法的貫徹施行情況
清政府對(duì)商法的貫徹施行主要表現(xiàn)在辦理公司注冊(cè)和對(duì)商事案件的處理上。
《欽定大清商律》和《公司注冊(cè)試辦章程》頒布后,先已設(shè)立的公司紛紛呈請(qǐng)注冊(cè),新設(shè)立的公司也陸續(xù)呈文到部,要求注冊(cè)給照開(kāi)辦。《商務(wù)官報(bào)》第五十一期載:“近日商部公司注冊(cè)局辦公頗形忙碌。因各處商家集股開(kāi)設(shè)公司局廠日多一日,并悉商部所辦各事皆系實(shí)心保護(hù),故均向注冊(cè)局呈請(qǐng)注冊(cè)。”公司注冊(cè)既是公司開(kāi)辦必須履行的手續(xù),也是商部貫徹實(shí)施商法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從《商務(wù)官報(bào)》和歷史檔案中保存的材料可以看出,商部辦理注冊(cè)時(shí),要依照商法進(jìn)行嚴(yán)格的審查,凡認(rèn)為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者,均予以駁回。根據(jù)《商務(wù)官報(bào)》第一期至戊申十期的記載統(tǒng)計(jì),光緒32年4月(1906年5月)至光緒34年4月(1908年5月)兩年間,因此而未準(zhǔn)注冊(cè)者達(dá)118起。
光緒34年4月以后的《商務(wù)官報(bào)》中,此類記載亦復(fù)不少。如宣統(tǒng)元年11月(1910年1月),批上海商務(wù)總會(huì):“職商韓棟林等創(chuàng)設(shè)協(xié)綸繅絲公司,合同內(nèi)稱韓棟林等各出資本洋一萬(wàn)元,共洋五萬(wàn)元,注冊(cè)呈式內(nèi)又稱每股銀數(shù)五百元,究系合資公司,抑系股分公司,飭詳細(xì)聲敘,補(bǔ)呈到部,再行核辦。”宣統(tǒng)2年正月(1910年2月)批鎮(zhèn)江商務(wù)分會(huì):“商人查濟(jì)鐄、查濟(jì)柄、查濟(jì)純等三人合資開(kāi)設(shè)查二妙堂友于氏友記墨號(hào),援合資有限公司之例,呈請(qǐng)注冊(cè)。查公司律第五條內(nèi)載,合資公司所辦各事,應(yīng)公舉出資者一人或二人經(jīng)理,以專責(zé)成。又第七條內(nèi)載,設(shè)立合資有限公司,集資各人應(yīng)立合同,聯(lián)名簽押,載明作何貿(mào)易,每人出資若干,某年某月某日起期限以幾年為度,報(bào)部注冊(cè)等語(yǔ)。本部詳閱該號(hào)原呈,所開(kāi)經(jīng)理人查益生,并非出資之人,於有限無(wú)限一款漏未填寫(xiě),合資合同亦未呈送到部。以上各節(jié)均與定章不符,合行批示該商會(huì)仰即飭該商等遵照定章抄錄合同另具呈式,公舉經(jīng)理人報(bào)部查核。”可見(jiàn),商部辦理公司注冊(cè)是較為嚴(yán)格的。
至于商事案件,由于材料有限,難以對(duì)有關(guān)情況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從目前所見(jiàn)材料看,一般情況下,清政府是按照所頒商律處理商事案件的。如宣統(tǒng)2年(1910年),發(fā)生了川漢鐵路公司虧短巨額款項(xiàng)的大案,該公司經(jīng)管滬款的職員施典章先后虧挪、侵蝕路款百余萬(wàn)元,因其經(jīng)營(yíng)不善,上海正元、謙余、兆康等錢(qián)莊和利華銀行還倒欠該公司路款二百余萬(wàn)元。案發(fā)后,四川京官鄧镕及資政院先后提出應(yīng)照公司律關(guān)於查帳人和公司清算的規(guī)定,公舉查帳人,會(huì)同部派監(jiān)察人員進(jìn)行徹底清算,并按商律第129條的規(guī)定,對(duì)有關(guān)人員進(jìn)行制裁。這些主張大都被主管該案的郵傳部所接受。宣統(tǒng)3年4月,郵傳部在經(jīng)過(guò)幾個(gè)月的清查后奏報(bào):“查商律一百二十九條內(nèi)載董事總辦或總司理人、司事人等,如有偷竊虧空公司款項(xiàng)或冒騙他人財(cái)物者,除追繳及充公外,依其事之輕重,監(jiān)禁少至一月,多至三年,并罰以少至一千元,多至一萬(wàn)元之?dāng)?shù)等語(yǔ),施典章除虧挪各款應(yīng)責(zé)令擔(dān)任歸還,暨正元、兆康之二十萬(wàn)兩歸其自理,業(yè)由江督等奏準(zhǔn)辦理外,其虛報(bào)股票價(jià)值、侵蝕公司銀十二萬(wàn)余兩,合依資政院議決辦法,照商律一并追繳充公,仍俟全案完結(jié),發(fā)交該管地方官監(jiān)禁三年,罰金即定為一萬(wàn)元,繳清后方得釋放。如蒙俞允,應(yīng)由臣部分咨江蘇督撫,臣轉(zhuǎn)飭江海關(guān)道仍提施典章到案,先行管押,勒限嚴(yán)追。”雖至清亡,此案尚未了結(jié),但從所奏處理意見(jiàn)看,基本是按商律的規(guī)定辦理的。再如,宣統(tǒng)元年9月(1909年10月),有人參奏上海交通銀行總辦李厚祐貪鄙成性,朝廷命郵傳部查處。尋奏:“李厚祐被參各節(jié),或傳聞未確,或查無(wú)實(shí)據(jù)……查商律規(guī)定,凡為公司理事人員,即不得更為同等之營(yíng)業(yè)。李厚祐既為華商銀行招股人,應(yīng)將所充之上海銀行總辦撤去,另派委員接辦,以專責(zé)成。從之。”
但也存在著相反的案例。如宣統(tǒng)2年,浙路公司總理湯壽潛因在雇用英工程師及領(lǐng)款等問(wèn)題上與郵傳部多次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被郵傳部奏準(zhǔn)革職。事情發(fā)生后,浙路公司援引《公司律》第77條關(guān)于公司總辦或總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選派,如有不勝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開(kāi)除的規(guī)定,認(rèn)為湯壽潛為商人公舉之總理,郵傳部不得撤銷(xiāo)。郵傳部援引過(guò)去奏準(zhǔn)之成案,強(qiáng)調(diào)鐵路公司與一般公司不同,應(yīng)受?chē)?guó)家特別監(jiān)督,政府有權(quán)任免總理。浙路公司不服,遂援引商部所擬《鐵路章程》第2條關(guān)于無(wú)論華洋官商開(kāi)辦鐵路一律遵行公司律不得有所違背的規(guī)定,據(jù)理力爭(zhēng),并將此事呈報(bào)資政院,請(qǐng)資政院議決。資政院認(rèn)為,“此項(xiàng)陳請(qǐng)系為尊重法律、保護(hù)商民權(quán)利起見(jiàn),實(shí)不僅為浙路公司而發(fā),郵傳部此奏實(shí)系以命令變更法律……。資政院有協(xié)贊立法之責(zé),見(jiàn)行政衙門(mén)有輕率變更法律情事,不能不起而維持。似此情形,自非請(qǐng)旨飭令郵傳部,凡關(guān)于鐵路公司事項(xiàng)仍按照公司律辦理,不足以維商業(yè)而安眾情”。遂議決上奏。在此期間,郵傳部盛宣懷等人又陳具說(shuō)帖,歷數(shù)以往奉旨撤銷(xiāo)鐵路公司總協(xié)理成案,與資政院辯駁。這場(chǎng)圍繞著浙路公司總理革職一事而展開(kāi)的關(guān)于行政命令與法律何者為先的辯論,最后以朝廷“著郵傳部仍照該部奏案辦理”的裁決而告結(jié)束。可見(jiàn)在鐵路公司問(wèn)題上,商法的有些規(guī)定并未真正得到實(shí)施。
三、民間對(duì)商法的遵守
從當(dāng)時(shí)各公司所訂章程看,許多公司和企業(yè)似乎都是按照商律辦理的。如煙臺(tái)張?jiān)a劸朴邢薰尽⑸剔k江西瓷業(yè)有限公司、中日商辦沈陽(yáng)馬車(chē)鐵道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同蒲路鐵路總局、保牛有限公司、商部奏定浙江鐵路公司、匯源銀行有限公司、直隸工藝局新興造紙有限公司、呢革公司、商部奏定新寧鐵路有限公司、山東諸城、莒州、日照三縣土產(chǎn)繭辮股份有限公司、徐屬宿遷縣龍井鎮(zhèn)永豐機(jī)器面粉公司、江西鐵路公司、商辦輪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川漢鐵路公司等15個(gè)公司的章程幾乎百分之百符合商律的規(guī)定。其中許多章程都明確規(guī)定悉依有關(guān)法律辦理。如匯源銀行有限公司章程第1條規(guī)定,本銀行一切均照有限公司定例辦理;中日商辦沈陽(yáng)馬車(chē)鐵道有限公司合同第2條、第14條規(guī)定,本公司應(yīng)恪守中國(guó)法律,此合同未訂明之處,均照商律及鐵道條規(guī)宗旨辦理;呢革公司章程第1條規(guī)定,本公司遵照商部有限公司章程辦理;江西鐵路公司章程規(guī)定,本公司悉照商部奏定有限公司章程辦理,以后如有意外虧折等事,悉由公司承擔(dān),不另派款于入股之人。
但考查其它材料,各公司店鋪在其實(shí)際活動(dòng)中未必都如章程或合同所云,按照商律辦理。光緒34年3月(1908年4月),給事中王金镕在一個(gè)奏章中就當(dāng)時(shí)普遍存在的奸商虛設(shè)公司、買(mǎi)空賣(mài)空現(xiàn)象寫(xiě)道:“病商之弊端不一,要莫甚于買(mǎi)空賣(mài)空。……此等情形,乃南北各省通病。”宣統(tǒng)2年12月(1911年1月),學(xué)部員外部袁榮叟在一個(gè)呈文中說(shuō):“實(shí)業(yè)公司多不按照公司律辦理,主辦工廠之人不識(shí)機(jī)器名類,不諳管理法制,甚至有行同倒騙者,有籍彩票為招股之具者,有但見(jiàn)工廠輪奐美觀而始終不聞開(kāi)工者。”另?yè)?jù)《大清宣統(tǒng)新法令》第八冊(cè)所收《農(nóng)工商部咨查各省興辦實(shí)業(yè)不得攙合外款》文記載:“振興各省實(shí)業(yè),……商埠公司各有專章,奏準(zhǔn)通行,各省均聲明中國(guó)自有權(quán)利,外人概不得干預(yù)。乃近日承辦各項(xiàng)事業(yè)之人,當(dāng)呈報(bào)開(kāi)辦時(shí),均注明不招外股,乃至催辦,或輾轉(zhuǎn)更易,籍口於資本不敷,股款未足,輒私行攙合外股,或借用外款,實(shí)屬顯違限章。年來(lái)由部查辦此等案件層出不窮,亟應(yīng)認(rèn)真整頓,以重實(shí)業(yè)而保利權(quán)。”此外,上海商務(wù)總會(huì)、預(yù)備立憲公會(huì)、上海商學(xué)公會(huì)等于宣統(tǒng)元年編成的《商法調(diào)查案理由書(shū)》也列舉了一些當(dāng)時(shí)商人不遵守商律的現(xiàn)象。該書(shū)第四章第六節(jié)寫(xiě)道:“公司律第一百七條有董事局結(jié)算公司帳目每年至少二次之語(yǔ),是以采用各國(guó)制度定有每年結(jié)帳二次以上之新制,最為文明之立法。而就社會(huì)上事實(shí)觀之,往往有等股份公司頻年不結(jié)帳目,造報(bào)分送,籍以取信於各股東。此則非但顯違公司律每年結(jié)帳二次以上之新制,并大背商業(yè)界每年結(jié)帳一次之舊習(xí),此急宜糾正,不容使之藐視公司律,致成為具文者也。”同章第八節(jié)寫(xiě)道:“我現(xiàn)行公司律雖不認(rèn)有優(yōu)先股,而實(shí)際上未始無(wú)其例,往往有於創(chuàng)辦之時(shí),即分普通股若干及優(yōu)先股若干者。”由于這些記述均為籠統(tǒng)之言,我們難以從中了解其詳情,但至少可以看出,所頒商法在商人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貫徹遵守。
四、對(duì)清末商法執(zhí)行效果的評(píng)價(jià)
清末商事法規(guī)是法制的靜態(tài)形式,商事立法的具體運(yùn)作就是當(dāng)時(shí)法制的動(dòng)態(tài)形式。只有充分了解動(dòng)、靜兩種形態(tài)的商事立法,才能更好地了解商事立法的整體施行情況。清政府頒布商事法以后,確實(shí)辦理了一些商務(wù)事宜,如依法進(jìn)行公司登記,1906年,根據(jù)《公司注冊(cè)試辦章程》頒布后的實(shí)際需要,商部下設(shè)注冊(cè)局,是專門(mén)負(fù)責(zé)公司注冊(cè)事務(wù)的機(jī)構(gòu)。
公司法頒布后,許多企業(yè)也樂(lè)意到商部進(jìn)行登記,辦理注冊(cè)手續(xù),探究個(gè)中原因,主要是為尋求政府的保護(hù)。誠(chéng)如時(shí)人論之:“然據(jù)理勢(shì)以度之,不過(guò)欲借農(nóng)工商部以為保護(hù)而已。蓋生機(jī)衰沉,產(chǎn)業(yè)停滯,經(jīng)營(yíng)實(shí)業(yè)者,岌岌不可終日,咸欲輕其負(fù)擔(dān),以防萬(wàn)一之變”,農(nóng)工商部基本上能夠依法辦理相關(guān)的注冊(cè)事務(wù)。據(jù)稱:“農(nóng)工商部注冊(cè)之例,凡經(jīng)注冊(cè)者,一依西法,無(wú)論中外公司,皆有受部保護(hù)之權(quán)利。凡公司法第九條與第二十九條,明定合資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私人商肆,一經(jīng)破產(chǎn),而無(wú)隱匿欺詐之行者,其償還債累,只以公司現(xiàn)有財(cái)產(chǎn)為限,不負(fù)財(cái)產(chǎn)以外之責(zé)任,又不許債戶追求社員股東。”這樣,公司登記之風(fēng)旋起,“自立部后至光緒三十四年末,凡五年間,報(bào)部注冊(cè)之公司凡二百六十五,其資本總額一萬(wàn)三千八百三十三萬(wàn)七千六百六十元,不可謂非一時(shí)之盛也。”公司只有經(jīng)過(guò)商部的登記手續(xù),才能名正言順地獲得法律的保護(hù),“若未經(jīng)注冊(cè)而破產(chǎn)者,悉以大清律例處辦,不僅負(fù)公司所有財(cái)產(chǎn)之責(zé)任,即一己之私財(cái),亦將查抄作抵,甚或累及父兄。”公司法已正式頒行,同時(shí)原來(lái)的大清律例仍然有效,“夫以新舊兩法論,今輕昔重,人所易知,今當(dāng)舉國(guó)窮困之時(shí),經(jīng)商者咸揣揣焉唯恐有變,故亟自注冊(cè),以備不虞,其情真可哀也”,卻反映出清末執(zhí)行商法時(shí)的極度混亂。
除按律辦理公司登記外,清政府也處理了一些商法案件。如1906年,官商合辦的廣東自來(lái)水公司設(shè)立時(shí),公司章程第10條稱“總副董事及董事并無(wú)任期,永不更換”,顯然有悖于商律第30條:“無(wú)論官辦、商辦合辦等各項(xiàng)公司及各局均應(yīng)一體遵守商部定例辦理。”商部認(rèn)為董事無(wú)任期是不符有關(guān)規(guī)定的,可以連選連任,但是不能“永不更換”。1907年,商部處理無(wú)錫業(yè)勤紗廠帳目的案件,也是按律辦案的有力佐證。該廠經(jīng)營(yíng)“不無(wú)成效,惟積習(xí)相仍,并未按商律辦事”,“經(jīng)理人帳目從未報(bào)告”,激起廣大股東的憤慨,要求商部主持公道。商部為維護(hù)法律尊嚴(yán),保護(hù)股東權(quán)益,責(zé)令業(yè)勤紗廠公布帳目,嚴(yán)格按照商律辦事。1908年,商部按照商標(biāo)法規(guī)定,嚴(yán)禁陜西義禮火柴廠冒用昌商標(biāo)。
但總體而言,商法的執(zhí)行很不理想,很多法律頒布之后,便被束之高閣。誠(chéng)如張謇所言:晚清商事法律“雖有法而不完不備,支配者及被支配者,皆等之于具文,前仆后繼,累累相望,而實(shí)業(yè)于是大隳”,對(duì)此,張謇痛稱:“如謇所親見(jiàn),且累見(jiàn)不一,并嘗身經(jīng)其苦痛也。”主持修律的伍廷芳也不得不承認(rèn)已經(jīng)訂定的新律,未見(jiàn)多大實(shí)效,雖然他“屢有條陳,輒思補(bǔ)救,奈終見(jiàn)阻,十不一行。”梁?jiǎn)⒊瑒t尖銳地指出:“中國(guó)法律,頒布自頒布,違反自違反,上下恬然,不以為怪”,繼而憤慨:“夫有法而不行,則等之于無(wú)法,今中國(guó)者,無(wú)法之國(guó)也。”商法的執(zhí)行自不免其外。法律制定出臺(tái)以后,執(zhí)法部門(mén)較為混亂,承襲原來(lái)落后的做法,法律賦予地方官員執(zhí)法權(quán)力,如破產(chǎn)律制定之初,便已確定了法成之后“仍責(zé)成地方官握行法之關(guān)鍵,而以商會(huì)副之”的方針。
一位美國(guó)學(xué)者認(rèn)為:在中國(guó),“法律只是國(guó)家的工具而已,而且法律和其他的強(qiáng)制性工具一起是由缺乏法律知識(shí)的官員去執(zhí)行的。”這位學(xué)者對(duì)近代中國(guó)法律在實(shí)際執(zhí)行過(guò)程中,客觀存在的有治法無(wú)治人的落后面貌的揭示無(wú)疑是切中要害的。《公司律》、《破產(chǎn)律》等單行法能否切實(shí)遵行令人堪憂,上海商務(wù)總會(huì)擔(dān)心:如果清政府繼續(xù)頹廢,不事振作,切實(shí)遵行商法,中國(guó)的商業(yè)將永遠(yuǎn)不可能與他國(guó)競(jìng)爭(zhēng),“政府一定公司律、再定破產(chǎn)律,雖奉文施行,而皆未有效力”。商事法規(guī)在清末并沒(méi)有得到嚴(yán)格遵行,對(duì)于實(shí)施商律的不力情形,鄭觀應(yīng)寫(xiě)有《商務(wù)嘆》以為披露:“商律頒行宜認(rèn)真,精其事者管商部”。后來(lái),清政府違背民意商情,實(shí)行鐵路的“干路國(guó)有”政策,對(duì)自己制訂的商律視而不見(jiàn),有如一紙空文,根本置商辦鐵路公司諸董事、股東的利益于不顧,任意踐踏商業(yè)法律的尊嚴(yán),損害商人利益,這種做法只能降低政府的威信,自食惡果。
晚清地方官還有公然違反《公司律》等法律規(guī)定,為解決財(cái)政危機(jī)而將利潤(rùn)豐厚的商辦礦業(yè)轉(zhuǎn)歸官辦的卑劣行徑,名義上標(biāo)榜獎(jiǎng)商、恤商,實(shí)際則壓榨工商業(yè)者。1905年,廣東曲江商辦煤礦“為官場(chǎng)查知該礦之暢旺,勒令交出,改歸官辦”,清政府獎(jiǎng)勵(lì)工商、鼓勵(lì)工商發(fā)展的法律法規(guī)很多流于形式,正如時(shí)人所言“名為保商是剝商”,當(dāng)遇上中西商務(wù)交涉的沖突和糾紛時(shí),商部作為主管商務(wù)訴訟的部門(mén),竟然也無(wú)力維護(hù)華商的合法權(quán)益而一味退讓。1904年,禮和、瑞記兩洋行勒索漢口華商,使華商損失高達(dá)銀十萬(wàn)兩。無(wú)奈之下,求助于商部,要求公允處理商務(wù)訴訟,給予正當(dāng)?shù)谋Wo(hù)。未料到反遭各級(jí)官吏調(diào)撥士兵加以彈壓,因?yàn)樯滩课值米镅笮姓腥歉嗟氖欠牵梢?jiàn)清政府的軟弱,這與當(dāng)時(shí)滿清政府的積貧積弱直接相關(guān)。“務(wù)期中外通行”的商律遇有此等案件,國(guó)人只有望“商律”而興嘆:“近日政府日言保護(hù)商人,振興商業(yè),而卒無(wú)明效大驗(yàn)之可指”。又曰“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華商被洋人欺凌,而商部諸公尚高枕不知也”。
我們知道,商事立法的前提是中國(guó)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然而在清末時(shí)的民族資本主義,其發(fā)展還處在初級(jí)階段。當(dāng)時(shí)所制定的商法,大多是直接從西方國(guó)家移植過(guò)來(lái)的,與中國(guó)人固有的觀念、習(xí)慣大相徑庭。雖然就這些法律、法規(guī)而言,它們是非常先進(jìn)的,但是實(shí)際情況是,由于這些法律、法規(guī)和大多數(shù)人沒(méi)有發(fā)生直接的聯(lián)系,使它們只能存在于少數(shù)先進(jìn)中國(guó)人的思想觀念里,而沒(méi)有發(fā)生法律、法規(guī)所應(yīng)起到的調(diào)整作用。如清末《破產(chǎn)律》頒布后不久,各地商會(huì)就以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商智未開(kāi),商業(yè)亦未齊同為由,要求暫緩實(shí)行。實(shí)際上《破產(chǎn)律》雖經(jīng)政府頒布施行,但在實(shí)際生活中,它卻是一紙空文。其它法律、法規(guī)也存在類似現(xiàn)象。商法內(nèi)容的超前性雖然與社會(huì)及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相脫節(jié),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法為教"的示范作用,啟迪了人們的民事法律意識(shí)、權(quán)利意識(shí),而且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社會(huì),人們確實(shí)很難看清楚究竟是法律脫離了實(shí)際還是實(shí)際滯后于潮流。總之,清末商事立法雖大多未在實(shí)際生活中施行,但它為后來(lái)商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礎(chǔ),如北洋政府、國(guó)民政府的商法就是在諸如《欽定大清商律》、《商人通例》、《公司律例》等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
五、結(jié)語(yǔ)
清末法制改革中,隨著各項(xiàng)新法的出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法律體系開(kāi)始走向解體,其中商法的產(chǎn)生具有重要意義。清末的商事法規(guī),除個(gè)別例外,在中國(guó)歷史上均屬首次制定頒行,因而具有開(kāi)創(chuàng)意義。如1898年《礦務(wù)鐵路簡(jiǎn)明章程》以及后來(lái)的《重訂鐵路簡(jiǎn)明章程》,其他法規(guī)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冊(cè)試辦章程》、《商標(biāo)注冊(cè)暫擬章程》、《破產(chǎn)律》、《試辦銀行章程》、《出洋賽會(huì)章程》、《劃一度量權(quán)衡制度及推行章程》以及各類經(jīng)濟(jì)法規(guī)、獎(jiǎng)商類法規(guī)等等,在中國(guó)法制史上均屬首創(chuàng)。清末的這些商事法規(guī),對(duì)中國(guó)商事法律制度建設(shè)起了明顯的奠基作用。
清末商事立法,發(fā)生在一個(gè)社會(huì)急劇變革與轉(zhuǎn)型的時(shí)代,有其特定的時(shí)代意義。考察清末商法及其實(shí)施情況,重要者在于借此來(lái)印照現(xiàn)實(shí),啟示未來(lái),這也是站在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角度考察商法之目的。盡管所處時(shí)代不同,商法移植與對(duì)本國(guó)商事習(xí)慣的尊重和繼承、商事習(xí)慣之于商事法律制度的地位、民商關(guān)系的處理等等,仍然是我們今天從事商事立法所不能回避的問(wèn)題。一個(gè)國(guó)家的法制建設(shè)與發(fā)展,無(wú)論怎樣借鑒與移植別國(guó)的法律制度,終究離不開(kāi)本國(guó)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離不開(kāi)本國(guó)的法制實(shí)踐。本國(guó)歷史上和現(xiàn)實(shí)中的法律制度、習(xí)慣、慣例乃至法律文化仍會(huì)自覺(jué)地發(fā)揮著作用。我們必須立足于本國(guó)法制實(shí)際,積極吸收、借鑒和移植外國(guó)的先進(jìn)的法律制度。商事法律制度的移植不像僅僅是引進(jìn)外國(guó)的資金、技術(shù)和設(shè)備那樣簡(jiǎn)單,任何法律或制度在一國(guó)的適用性和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種法律或制度的內(nèi)在精神、價(jià)值取向是否與該國(guó)的文化傳統(tǒng)、倫理思想淵源是否相吻合。所引進(jìn)的外國(guó)法律制度只有被本國(guó)民眾所認(rèn)可、接受、遵守,并且成為人們社會(hu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時(shí),即成為該國(guó)法律文化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時(shí),所移植和引進(jìn)的外國(guó)法就逐漸轉(zhuǎn)化成了本國(guó)的法律,或者說(shuō)被本國(guó)法所取代。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外國(guó)法律制度就會(huì)成為促進(jìn)本國(guó)社會(huì)不斷進(jìn)步的因素。總之,探討清末商事立法,就是為了對(duì)我國(guó)當(dāng)下的商事立法有所參考,在借鑒、移植外國(guó)商法制度時(shí)進(jìn)行合理取舍,確立正確的目標(biāo)。所以說(shuō),清末商事立法及其實(shí)施的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留給我們?cè)S多的思考,并且對(duì)于今天的法制建設(shè)和早日實(shí)現(xiàn)法治社會(huì),都有著深刻的借鑒和指導(dǎo)意義。
注釋:
① 該章程未見(jiàn)頒布。其草案保存在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法部檔,32174號(hào)。
② 《清德宗實(shí)錄》卷513。
③ 《大清光緒新法令·官制一》。
④ 商務(wù)官報(bào)[N]第二十九期。
⑤ 例如:《欽定大清商律》頒布后,南洋大臣魏光燾提出,該律關(guān)于外國(guó)資本入股中國(guó)公司,只規(guī)定即應(yīng)遵守公司章程和中國(guó)商律,對(duì)外資入股的范圍和所占份額未作明確限制,容易給外商蒙串造成可乘之機(jī)。為此,商部解釋:根據(jù)有關(guān)條約和鐵路、礦業(yè)章程的有關(guān)規(guī)定,外商只準(zhǔn)于通商口岸附股中國(guó)公司,且所入股額不得超過(guò)華股之?dāng)?shù)。參見(jiàn)《大清光緒新法令·實(shí)業(yè)》。
⑥ 《大清光緒新法令·實(shí)業(yè)》。
⑦ 《大清光緒新法令·實(shí)業(yè)》。
⑧ 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法部檔,32174號(hào)。
⑨ 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法部檔,32188號(hào)。
⑩ 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法部檔,32209號(hào)。
TheImplementationandEffectivenessofCommercialLawofLateQingDynasty
XuShi-ying
(Law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and Law, Beijing 100088)
The commercial legisl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was the first practice in commercial legislation in modern China , and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gal reform of late Qing Dynasty . This thesis was included the implementing agencies of commercial legislation, the attitude of Qing-Dynasty to the commercial legislati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orporation comply with commercial legisl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to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eommercial legisl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this thesis,the author also deeply discusse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ctual social role of the commercial legisl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 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his own view of constructing the legal culture in the areas such as transplant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late Qing Dynasty;commercial legislation;law enforcement;legal effect
DF08
A
(責(zé)任編輯:孫培福)
1002—6274(2011)02—123—07
許世英(1971-),男,山東聊城人,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法律史專業(y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yàn)橹袊?guó)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