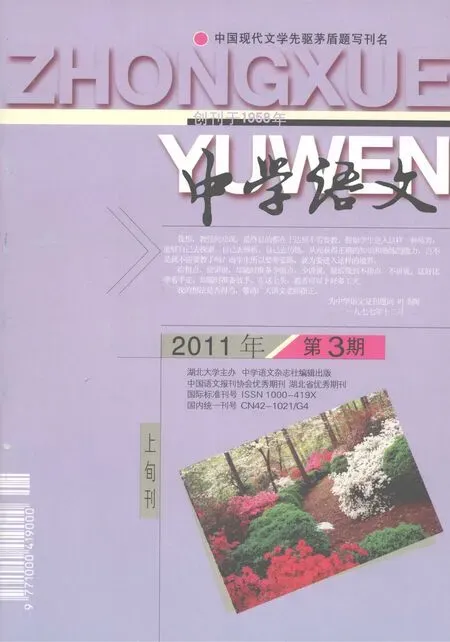觸景生情與景為情設(shè)
張至真
景和情是一對(duì)連體兄弟,無法分割。情景相生,景由情美,情由景出,美學(xué)家說,自然中的景,一經(jīng)人們的認(rèn)識(shí),就打上了情感的烙印,成了第二自然。王夫子《姜齋詩(shī)話》卷上云:“‘池塘生春草’,‘蝴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之相融浹,一出語(yǔ)時(shí),即得珠圓玉潤(rùn),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景相迎者也。”這“心中”的是“情”,“目中”的是“景”,“所懷”的情與“景相迎”,才是作者表達(dá)所在。文學(xué)上寫景即是為了表達(dá)心中之情,所以王國(guó)維說“一切景語(yǔ)皆情語(yǔ)也。”
常言道,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人們自可坦露心肺,盡情表述心中的愛與恨,但真正的高明者卻常常是“情至不堪處,付諸流水,以不盡而盡之,”將滿腔的情暗藏于眼前的景中,讓人感悟深思。因此嗥啕大哭者能示其悲;懷抱柳樹、黯然飲泣者也能慟其人。
劉熙載說“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文章是感情的傾訴,文學(xué)作品的審美教育功能,主要得益于作品能把作者心中的哀樂情感傳達(dá)出來,去感染讀者,影響讀者,產(chǎn)生共鳴,在與文本的對(duì)話中,激起內(nèi)心深處情感的浪花。直抒胸臆,衷情決堤,故動(dòng)人心魄;曲徑通幽,欲說還休,纏綿悱惻,亦情愫蘊(yùn)藉。觸景生情,如“楊柳岸曉風(fēng)殘?jiān)隆薄ⅰ半u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等,感人千古。現(xiàn)代作家史鐵生的《我與地壇》,那景,那情,那輪夕陽(yáng),那群雨燕,描繪的是自然之景,其中吞吐的不正是作者的款款深情?讓讀者去感知母愛的偉大、生命的可貴,從而提升自己的生命意識(shí)和責(zé)任感。
靜靜的小橋、幽幽的流水、春天飄落的絲絲斜雨,江南風(fēng)韻凸現(xiàn),何嘗不是歲月的流痕、飄逸的心靈感觸?“雪里紅梅半枝開”,“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又何嘗不是心中塊壘的渲泄?
這里所講的景物,不僅僅是第一自然,更是加上了人的意識(shí)的第二自然。《歌德談話錄》中說:“我深深了解,自然往往展示出一種可望而不可攀的魅力,但是我并不認(rèn)為自然的一切表現(xiàn)都是美的。自然的意圖固然總是好的,但是使自然能完全顯現(xiàn)出來的條件卻不盡是好的,”如橡樹,“它須和風(fēng)雨搏斗上萬年才能長(zhǎng)得健壯,在成年時(shí)它的姿勢(shì)就會(huì)令人驚贊了”。而藝術(shù)家能從更多的層面來處理自然的美景。“藝術(shù)家對(duì)于自然有著雙重關(guān)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隸。他是自然的奴隸,因?yàn)樗仨氂萌耸篱g的材料來進(jìn)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時(shí)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yàn)樗惯@種人世間的材料服從他的較高的意旨,并且為這較高的意旨服務(wù)。”
歌德是真正的藝術(shù)大師,更是文學(xué)大師,他用淺近的語(yǔ)言表述了藝術(shù)的真諦。同樣,現(xiàn)代畫家李可染先生在《漫談山水畫》中說:“山水畫不是地理自然環(huán)境的說明和解圖,不用說,它當(dāng)然要求包括自然地理的準(zhǔn)確性,但更重要的還是表現(xiàn)人對(duì)自然的思想感情,見景生情,景與情要結(jié)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科學(xué)的一面,畫花、畫鳥都會(huì)成為死的標(biāo)本,畫風(fēng)景也缺乏情趣,沒有畫意,自己就不曾成功,當(dāng)然感動(dòng)不了別人。”
真正的藝術(shù)家正是自覺地駕馭自然,齊白石倡導(dǎo)的“師法自然”即是此理,并且真正的藝術(shù)家還懂得驅(qū)遣自然為主題服務(wù),因情設(shè)景就是方法之一。
高中語(yǔ)文教材中選的《孔雀東南飛》和《藥》,都寫到了墳場(chǎng)的景象,但《孔雀東南飛》中的墳場(chǎng)并不能使人產(chǎn)生凄涼的情感,而《藥》中華大媽與夏四奶奶上墳的地方卻使人無限酸楚,倍感凄涼。筆者突出奇想,如果將兩文中的景象調(diào)換,會(huì)是怎樣的結(jié)果呢?讀者一定會(huì)說荒唐,但《藥》中的墳場(chǎng)就不能有松柏和鴛鴦,焦仲卿與劉蘭芝的墳場(chǎng)就不能有槐樹和烏鴉?但這樣安排的結(jié)果恰恰就出現(xiàn)了讀者審美中的逆轉(zhuǎn),情感表述中的滑稽。
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高明者無不根據(jù)情感的需要而創(chuàng)設(shè)相應(yīng)的景物。同樣,在朱自清《荷塘月色》中那筆下的荷塘,其中就沒有廢紙、垃圾、癩蛤蟆?但它們的出現(xiàn)就是敗筆。在茅盾的《風(fēng)景談》中那星星峽外的戈壁灘上難道就沒有一叢紅柳、一棵胡楊?有的只是“死一般的寂靜”?但文本中不能去表現(xiàn),即使有,都必須略去,只有這樣,才符合朱自清所表現(xiàn)的月下荷塘的清幽之美,才能讓茅盾在文本中為征服沙漠的 “人的偉大”而張本。作為藝術(shù)審美的對(duì)象,它必須表現(xiàn)出極致,才能更好地表情達(dá)意,為主題服務(wù),感染讀者,達(dá)到審美的娛悅。劉熙載在《藝概·詩(shī)概》中精辟地闡明了寫景為表情達(dá)意服務(wù)的內(nèi)涵:“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確是至理至性之言。
中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指導(dǎo)學(xué)生的鑒賞及寫作,也應(yīng)參透其道理,否則對(duì)自然的描述就會(huì)墜入自然主義的泥潭,而真情實(shí)感的表達(dá)也會(huì)有偏差。如學(xué)生作文描寫家鄉(xiāng)的美景,寫了寬暢的馬路,寫了新農(nóng)村的別墅,也寫了小河流水及青石板的小橋,構(gòu)建起江南水鄉(xiāng)的風(fēng)貌,但文中出現(xiàn)的橋邊的枯柳,橋腳下紅綠的塑料袋垃圾。確實(shí)這是他眼中的實(shí)景,如果放在另一場(chǎng)合,表現(xiàn)人們素質(zhì)的有待提高,表現(xiàn)和諧中的噪音,那是點(diǎn)睛的細(xì)節(jié),但放在歌頌家鄉(xiāng)美景的主題中就不和諧了,學(xué)生不知材料的取舍就破壞了文章的整體感。為什么不能寫寫那枯樹根上發(fā)出的新柳,橋腳下幾個(gè)懂事的孩子在撿拾五顏六色的塑料袋呢?在生活中這些現(xiàn)象都是客觀的、真實(shí)的。那才是高于生活的文學(xué)的真實(shí)。
魯迅先生在《藥》中為夏瑜墳上憑空加上去一個(gè)花環(huán),哪怕魯迅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的黑暗社會(huì)是“萬難破毀的鐵屋子”,但仍給作品涂上“若干亮色”,給后來者以希望。經(jīng)典作品的魅力就在此,而提升學(xué)生的鑒賞力、實(shí)踐性不正可資借鑒嗎?
無論觸景生情,還是因情設(shè)景,只要有自己的認(rèn)識(shí)就能尋找出其中的規(guī)律,從而指導(dǎo)自己的實(shí)踐和體驗(yàn),達(dá)到創(chuàng)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