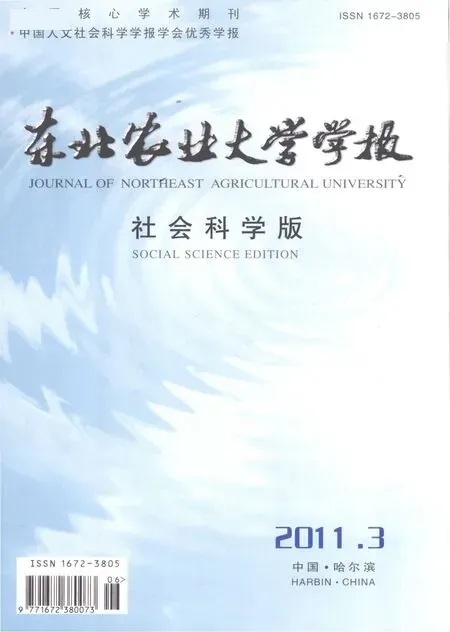孔子“禮制”與建設公共生活有序性的思考
喬 丹
(東北農業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150030)
孔子“禮制”與建設公共生活有序性的思考
喬 丹
(東北農業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150030)
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稱號,儒家禮學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近代以來,由于時代的變遷、戰爭的破壞、社會的動蕩以及價值觀念的混亂,沒有形成一套系統的為全民族共同遵守的禮儀規范。特別是在當下,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社會轉型期的種種矛盾日益凸顯出社會公共生活無序性的加劇。本文旨在運用發展的眼光,追根溯源,從中華民族之根——中華文化“孔禮”的角度出發,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為建立和諧社會公共生活新秩序作以實踐性思考。
孔子禮制;公共生活;有序性;和諧
翻開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史,我們可以看到先秦儒家管理思想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即高度重視從倫理道德層面論述管理問題。作為儒家鼻祖的孔子,強調用倫理道德來解釋社會公共生活管理過程中的一切現象、行為和關系,甚至通過一套倫理道德規范來構建社會管理秩序。以古鑒今,當前我國同樣處于社會轉型期,隨著新舊體制的更替,社會財富分配出現新變化,一些新的利益群體和階層開始采用變革的手段去打破傳統的社會管理體制,建立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新的社會管理體制,在社會轉型的陣痛期,人們的思想意識領域也出現動蕩和無序,甚至部分人道德淪喪,為所欲為,新舊秩序的交融和變革迫切需要新的社會公共秩序規約人們的行為,使社會公共生活保持在秩序和文明之中。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具有其傳承性。中國傳統社會是“禮治”社會,十分重視人們的德行修養和公共秩序,對各種人際關系都制定了詳細的規范,西周以來就享有“禮儀之邦”的美譽,從中國人的心理和思想實際出發,深入挖掘中國“禮制”思想的深刻內涵,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容,創新地為我國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構建新的社會公共生活新秩序煥發光彩,既有極強的可行性,且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現有社會公共秩序及其缺失的根源
公共生活有序性簡言之就是公共秩序,是指人們在工作、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為維護公共事業、集體利益和正常的社會公共生活所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是為了建立一種保障執行后對所有人都有益的秩序環境。實踐證明:人類文明越發達,人們對公共秩序的需要也就越多,期望值也就更高,可以說,公共秩序是現代社會文明的核心內容,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石。
目前,社會公共秩序狀況存在諸多不能令人滿意之處,究其根源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歷史根源。鴉片戰爭以來,中華兒女在救亡圖存、建設國家的過程中,也導致了經濟、政治、文化的嚴重失衡,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幾乎被完全割裂,人的價值觀被扭曲和片面化;五四運動徹底擯棄封建禮教,在推動社會巨變的同時也埋下了割裂近現代文明與古代文明聯系的隱患;建國后的“十年動亂”,是對整個社會文明的幾近毀滅式的摧殘——種種歷史原因造成人們的公共道德意識不足,缺乏公德心,長期生活在傳統社會中的人,道德標準總是表現為私人道德,置身于現代社會的公共環境中,往往會違反公共道德,破壞公共秩序。
其次,經濟根源。隨著工業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的不斷增加,致使有效資源過度稀缺,由于個人求生本能的驅使,導致了人們對他者的“無視”,公共道德的缺失,而且目前處于轉型期的市場經濟的私利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社會生活的無序性。
再次,文化根源。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缺點就是“講人情”,“不重規矩”,對于公共的東西,包括規則和秩序,很多人習慣于把它們當做是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一旦覺得對自己不便時,便首先考慮怎樣超越它,繞開它,使自己成為規則程序和秩序中的“例外”。部分人群的教育缺失導致人格缺陷、無視“秩序”的存在等等。
二、挖掘孔子“禮制”思想與促進社會公共生活有序性的契合點
“禮”在孔子思想體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追慕周公,主張捍衛傳統的禮樂文明。“在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中所發展的那些內容,不是與西周文化及其發展方向對抗、斷裂而產生的,在孔子與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氣質方面,與西周文化及其走向有著一脈相承的連接關系。可以說,西周禮樂文化是儒家產生的土壤,西周思想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觀、政治哲學、德性倫理的基礎。”在孔子看來,夏、商、周三代之禮一脈相承,而周禮集其大成,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西周以前的中國古代政治文化是一種帶有原始宗教性質的巫術文化,雖然禮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其主要是作為輔助宗教性政治活動的形式而存在。而正是到了西周,“的確是孔子所崇奉的周公將從遠古到殷周時的禮樂加以大規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為系統化的社會典章制度和行為規范,尤其是立嫡立長的繼統法在西周初期通過禮制而得以確立,促成了宗法、封建、等級三位一體的社會政治制度模式的建構,從根本意義上解決了政治運行的有序化問題。”這的確是一個創舉,孔子對周公及周禮的崇拜是隨處可見的,他一再強調自己“述而不作”吾從周”“夢見周公”。周禮的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有上下等級、長幼尊貴等明確而嚴格的秩序規定,在中國傳統等級社會當中,“禮”就維系了社會等級結構,促進了社會的整合。“事實上,周代的‘禮樂文化’的特色不在于周代是否有政治、職官、土地、經濟等制度,而在于周代是以禮儀即一套象征意義的行為及程序結構來規范、調整個人與他人、宗族、群體的關系,并由此使得交往關系‘文’化,和社會生活高度禮儀化。”面對禮制崩潰的混亂現實,孔子不但沒有棄置、批判禮樂傳統,反而堅信正是人們對禮樂傳統的棄置不顧或“禮”的空洞儀式化才導致了社會的失序,他不僅高度肯定和頌揚禮樂傳統,而且堅決地批判和憎惡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破壞禮樂秩序的行為。但孔子絕不是單純的復古者,而是根據時代的發展給“禮”注入了新的闡釋,從積極的意義上理解和把握禮樂的內在精神實質,以及它對于社會、政治和人生所可能具有的現實性價值,這才是孔子擇取傳統禮樂重建社會秩序的基本取向。
大多數孔子研究者都承認,孔子思想的主要范疇是“仁”而不是“禮”,相對于孔子是繼承周公而談“禮”,將“仁”作為思想系統的中心確實是孔子的獨創。前者是因循,后者則是創造。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孔子是為了要恢復、重建禮制而引入“仁”這一中心觀念的,在孔子看來,“禮”并不僅是對人的行為的各種規范和約束,“禮”中還飽含了人的情感、心理因素在其中。從孔子開始,儒家對“禮”有著獨到的思考和見解,“仁”因“禮”而設,無“仁”而談“禮”,“禮”就會變得空疏,變成一種外在束縛而讓人難以忍受。孔子對宰我問“三年之喪”的回答,就能代表他的此種看法。“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可以。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禮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開,鉆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制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在這里,孔子把“三年之喪”的傳統禮制,直接歸結為親子之愛的生活情理,把“禮”的基礎直接訴之于心理依靠。“三年之喪”的禮制在孔子看來是非常符合人情的,子女之所以為父母守喪三年并不是出于禮的外在強制性規定,而是出于子女對父母的真情流露,因而在守喪期間無心于世俗之樂,三年之喪確實是內心真實的悲痛,三年的期限之規定是對每個人的最初三年全靠父母的呵護才得以生存的一種回報,“三年之喪”是人的真性情、真情實感的一種表達和發揚。“這樣就把整套禮的血緣實質規定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親子之愛上,這就把‘禮’以及‘儀’從外在的規范約束解說成人心的內在要求,把原來的僵硬的強制規定,提升為生活的自覺理念,把一種宗教性神秘性的東西變而為人情日用之常,從而使倫理規范與心理欲求融為一體。”正因為禮制符合于人的真實性情,所以禮制之重建才有了最堅實可靠的基礎,禮并不是一種外在人的束縛,而是本乎人情的。孔子對那種只注重儀式而忽略禮之真實體驗的做法深表痛疾,“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在論及孝道時語重心長地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他在向樊遲解釋“孝”為“無違”時,進而將其規定為“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執禮之時,孔子則強調“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這些都突出了孔子論“禮”時更強調禮的內在情感因素,“禮”因情而生,“禮”之建制是充分考慮到了人之性情而并非僅僅通過外在的禮儀制度來規范人的行為。孔子援仁入禮,實際上對禮作了一個深刻的轉換:孔子認為行“禮”必須有內在的基礎,只有有了內在的基礎,行禮才能變成人們的自覺行動,這也是恢復禮制秩序的一個切實出發點。仁的修身也就是“克己”。當顏淵問仁于孔子時,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并進一步把“克己復禮”具體化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行。”這就是說,仁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時刻約束自己的欲望和行為,使之符合禮的規范,通過行禮的真實體驗而把禮內化為一種穩定的心理秩序。孔子援仁入禮,建立了仁禮相統一的倫理模式。禮制建設有了仁的真實情感體現而有了堅實的現實基礎,同時通過禮的踐行,人的真實體驗得到培養和發展。“仁”就屬于“禮”的日常應用之中,“禮”是“仁”的行動軌跡,而“仁”是“禮”的品德表現和真實內核,二者互為表里。
我們嘗試從管理層面去認識孔子所宣揚的“禮”,會發現“禮”是孔子從倫理道德角度闡釋其社會管理觀念的一種載體,今天,如何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進行思想創新,至少有兩個方面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和挖掘,那就是“秩序””和“和諧”,其不僅表現出“禮”的本質,而且也構成了孔子管理思想中最核心的內容。孔子把禮制思想與他的“仁義”思想互相滲透融合,形成了一種人倫觀與管理觀相結合的禮制思想,這一思想既順應了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組織結構,又符合把“家”作為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實體的價值觀。
“禮制”怎樣才能貫徹落實到具體的社會管理中,促進社會秩序良好運行呢?孔子提出了“修、齊、治、平”的實踐模式(《大學》),即一個人首先應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并運用修養成的倫理道德規范管好自己家庭的關系,然后,整肅好整個社會管理秩序,這時,“禮”就體現出倫理道德的社會規范功能。那么個人自身的倫理道德修養該怎樣進行呢?即最高境界“仁”,其基本原則是“愛人”(《論語》),并且要推己及人,這是一種同類相親、善意共存的意識,屬于一種普遍的以心理情感為基礎的人倫道德原則。“仁”是主觀方面的精神價值,“禮”是客觀方面的行為規范,由“仁”及“禮”,才能使“禮制”思想在具體的社會管理中得到貫徹落實,這就促使我們每個人在心中確立“仁”的價值坐標,強調個人的倫理道德精神與整肅井然的社會管理秩序的整合,以促進社會和諧局面的形成。
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歷久彌新,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深深地根植于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創造力和生命力之中,重新有效地汲取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重新煥發孔子“禮學”的光輝,這既符合中國人的心理認知又符合其長期以來的思維習慣,易于被人們所接受。
三、孔子“禮制”思想促進社會公共生活有序性的現實性思考
綜觀古今,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它既為現實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提供了終極的意義,更為社會生活提供了制度和秩序的安排。孔子“禮學”強調以“禮”治國,用禮法的謙讓精神來治理國家,促進國家安定,人民和諧,而達到至善,這一點同我們所說的“以德治國”相吻合,并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對于從國家制度、親族制度到復雜的人際關系網絡的構建,都具有重大的規范指導意義。
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闡發了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這反映了我們黨執政思維的日益成熟和執政能力的不斷提高。中共十七大再次強調“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2010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溫家寶總理的這個表述,已是第三次在公開場合使用,并記入政府工作報告。這一切都說明: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孔禮”大有可為,是時世所需,其當代價值主要體現在感化個體心靈、陶冶思想情操、協調人際關系、穩定社會秩序等等層面。
當下,隨著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社會階層的分化不斷加劇,階層對立、人際關系緊張的狀況也不斷加深,一部分人的地域歧視、學歷歧視、財富歧視等積重難返;另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報復心理愈燃愈熾;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心理畸形、人格分裂——凡此種種,都表明社會轉型時期風險的加劇,的確需要包括禮俗教育在內的各種手段綜合運用來調節各種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的穩定性,需要踐行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這里的“禮”明顯具有和諧、和睦之義,這是不同社會成員之間,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和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構筑和諧關系的基礎,是一種以“禮”為導向,以“和”為內涵的穩定管理秩序的社會機制,“禮”與“和”相互貫通,“禮”是構筑“和”的前提,“和”是實現“禮”的基礎,兩者內在統一,相輔相成。從這一點來看,一個缺乏和諧氛圍的社會是很難有秩序的,只有和諧才有利于社會秩序的長久穩定(在這里并不否定懲罰),并強調“君子和而不同”,是充分包容了差異性的“和”,即正確對待個體間、階層間和利益群體間的差異,協調、尊重和包容,這樣的社會充滿和諧,管理者仁愛民眾,被管理者和睦相處,人的尊嚴和價值才會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重視與肯定,這也是我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總之,當代中國社會公共秩序需要孔子“禮制”思想的重新建構,當代的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而這不僅需要依靠“法制”的強制作用,更需要發揮“禮制”的道德力量,對禮學有效繼承并創新發展,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促進社會公共生活的有序、和諧與健康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 王權.儒家禮學及其對中國社會秩序的影響[J].讀與寫,2008(5):5~9.
[2] 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三聯書店 ,1996:248~249.
[3] 趙明.先秦儒家政治哲學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114~115.
[4]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0~21.
[5] 黃森榮.孔子禮治思想新論[J].株洲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1):2.
[6]
On Confucius’Rules of Propr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Life Order
Qiao Dan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10)
China has been famous as a country of propriety,in which Confucianism’s ideas of etiquette play an important part.Etiquette is Chinese nation’s fine tradition.Since modern times,as a result of time vicissitude,war's destruction,society's turbulence as well as value confusion,there has been no set of etiquette standards observed by the entire nationality.Especially in the present age,with the fast improvement of social economy,social transformation increasingly highlights the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 disorder in public life.This paper aims to date back to the root of Chinese nations,Confucius’idea of etiquette,and endow with new connotation,so as to practically make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public life order.
Confucius’rules of propriety,public life,order,harmony
B222.2
A
1672-3805(2011)03-0100-04
2011-02-16
喬丹(1978-),女,黑龍江肇州人,東北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