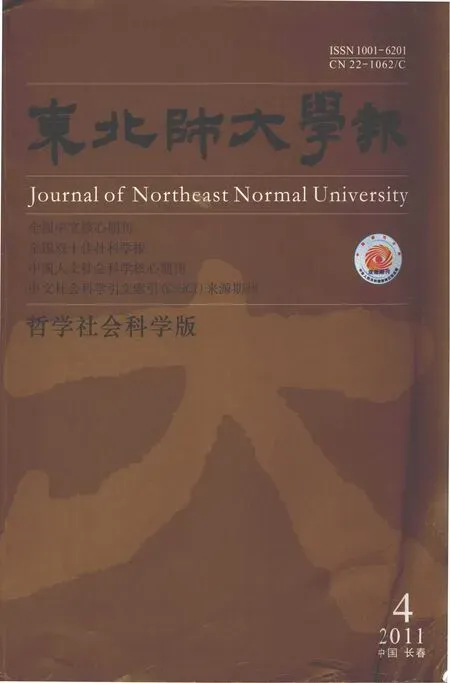現代性語境下跨文化作家超越創傷的書寫
周桂君
(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吉林長春130024)
現代性語境下跨文化作家超越創傷的書寫
周桂君
(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吉林長春130024)
與現代性語境相伴而來的是人的創傷感。遭受創傷,就必然要解釋創傷。文學作為審美的意識形態,在解釋創傷中獨具優勢。當今時代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個人有更多的機會生活在多元文化語境下。多元文化造就了跨文化作家,這個作家群體與現代性語境下的創傷感關系密切。跨文化作家的多元文化視角是在創傷體驗中形成的,他們身上都不同程度地體現著流亡情結,這也使跨文化作家獲得了世界眼光。
現代性;創傷;跨文化作家
一、現代性與文學中的創傷書寫
理解現代性(modernity)要從理解現代開始。歐洲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古代、中世紀、現代。廣義上,現代指中世紀以后,狹義上,現代指1870-1910年這段時間,甚至特指20世紀。廣義上的現代經歷的主要歷史事件有印刷術、清教徒革命、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1848年的革命運動、俄國革命、兩次世界大戰。現代性是人們從哲學高度抽象出的現代社會的本質,從思想觀念上把握到的現代社會的屬性。現代性為人們帶來了益處,但它也有陰暗面。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結果,如環境污染、人類精神與道德的危機等都是現代性批判的不可逃避的問題。
與現代性語境相伴而來的是人的創傷感。在現代環境下生存的人們面對的是一個飛速發展的世界,一個充滿危機的世界。人們不斷地遭受創傷,并在創傷中調解自己,以適應社會,獲得生存的空間。遭受創傷,就必然要解釋創傷。通過對創傷的反思,才能在創傷中進行自救,并在痛苦中走向成熟;創傷的文化意義在于“創傷已用來塑造個人和民族的經驗……神經科學可能會終有一天能夠弄清楚控制每一種創傷表現的過程,但是,即使到那個時候,我們依然需要衡量那些塑造我們的故事,因為創傷事件不是在真空里發生的。”[1]349這就是說,反思創傷不是神經科學的專利,因為創傷發生在社會中,受到各種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
文學在解釋創傷中獨具優勢。可以說,書寫創傷是文學永恒的主題,現代性又為作家提供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讓人們經受創傷的舞臺,文學便有了更大的空間來思考和書寫現代性語境下的創傷。創傷的經歷引起人們痛苦的體驗與情感,也引人思索。“悲愴藝術最能刺激病態情調和激情”[2]5孔子《論語·陽貨》中寫道:“《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怨”指的就是文學可以抒發痛苦的情感,表達痛苦的感受,從而成為藝術創作的源泉。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詩學》中提出卡塔西斯說。朱光潛先生認為,卡塔西斯指的是“宣泄”,就是說,藝術能使某些過于強烈的情緒因宣泄而達到平靜。羅念生先生則認為,它指的是“陶冶”,認為倫理德性要求適度,只有將過強或者過弱的情緒調解到適度,才能培養倫理品德。無論如何理解亞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說,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這個學說表明文學對人類情感的平衡有重要意義。
書寫創傷還能讓痛苦中的人看到希望。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故事——潘多拉的盒子,講的是主神宙斯因普羅米修斯盜了天火給人類,十分震怒,決定懲罰人類,派遣美麗女子潘多拉去完成這一使命。宙斯送給潘多拉一個盒子。當她打開盒蓋時,一股黑色煙霧從盒中飛出,彌漫了天空,黑霧中是嫉妒、奸淫、偷竊、貪婪等罪惡和病痛、瘋癲等災難,它們飛落在大地上。好在盒子最底下最美好的東西“希望”還沒來得及飛出盒子時,潘多拉就把它給關上了。潘多拉的盒子代表的是災難與邪惡。更重要的是盒子底下還有希望。正因為有希望——“災難的忠實的姊妹”(普希金:《致西伯利亞的囚徒》),人才能夠經歷創傷,走過痛苦,生存下去。如果說潘多拉的盒子象征的是痛苦人間的話,那么留在盒子底下的沒有飛出的“希望”就是人類在世上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而文學就是提醒人們希望的存在。
文學書寫創傷的另一個原因,是在創傷的述說中實現人的完整性。盧卡奇的藝術理論貫穿著這樣一種思想:藝術品是以人為中心的,要把人提升到完全的社會人格境界,實現人性的完整。劉建軍先生指出,傳統主體論有關“‘人是主體’的說法是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偽命題。因此我們要對‘人是主體’的理論進行重新闡釋。我們認為,人是主體,但同時要承認,人又是‘不完整的主體’。”[3]124劉先生進一步分析指出,“從人與對象的宏觀角度而言,在人類與外在世界的關系中,人類和對象世界都是不完整的主體。這是因為,人和對象之間,都是以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存在的。”[3]124
人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屬性,所以,“對象”指的主要是自然與他人。人與自然是一種互補的關系,人與人之間也是一種互補關系。劉建軍先生還指出,“在人與人的內部關系中,每個個體也都是不完整的。社會是由億萬個‘不完整的個體的人’組成的,這就決定著人與人之間也是互為對象的不完整主體關系。兩個或者兩個以上不完整的個體的人,在一定的關系中才能形成一個特定時期的‘人的主體’。個人意義上的‘個體’,階級或行業意義上的‘個體’都是不完整的,都是需要他者的。”[3]125
對自我利益的維護,或者說自私(這里的“自私”是哲學意義上的),是人的本性,人要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作為對象的他者也要維護自己的利益,所以人在補充自己的完整性時,必須在沖突、斗爭、調解中求實現。而在這個過程中,文學會發揮它特有的作用。文學作品一旦問世,它就走入了一個與讀者和世界的對話圈中。美國批評家艾布拉姆斯說過,“每一件藝術品總要涉及四個要素……第一個要素是作品,即藝術產品本身……第二個要素便是生產者,即藝術家。第三個要素……世界。最后一個要素是欣賞者,即聽眾、觀眾、讀者。”[4]4文學作品面世后,在艾布姆斯所說的四大文學要素的鏈條上運行,它影響人們思想的活動也就開始了。這樣,文學為人了解自己立了一面鏡子,也為人認識世界提供了參照。了解自己,也認識他人,就有助于人與自然、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系,在互補中實現人的完整性。
自然和社會是文學產生的母體。《文心雕龍:原道篇》有言:“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錦繡山河、日月變幻,這美景似乎是大自然信筆寫就的詩章,它啟迪著人的心靈。社會則為文學提供了另類豐富壯麗的圖景。《文心雕龍·時序》又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文學從來不是空中樓閣,即使是最遠離現實的文學也是社會意識的反映,因為逃避現實本身就是一種對待現實社會的態度。所以丹納堅信“文學也受到時代的影響。藝術作品必然與條件完全符合,任何時期的藝術都是按照這一規律產生的。”[2]2
作品的背景是作家生活背景的一部分,研究作者生平對創作的影響是一種傳統的文藝學的研究方法。雖然形形色色的文學理論讓這種研究方式顯得有些過時,但它是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的。方法是“主體與客體的中介,它一方面固然決定于客體,另一方面也聯系著主體。”[5]29-30只研究客體,而不研究主體的對作品的研究是偏面的。雷·韋勒克對社會學文學研究頗有微詞,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文學研究是脫離不了作家的社會學。
二、跨文化作家與多元文化視角
世界進入現代社會以來,全球化傾向越來越明顯。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推進,人們生活的空間更大,選擇的機會更多。人一生中可能會多次遷移,游走于各種文化之間。于是在文藝界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這就是跨文化作家群體的涌現。下面我們先從文化概念入手來解釋跨文化作家,并從跨文化作家的特點出發進一步探索跨文化作家與現代性語境下創傷書寫的關系。
文化的概念首先是在人類學領域發展起來的。文化被看做是一個民族的屬性。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文化,美國文化,是將文化的概念建立在民族和種族的基礎上。這種看似準確的分類,對具體的人而言其實是很含糊的。例如,兩個作家都是美國作家,一個是猶太裔美國人,一個是華裔美國人,如果將他們都歸屬于美國文化,那是不準確的,將事實簡化了,忽略了影響他們成長的異質文化因素。而如果按種族來劃分的話,則又忽略了他們接受美國文化的事實。這就是說,文化的分類只能以其主體成分作為依據,由此,有批評家主張文化所指稱的就是“主體文化”(subjective culture)
“‘主體文化’框架將個人看成文化群體得以存在的基礎。每個人都將過去的經驗擺到臺面上。這些過去經驗的基礎是社會化,以及那些被重要的他者,如合作者、同齡人、社會群體和家庭成員強化了的知識。通常,這些經驗或是含糊的,或是心照不宣的,它們影響著人們可能采用的觀點。當這些方面的共同點出現在集體中時,我們就稱之為文化。就是說,文化存在于人們的經驗與期待的橫切面上。”[6]13-14這也就意味著,“主體文化認為文化即是分享共同態度、價值觀及行為準則。”[6]14
作為了解文化的出發點,主體文化的概念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但是當今時代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人們有更多的機會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受多種文化熏染。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經歷的作家就是跨文化作家。
文化與人的關系是相互的。首先,文化是由人建構的,人們創造性地建構文化。因為“文化不是一輛已經載滿了一套歷史和文化商品的購物車。我們這樣構建文化:從過去的、現在的架子上選取物品……換言之,文化是變化的:他們被借用,混和,重新發現并重新詮釋。”[7]58反過來,文化塑造人的身份,人的身份來源有很多:信仰、健康、教育、生活體驗、民族、性別、家庭、性取向等等。人是在與他所從屬的文化的對話中不斷尋找自我,并漸漸確立起生活的位置的。跨文化作家被多元文化所塑造,同時,他們又以自己的藝術進一步塑造多元文化的時代品味。
跨文化作家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這個作家群體由于深受多種文化的影響而表現出自己的獨特之處。這些特點又與現代性語境下的創傷關系密切。
跨文化作家的多元文化視角是在創傷體驗中形成的。“多元文化視角的前提是認為文化是一個集體的社會性現象,由社會成員創造商定。其核心由認知因素組成,諸如基本的信念、假設或者指導群體成員思考、感覺和行動的文化知識。身體的表現,語言的、非語言的行為和象征性的事件,處在文化最明顯的層面,是文化網絡的一部分。”[8]40由于多元文化視角的前提是將文化認定為“一個集體的社會性的現象,由社會成員商定”,這就意味著主體文化的消解,或者叫去中心化,向外在的世界敞開。通過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生存,跨文化作家切身地體驗異質文化。“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跨文化作家好就好在此身不在廬山中,因為不在,而又熟悉,所以可以做到旁觀者清,準確地體驗世界與人生。
多元文化視角還意味著“一種共享的文化定勢可能出現。這樣,個人最有可能成為多元文化的攜帶者,因為他們在某一時刻屬于不同的文化群體。”[8]40這正是跨文化作家的情形。跨文化作家不僅僅是多元文化的攜帶者,更是多元文化的傳播者。正像上面所說的,文學作品一旦面世,就進入了與讀者和世界的對話圈中,多元文化就這樣進入了流通領域。當然,這里還要避免一種誤解,認為跨文化作家筆下寫的就是多元文化問題。跨文化作家筆下的作品直接涉及多元文化的并不多。文學是要寫人的,并不是文化的解說詞。多元文化更像空氣一樣浸透著作家的每一個細胞,像雨露一樣滋潤著作家的心靈。如果把作品比作花朵的話,當讀者看到那些美麗的花朵的時候,卻很少有人想到那催開花朵的雨——那雨露就是文化。
多元文化視角與主體文化視角是沖突的。雖然當今世界的人們對多元文化已并不陌生,但主體文化思想仍然是占主導地位的。獲得多元文化視角意味著跨文化作家是在經歷創傷的過程中培養起自己認識世界的態度的。
三、跨文化作家與創傷體驗
跨文化作家通常有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生活的經歷,這種生活經歷使他們在許多場合成了陌生人。如果他出生在異國或者在那里度過了童年,他是作為一個外來者,生活在異國的土地上,而當他回到自己的國家,在那里,他仍然感到自己是一個外來者,因為異國的生活已讓他與其所屬的那個國家的文化有了距離感。一般來說,跨文化作家往往具有流亡情結。“流亡的思想就是流亡的人,無家可歸的人,陌生人的想法與其‘所受的教育’。這是一種因為遠離‘家園’處在移位和不確定的情況下,處在一種不同的母語環境下,不同的語言傳統和文化中而產生的連根拔起來的想法。流亡的思想有自我強加的作為‘陌生人’的準則。這個‘陌生人’是作為一個客居國文化的‘陌生人’或移民,并從一個外來者的視角發展起他的身份意識的。”[9]593這個流亡者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建構他的身份,而這種對自我身份的建構會對他的思想產生深刻的影響。同時,在人格形成過程中,有跨文化經歷的人會更多地面對滄桑的世界,感受創傷的體驗。當賽珍珠(Pearl Buck)回到美國時,雖然她的外貌證明她是這個國家的一員,但在這個國家里,她感到陌生;而作為一個金發碧眼的外國人,在中國她仍然是陌生者——兩個國家的陌生者。
然而,流亡并不只給予跨文化作家以傷痛。“如果真正的放逐是一種永久損失的狀態,它為什么這樣容易就被轉化成一種潛在的、甚至是日益豐富的現代文化的動機?……現代西方文化多數是放逐的、遷移的。”[9]592賽珍珠通過對中美兩個國家文化的吸收、理解和傳播,終于在書寫中超越了文化的隔膜,將流亡中的創傷變成人生的財富。出生在非洲的萊辛(Do ris Lessing)在英國奮斗,印度的奈保爾(V.S.Naipaul)在西方世界打拼出一片天地,這些跨文化作家成功地走向世界的例子表明流亡并不是損失。這正是《孟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篇中所說:“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對于作家來說,流亡則更有價值。跨文化作家有機會接觸到現代性語境下的多重創傷體驗,這決定了他們作品的深刻性和現代意識。
跨文化作家從另類文化的角度觀察問題、思索問題。他既是某種文化的參加者,又是旁觀者,而同時,他又可充當文化的中介,將各種文化在作品中融會貫通來理解世界,這樣,跨文化作家的視角又具有世界性。這就是說,跨文化作家關心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都是針對全人類的,而不是將自己局限在某一主題或者某一思想上。僅以萊辛的為例,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萊辛的《金色筆記》的主人公是一個獨身女人,小說主要講述了她的生活經歷。這使得女權主義評論家們異常興奮,稱之為女權主義的宣言。富有反諷意味的是萊辛自己卻拒絕加入女權主義的陣營。“但是這本小說并不是婦女解放的號角。它描寫了許多女人的情感:挑釁性行為、敵對心理、不滿。小說將這些情感訴諸紙面而已。”[10]9萊辛的拒絕表明她不屑于任何主義的偏激與狹隘。萊辛是一位具有極其廣闊視野的作家。自1950年發表《野草在歌唱》(The Glass is Singing)以來,已寫了五十多本書,體裁廣泛,內容豐富,涉及殖民壓迫和種族問題、共產主義思潮、兩性關系、階級關系、女性解放、世界政治、人類歷史、自然災害、戰爭、原子彈、人類末日、太空時代、現代人心理和神秘主義體驗等等。
英國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 Woolf)曾為女性對世界體驗的局限性發表過自己的看法,她說:“對于《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維萊特》和《米德爾馬契》的作者來說,除了中產階級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廳外,其他生活領域的每一扇大門都是緊閉著的。她們不可能有戰爭經驗或者航海經驗,也不可能有政界經驗或者商界經驗。不僅如此,就連她們的個人感情生活,還要受到法律和習俗的重重限制。”[11]51伍爾夫看到了女性小說家的癥結所在,但是她自己也由于生活范圍的局限,無法走入廣闊的天地。“按照格式塔(gestalt)心理學的觀點,人們之所以有能力由一個形象辨認出其整體,就在于人們的頭腦中有對這一形象的整體的認知印象。”[12]伍爾夫沒有做到的,萊辛做到了。作為一個女性作家,她不為自己的性別所限,不為主體文化所束縛,而是站在廣闊的地平線上縱觀古今,思考全人類的問題。萊辛所思考的問題正是現代社會及未來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她要寫的是人,不只是女人,而是所有的人。她要寫的是人性和人所生活的世界。如果說跨文化視角是在創傷的體驗中形成的,那么,伴隨而來的世界性眼光則是痛苦結出的甜蜜的果實。
[1]Farrell,Kirby.Post-traumatic Culture[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2]H·丹納.藝術哲學[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劉建軍.人的本質和“不完整主體”理論及其應用[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
[4][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5]陳鳴樹.文藝學方法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6]Goto,Sharon G.and Chan,Darius K.-S.A re w e the same or are we different?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f culture[A].Cultures:Insights from Master Teachers[C].Edited by Nakiye Avdan Boyacigiller,Richard A lan Goodman,and Margaret E.Phillips.Routledge,2003.http://www.myilibrary.com.myaccess.library.utoronto.ca/brow se/open.asp?ID=7954Crossing.
[7]Ferman,Bernardo M.Learning about our and others'selves:M ultip le identities and their sources[A].Insights from M aster Teachers[C].Edited by Nakiye Avdan Boyacigiller,Richard A lan Goodman,and Margaret E.Phillips.Routledge,2003.http://www.myilibrary.com.myaccess.library.utoronto.ca/brow se/open.asp?ID=7954Crossing Cultures.
[8]Sackmann,Sonja A.and Philips,Margaret E.One's many cultures:A multip le cultures perspective[A].Insights from M aster Teachers[C].Edited by Nakiye Avdan Boyacigiller,Richard A lan Goodman,and Margaret E.Phillips.Routledge,2003.http://www.myilibrary.com.myaccess.library.utoronto.ca/brow se/open.asp?ID=7954Crossing Cultures.
[9]Peters,M ichael A.Wittgenstein as Exile: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J].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2008,40(5).
[10]Lessing,Doris.Preface.The Golden Notebook.London:M ichael,1972.
[11][英]弗吉尼亞·伍爾夫.女性與小說[A].伍爾夫讀書隨筆[C].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
[12]王萍,王冬梅.空靈意境的營造與動態結構的平衡——中西詩學話語中的空白觀對比研究[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116.
Traumatic W riting of the Cross-cultural W riters under the Con text of M odern ity
ZHOU Gui-jun
(School of Fo reign Languages,No 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What accompanies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is traumatic experience.Trauma experienced needs an interp retation.Literature,as an aesthetic ideology p lays a key role in the interp retation of trauma.And now we liv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in w hich an individual has mo re possibilities to live in a multip le cultures circumstances.M ultip le cultures cultivate cross-cultural w riters,w ho b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w n.That is,a close relation w ith trauma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For one aspect,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e is formed in traumatic experience of crosscultural w riters.The complex of an exile is show n in different degrees in the cross-culturalw riters.For another,traumatic experience benefits cross-cultural w riters too.That is,these w riters see the world as an organic w hole,w hich means,w hat they aremostly concerned about is the w hole human being and their existence.
Modernity;Trauma;Cross-cultural W riters
I106.4
A
1001-6201(2011)04-00111-05
2011-05-12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09YJA 752009)
周桂君(1965-),男,遼寧北票人,東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責任編輯:張樹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