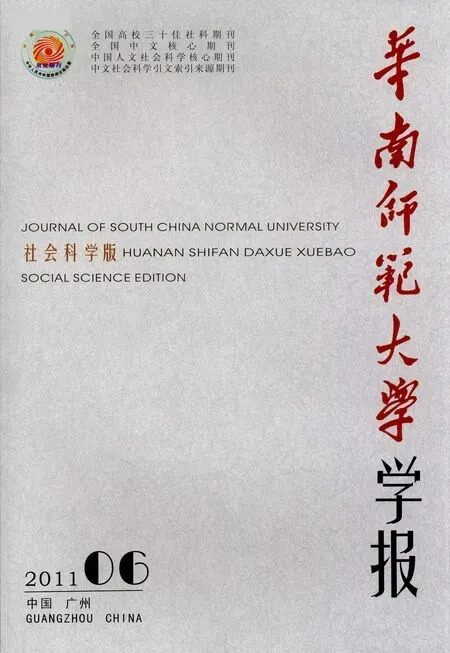《文選》賦與詩在唐宋時代的接受
汪 俊
(揚州大學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文選》賦與詩在唐宋時代的接受
汪 俊
(揚州大學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主要由于科舉的因素,唐宋人對《文選》賦與詩的接受各有側重。唐人對《文選》的接受與借鑒偏重于賦,而宋人則更偏重于詩。“選詩”自從被江西詩派正式引入詩壇后,影響漸趨深廣,在南宋后期在江湖詩派與理學詩派之外,實際上還存在著“宗選詩派”。
文選 賦 詩 接受
一
自昭明太子編《文選》出,歷一百多年至初盛唐時,曹憲、李善先后開講《文選》于江淮,“選學”之說遂興。唐代是“選學”大盛的時代。“文選學”一詞最早出自中唐元和間的劉肅,其《大唐新語》卷九《著述第十九》云:“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其后,《舊唐書·曹憲傳》、《新唐書·李邕傳》相繼提及,影響遂大。
“《文選》詩”指《文選》中所收之詩,又稱“《文選》體詩”。今通行本《文選》六十卷,收入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三十八類作品七百余篇,其中卷二十至卷三十一為詩歌,是《文選》中歷來最引人注目的部分。這些詩歌作品及后來的模仿之作,就被統(tǒng)稱為“《文選》體詩”,后來逕稱為“選體”或“選詩”。南宋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將“選體”與柏梁體、玉臺體、西昆體、香奩體、宮體并立,可見嚴羽認為“選體”詩篇雖然“時代不同,體制隨異”,但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
就文體而言,筆者以為,唐人對《文選》的接受主要興趣表現(xiàn)在賦,其次才是詩歌。其實,“文選學”在唐代就主要表現(xiàn)為三方面的內涵。
首先,是如曹憲、李善及五臣等為《文選》作注、就《文選》講學及由此引起的相關討論。在這方面,唐人的主要興趣和貢獻是針對《文選》所收作品進行注音、釋事、釋義和校勘等工作。所謂廣釋事類、搜討幽冥,為后世“《文選》學”奠定了基礎。這一點是最為人們所熟知的。
其次,是視《文選》為科考利器。《文選》一書與唐代科考的關聯(lián)甚深。唐代科舉以詩賦為主,然就重要性而言,賦乃在詩之前。今《文苑英華》尚保存大量唐代律賦,就是科舉試賦的產物;而科場試詩存留略少,亦可想見二者所受重視的程度是不同的。《新唐書·選舉志》載唐高宗因考功員外朗劉思立建言,下詔“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試策”;《唐大詔令集》卷一○六《條流明經進士詔》:“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后并令試策。……即為恒式。”末署“永隆二年八月”。據(jù)《唐摭言·試雜文》所載,可知此“雜文”是指賦。又徐松《登科記考》云武則天光宅二年(685)進士科下“是年雜文試題為《九河銘》、《高松賦》”可為旁證。要先過“雜文”一關然后才能進入下一步試策,自此以后科舉試詩賦成為定例。《唐代墓志匯編》開元三六三《大唐故亳州譙縣令梁府君之墓志》載梁玙“制試雜文《朝野多歡娛詩》、《君臣同德賦》及第”。據(jù)陳鐵民《梁玙墓志與唐進士科試雜文》,以為是武周垂拱二年(686)。總之,自初唐起,科舉試詩賦已成定例。而《文選》是進修詩賦的最好教材和范本,所以攻讀《文選》成為唐代士子的努力方向。唐人尤其重視《文選》賦,其創(chuàng)作多有融化前人之作者,如王勃《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翔丹,下臨無地”;即效王棲簡《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出云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效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杜甫的賦作名篇《雕賦》,亦被人們指為效袁淑《賀表驢山公九錫文》。但是,在這方面,當以李白為典型。雖然李白并不參加科考,但他的重視《文選》賦,正是唐代風氣之反映。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云:“白先后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此“詞選”即指《文選》。李白《擬別賦》亡佚,《擬恨賦》今存。王琦《李太白全集集注》卷一評曰:“太白此篇,段落句法,蓋全擬之,無少差異。”又《古賦辯體》卷七亦指出:“太白諸短賦,雕脂鏤冰,是江文通《別賦》等篇步驟。”
最后,是視《文選》為文學經典,不僅僅用于科考,而且作為一般文學創(chuàng)作范文和指導。在這方面唐人所重視的,是除了《文選》賦外,自然也包括《文選》詩,即所謂的“選詩”,但以前者為主。唐代視《文選》為文學經典尤其是詩歌經典的人較少,這要直到宋代才蔚為大觀。
北宋立國后,對《文選》的重視一如唐代。據(jù)范志新《〈文選〉版刻年表》統(tǒng)計,北宋刊刻《文選》共七次。北宋一百六十年左右,則平均二十多年就印一次,可見社會的需求程度之高。北宋太宗時命李昉等人效《文選》體例編《文苑英華》,所收作品上起梁末,下迄五代,其目的就是承續(xù)《文選》,成就新的一代文學總集。宋代雖然再無人如唐人那樣大規(guī)模地為《文選》作注(因為這屬原創(chuàng),無法重復),但對《文選》的研究卻比唐人更加熱鬧。這主要表現(xiàn)在文學理論和考據(jù)兩個方面。宋人重學問、勤思考,故對《文選》雖多贊譽,但也多有批評:或批評蕭統(tǒng)之選擇作品時去取不當,或批評五臣注之荒陋,或就李善和五臣的具體注文表達意見。這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當然是蘇軾。其他如呂南公、王得臣、葛勝仲、洪邁、王觀國、王楙等人,議論紛紛,間有考證,或是或非,由北宋而南宋,經久不息,頗為熱鬧。
對《文選》賦的重視程度,北宋初一如唐人,或更有過之。岡村繁云:“可以說北宋前期的八十多年間,大體繼承了隋唐以來的崇尚《文選》的傳統(tǒng),《文選》所代表的精巧麗雅之形式和風格一直被視為理想。”①岡村繁:《文選之研究》,第3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其實這主要體現(xiàn)在賦這種文體方面。宋初皇帝就對《文選》賦很感興趣。《宋史》卷二百九十六《呂文仲傳》載:
(宋太宗)嘗令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赍。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
《玉海》卷五九“淳化東西京賦”條記載:
淳化三年三月,賜楊億及第。億年十二,讀書秘閣。因擬《文選·兩京賦》作《東西京賦》以進,太宗嘉之,詔學士院試。
宋代科舉及第人數(shù)比唐代大增,且更重視詩賦,大大刺激了讀書人在這方面用功。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載: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歷后,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引《雪浪齋日記》云: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為《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zhàn)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
以上《老學庵筆記》與《雪浪齋日記》所載,應是各自對相同史實的分別記載,兩段文字可以參照領會。所謂“《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指《文選》為典故之淵海、語言之寶庫,熟讀《文選》即能掌握作文之技巧,即草稱王孫、梅稱驛使之類,此皆科場試賦試詩的看家本領。熟看《文選》,運用自如后,自然可以一逞以得志。
宋庠、宋祁兄弟就是熟讀《文選》科場得志的顯例。王得臣與二宋為同鄉(xiāng),其《麈史》記載,鄉(xiāng)里傳言宋祁出生時,其母夢朱衣人送來《文選》一部,故宋祁小字“選哥”,且宋祁曾對王得臣父親說:“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②(宋)王得塵:《麈史》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可見其用功之深。二宋兄弟年輕時熟讀《文選》、勤苦作賦,后來終于進士及第入朝為官,成為鄉(xiāng)里美談。得臣父就以二宋為例鼓勵王得臣攻讀《文選》,使幼小的王得臣痛苦不堪。凡此種種,正是宋初《文選》賦大行于世的真實寫照。
但很快情況就發(fā)生了變化。自慶歷間范仲淹的新政開始,到熙寧間王安石變法,《文選》的地位下降了。先有石介門人何群上書,請罷詩賦,且取平生所為賦八百余篇當街焚之,后有王安石新學起,改革科舉法。王應麟認為:“熙豐之后,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①(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熙寧元豐之后,王安石新學盛行,太學以王氏新學授徒,朝廷據(jù)以取士,在此大背景下,大致北宋中后期開始,“選學”走向衰微,《文選》賦因與科考絕緣也少人問津了。但幾乎同時,《文選》詩卻受到越來越多的人重視。而且隨著雕版印刷術的普及、印刷業(yè)的興盛,也為《文選》的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且南渡之后,科考制度又有所鼎革,南宋時《文選》幾成為一般士子案頭常備的讀本。“選詩”可謂南宋士子學詩寫詩的必修課程,于是在南宋就出現(xiàn)了《文選》詩的各種刻本。其類型主要有三:單行本、句圖、注本。《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總集類》載:
《選詩》七卷,《文選》中錄出別行,以人之時代為次。
又卷二十二《文史類》:
《選詩句圖》一卷,高似孫編。《直齋書錄解題》所載《選詩》七卷今雖不存,且我們并不知道編者為誰,但其刊刻印行卻很有意義。根據(jù)陳振孫的解題,有兩點我們應該給予特別的關注。首先,這是《文選》詩的首個單行本,所謂“錄出別行”,這很能說明問題。因為即便在唐代和北宋初《文選》賦大行于世時,也沒有出現(xiàn)過《文選》賦的單行本,可見南宋社會對《文選》詩的重視和需求程度之高。其次,《直齋書錄解題》將《選詩》作為詩總集著錄,且《選詩》對作品進行了重新編次,不再如《文選》以類編次,而是“以人之時代為次”,明顯體現(xiàn)出編者的歷史觀和詩史觀。后世研究“選詩”者多用這種編次方式,如清代吳淇著名的“選詩”研究著作《六朝選詩定論》就是“以人之時代為次”。所以今天看來,《選詩》七卷的首創(chuàng)之功的確意義重大。
《直齋書錄解題》將《選詩句圖》列入《文史類》,不甚可解。但好在此書今存,通行的有《叢書集成初編》本。這是《文選》中詩歌的佳句摘抄,屬于童蒙讀本,利于初學詩者參考模仿,亦可適應當時人們導讀之需。雖然編得較為粗疏簡單,但“其句下附錄之句,蓋即鐘嶸《詩品》源出于某某之意”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一《總集類存目·文選句圖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提示“選詩”與后世詩歌的某種淵源關系,為后世“選詩”研究作了初步的探索。
所謂注本,即南宋曾原一所撰《選詩衍義》四卷。曾原一乃南宋江湖詩派中人,曾與戴復古等結為江湖吟社,有《蒼山詩集》。《選詩衍義》似明代尚存,惜乎今佚。但元人楊士弘《唐音》引用了《選詩衍義》的三條較長的注文③見《唐音》卷一盧照鄰《送鄭司倉入蜀》注引、卷二“五言古詩”注引、卷二韋應物《擬古五首·有客天一方》詩注引。,我們據(jù)此可以推斷出《選詩衍義》的注本性質。另,據(jù)日本芳村弘道稱,他在韓國見到朝鮮活字本《選詩演義》。④[日]芳村弘道:《孤本朝鮮活字版〈選詩演義〉(撰者曾原一)》,見《古典文獻研究》,第12輯,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四庫全書存目》收此書,館臣提要認為《選詩衍義》對元代劉履《選詩補注》有一定影響,所言確實可信。此后,宋元之際方回撰《文選顏鮑謝詩評》,專評《文選》中所錄顏延之、鮑照、謝靈運等人之詩,下開“選詩”專家研究的先河。
二
人們一般認為,由于科舉政策的轉變,加上蘇軾對《文選》有所批評,致使“文選學”在北宋中后期漸趨衰落。其實,宋代科舉取消詩賦的時間很短,而且宋人對《文選》詩的熱情隨著時間的推移是逐漸升溫的,基本上是南宋甚于北宋,北宋后期甚于前期,降溫的是《文選》賦。而且,不管在蘇軾之前還是之后,宋人對《文選》都是重視的,并沒有出現(xiàn)大起大落的情況,宋人對《文選》并不排斥,只是他們的興趣已由賦轉而為詩。考宋人學詩軌跡,主要是學唐并在此基礎上有所創(chuàng)發(fā),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實際上,宋人在學唐詩的同時,也不排斥先唐詩歌。尤其北宋中后期以來,以蘇軾、王安石、黃庭堅等為代表的元祐詩家博學多聞,熱衷于以學問為詩,其詩材詩藝遠出唐人之外。如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評黃庭堅:“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雖含有偏見,但所述屬實。沈作哲《寓簡》卷八云:“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方回《桐江集》卷五《劉元暉詩評》云:“黃專用經史雅言、晉宋清談、《世說》中不緊要字融液為詩,而格極天下之高。”而考之《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等宋代主要公私書目,所錄先唐著述以經史類為多,集部則以總集為主,而別集尤少,故《文選》實為宋人學習漢晉南北朝詩之一最好津梁。就其實質而言,宋人著眼于《文選》一書,是將《文選》作為先唐文學史尤其是詩歌史對待的。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在《文選》賦漸趨衰微的宋代,為什么“選詩”可以獨盛一時了。
且相對于唐人而言,宋人所面對的文化遺產更多,可選擇的對象當然也更多。由于近體詩的成熟,宋人更多地從唐人那里汲取營養(yǎng)的做法,當然也是合乎情理的。《文選》只是宋人所面對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當然我們就沒有必要去要求宋人如唐人一般去對待《文選》。所以,在一般認為“選學”衰微于宋的同時,“選詩”則盛于宋,亦是歷史的必然。
后世詩家專意學習、模仿《文選》詩進行創(chuàng)作,以宋代士子最為用力。但其始,仍源于唐代,主要是四位大詩人:李白、杜甫、韓愈和柳宗元。宋人總結李、杜、韓、柳的詩歌創(chuàng)作經驗,有時也會將其歸結到“選詩”上去。如朱熹說:“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①(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四○,中華書局1994年版。又說:“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②(宋)朱熹:《晦庵集》卷八十四《跋病翁先生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人之重《文選》詩,尤以杜甫和韓愈為代表,而這兩位詩人又是宋人所著力學習的榜樣,所以杜、韓對待《文選》詩的態(tài)度給了宋人以強烈而持久的影響。杜甫《宗武生日》詩:“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又《水閣朝霽奉簡嚴云安》:“呼婢取酒壺,續(xù)兒誦《文選》。”儼然以《文選》作為兒子的詩學課本。故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云:
杜子美云:“課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
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郭思《瑤溪集》云:
子美教其子曰“熟茲《文選》理”,《文選》之尚,不愛奇乎。今人不為詩則已,茍為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采,萃而成編,則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wèi)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于詩學,世以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為獨步也。
宋何汶《竹莊詩話》卷七:
樊汝霖云:(韓愈)《秋懷詩》十一首,《文選》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文選》弗論也。而公詩如“自許連城價”、“傍砌看紅藥”、“眼穿長訝雙魚斷”之句,皆取諸《文選》,此詩亦往往有其體。
以上三段議論,與宋初人重視《文選》賦完全不同,而是著眼于“選詩”,指出熟讀《文選》對寫詩的好處,并推測李、杜、韓、柳皆因《文選》而導致詩歌成就。這就成了宋人的榜樣。在北宋后期,專意模仿《文選》詩進行創(chuàng)作的詩人亦可以推出四個大家: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相對而言,蘇軾、王安石集中用“選詩”體現(xiàn)出宋人“以學問為詩”之一端,這是蘇、王二人所喜歡表現(xiàn)的。蘇軾雖然批評蕭統(tǒng)和五臣,但對“選詩”本身實際上并無惡感。如沈與求《龜溪集》云 “(黃策)追和梁昭明所選詩,持見眉山蘇公,公期之曰:‘異時必以文顯’。”③(宋)沈與求:《龜溪集》卷十二《黃直閣墓志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蘇軾對浸潤“選詩”的文學后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黃庭堅、陳師道則不同,他們在這方面的作為就如同唐代的杜甫和韓愈。在宋人所作《山谷詩注》、《后山詩注》中,任淵、史容輩指出山谷、后山詩出“選詩”、用“選詩”、似“選詩”者比比皆是。大抵化用“選詩”語言并略作變化者為最常見,其次為取“選詩”之意,再次取“選詩”之法。如此動作,均合于江西詩派“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無一字無來處”之作詩三原則。以此看來,宋人專意模仿《文選》詩進行創(chuàng)作,在南北宋之際就已然生根發(fā)芽了,而其功臣乃江西派詩人。
黃、陳之后,“選詩”的另一功臣是徐俯。曾季貍《艇齋詩話》云:
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
東湖嘗與予言:“近世人學詩,止于蘇黃,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窺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小車無。”東湖嘗書此以遺予,且多勸讀“選詩”。近世論詩,未有令人學“選詩”,惟東湖獨然,此所以高妙。
山谷論詩多取《楚詞》,東湖論詩多取《選》詩。
東湖送謝無逸二詩,全似“選詩”,今集中無之。
東湖“呂侯離筵一何綺”,“一何綺”三字出“選詩”。有“高談一何綺”,又“高文一何綺”。
方回《瀛奎律髓》稱:“裘甫(按:曾季貍字)詩話多諛師川。”①(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三方惟深《和周楚望紅梅用韻》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曾季貍少從呂本中、徐師川游,故《艇齋詩話》多有關于呂、徐二人的說詩言論。就“選詩”而言,亦載呂本中“東萊送珪公果公入閩中詩五言‘宿昔春水生’者,絕似‘選詩’。東萊自云。”而呂本中《呂氏童蒙訓》亦云:
徐師川言: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亦引曾幾云:“蓋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②(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第50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所謂“有六朝風致”、“專師陶淵明”,即同曾季貍所言,以“選詩”為老杜、蘇、黃之外的又一學習對象。徐俯確是南宋初大力提倡“選詩”之第一人。
宋代是詩歌流派自覺的時期,各派相爭不讓、黨同伐異比較厲害。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自從“選詩”由江西詩派正式引入詩壇后,被南宋的主要詩歌流派所接受。江湖派如方岳、劉克莊乃至文天祥,理學詩派如朱熹,均有關于“選詩”的正面言論記載。而南宋后期詩壇,一般認為主要有江湖詩派與理學詩派,但學江西詩者往往也學“選詩”,如余杭二趙(趙汝讜、趙汝談)和上饒二泉(趙蕃、韓淲),在江湖詩派盛行的背景下依舊寫江西詩,不過若寫古體詩,則效“選詩”。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云:“蹈中詩,至中年不為律詩體,獨喜為《選》體,有三謝、韋、柳之風。”劉克莊《宋希仁詩》說:“近世詩學有二:嗜古者宗《選》,縛律者宗唐。”③(宋)劉克莊:《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張氏愛日精廬本。方岳《跋徐衡伯詩》也認為南宋詩壇有宗《選》與宗唐兩派:“高者曰‘選詩吾師也’,下者曰‘唐詩吾師也’。學唐學選者幾何人矣,不能唐不能選不論也。”④(宋)方岳:《秋崖集》卷三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江湖詩人趙汝回云:“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⑤(宋)陳起:《江湖小集》卷五十五,薛嵎《云泉詩》趙汝回序。這或許可以給我們以新的啟示,從另一個角度去觀照整個南宋詩歌發(fā)展脈絡。
The Acceptance of the Fugues and Poems in“Literary Selections”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by WANG Jun)
Mainly due to the factor of imperial examination,peopl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d different emphases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fugues and poems in ”Literary Selections”.People of Tang Dynasty attened more on fugues while people of Song Dynasty attended more on poems.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selected poems by School of Jiangxi,the impact was becoming deeper and greater.In fact there was“a school of literary selections”in addition to“the school of rivers and lakes”and the“school of science”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terary selections;fugues;poems;acceptance
汪 俊(1957—),男,江蘇揚州人,文學博士,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2011-10-16
I222.4
A
1000-5455(2011)06-0039-05
【責任編輯:趙小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