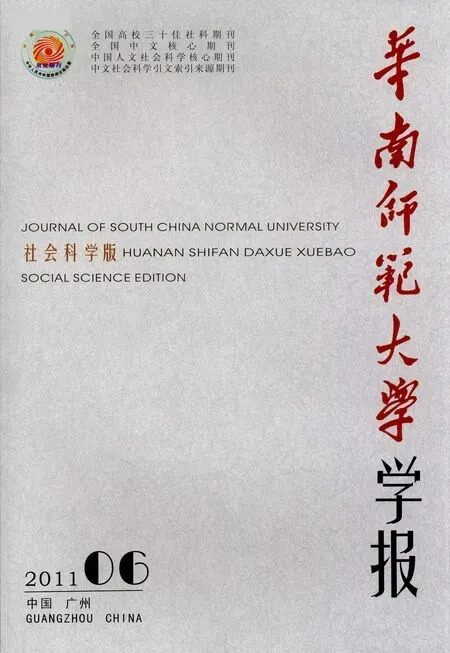中國轉型期城市化進程的路徑選擇——基于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視角
王 理
(廣東金融學院 經貿系,廣東 廣州 510521)
中國轉型期城市化進程的路徑選擇
——基于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視角
王 理
(廣東金融學院 經貿系,廣東 廣州 510521)
中國制度轉型的起點模式是傳統農業社會,目標模式是現代工業社會,城市化的實現同時也意味著轉型的完成。就長期、動態、持續的經濟發展來講,制度變遷理論比資源配置理論更有利于解釋我國城市化質量相對不高的根源。而以非正式制度的變遷為突破口,引導我國廣大農業地區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由傳統農耕文化向現代市場經濟理念進行轉變,可以有效地構建出一條非正式制度變遷驅動下的城市化路徑,順利推進我國當前的城市化進程。
非正式制度 制度變遷 城市化路徑
我國的城市化運動至今取得了巨大成績,僅從指標上看,中國的城市化率到2008年底達到45.6%,城市人口為6.07億人。如果按照1%的速度增長,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將超過50%,中國的城市人口將超過農村人口。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中國財政政策報告》,載新華網,2010-10-04。學者們在對待當前我國戶籍和土地制度與城市化推進的關系問題上,大致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將其視為城市化進一步推進的障礙和瓶頸,對其加快改革可以促進城市化進程,使我國內需在次貸危機之后可以有效擴大,進而保證經濟增長在高速度態勢上繼續運行。②巴曙松、邢毓靜、楊現領:《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動力:一種長期觀點》,載《改革與戰略》2010年第2期。而另一種態度則是反對為了一味追求城市化率指標而對當前戶籍和土地制度進行倉促改革。這些學者從農村現實情況出發,認為當前的戶籍和土地制度是農村社會經濟穩定的“穩定器和蓄水池”,而一旦倉促改革,則很容易使中國經濟發展脫離所需要穩定的社會政治條件。③賀雪峰:《小農經濟至少還應維持30年——答錢津先生》,載《貴州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
比較兩種觀點,我們認為第一種認識顯然缺乏對國情的深入了解。由于“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的農民大國的城市化,是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許多外國的經驗對我們是不適用的”④陳為邦:《中國城市化思辨》,載《城市》2008年第11期。。我國當前的戶籍和土地制度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存在,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客觀現實的需要。忽視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特有的制度因素,僅僅用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與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的模型和數據來簡單地評價和對比我國城市化的進程和質量,只能得出“半城市化”⑤王春光:《農村流動人口的“半城市化”問題研究》,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準城市化”⑥柴洪輝、晉洪濤:《農村城市化研究:一個綜述》,載《華東經濟管理》2009年第7期。和“偽城市化”⑦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中國財政政策報告》,載新華網,2010-10-04。的結論。而第二種觀點雖然立足于我國當前農村的現實,并用許多案例論證了當前戶籍和土地制度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由于其分析方法仍然沿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成本——收益法,既缺乏對這種正式制度與城市化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和揭示,也沒有提出有價值的建議和較強操作性的對策。
如何正確認識我國當前戶籍、土地等正式制度與城市化的關系,對于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和社會轉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從制度變遷的視角看,城市化是一個典型的制度變遷活動。因為城市化的內涵不僅是指農村居民在空間上從鄉村轉移到城市,而且也包括了他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過程。由于戶籍和土地制度等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間進行改變,但農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等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以非正式制度為切入點來研究城市化的制度瓶頸,有利于我們從本質上認識我國城市化質量相對不高的根源,并尋找出城市化順利推進的路徑。
一、非正式制度與制度變遷
(一)缺乏非正式制度改變的制度變遷是不完整的制度變遷
人們對非正式制度重要性的認識是隨著制度變遷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不斷深入的。無論是舊制度經濟學還是早期的新制度經濟學,都把制度簡單地界定為人們所制定的各種規則,制度變遷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理解為這些規則的變化。1973年,道格拉斯·諾斯提出了著名的制度效率假說——制度總是朝著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方向演進的,人們隨后便提出了質疑:如果制度演進的方向是經濟效率的提高,為什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并沒有像西歐少數國家那樣產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畢竟經濟發展的緩慢甚至停滯才是世界歷史的主旋律。對此,諾斯意識到了制度變遷絕不僅僅是人們制定規則的變化那樣簡單,并將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價值觀、道德、倫理、態度以及信仰等界定為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成文法、普通法、規章如產權、政治制度等)一起共同組成了完整的制度概念①[美]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4頁,劉守英,譯,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通過逐漸將學術重心轉移到對非正式制度、特別是對文化傳統的研究,得出了非正式制度的演變是制度產生及其變遷主要原因的結論,初步回答了人們對制度效率假說的質疑。由于制度本身就是由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共同構成的,因此,缺乏非正式制度改變的制度變遷根本就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制度變遷。
對于一個經濟共同體來講,正式制度的確定性與非正式制度的靈活性同樣重要。但由于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產生的前提和基礎,猶如有機體那樣脫離了母體,器官是無法單獨發揮其原有功能的,若強行進行器官移植,排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正式制度是被嵌入在非正式制度中發揮功能和作用的,根本離不開相關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協調與制約。如果將制度變遷簡單地理解為僅僅是正式制度的改變,無疑等于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正式制度的有限作用,這樣做就只能解釋制度變遷過程中的一些表面現象,無法觸及和解決深層次的實質性問題。正式制度的變遷必然要求非正式制度的相應改變,只有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的同步改變,才能真正完成完整的制度變遷,否則,變遷過程中必然會產生諸多復雜問題。因此,忽視非正式制度的變遷不但是不完整的制度變遷,更是對制度變遷的一種誤解。
(二)單一的正式制度變遷很難帶來相應的經濟績效
正確理解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它可以使人們從片面強調正式制度對制度變遷重要性的誤區中走出來,認識到非正式制度對制度變遷效率產生的重要影響,并為實施制度變遷活動的推進者提供一個重要啟示——單一的正式制度變遷很難帶來相應的經濟績效。
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自發性和持續性的特點使其一旦形成就會根深蒂固、不會輕易變化,并形成路徑依賴,而這也往往成為阻礙制度創新與變遷的重要原因。在制度變遷活動中,變遷很快的往往是正式制度,而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則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再加上正式制度是外部力量強加給共同體的原因,其存在和發揮作用必須依賴于非正式制度。因此,兩種制度變遷的時滯很容易使不適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干擾正式制度功能的發揮,擾亂社會經濟運行的秩序,從而降低經濟績效。
非正式制度的這種干擾性在以下的這個簡單模型中表現得很明顯:假定社會成員連續存在于T1和T2兩個相繼時期,在度過了T1時期之后,處于T2時期的人們是依靠T1時期存在于頭腦中的意識形態和信念體系對T2時的現實世界進行解讀的。也就是說,社會成員在T2時的共享心智模式是以T1時的共享心智模式為基礎的。這時社會成員的集體學習活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長期集體學習的內容發生改變,非正式制度就會由T1時期的內容變遷到T2時期的新內容。相反,如果集體學習的內容長期沒有改變,那么社會成員的共享心智模式就會相對僵化,與T時期相對應的新的集體信念體系無法得到更新和形成,非正式制度就沒有伴隨著正式制度的改變而進行相應的變遷,從而干擾正式制度應有功能的發揮,影響經濟效率的提高。“雖然正式規則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但非正式規則的改變只能是漸進的……采用另一個社會的正式規則的國家(例如:拉丁美洲國家采用的憲法與美國類似)會有與其起源國家不同的績效特征,因為他們的非正式準則和執行特征都不相同。”①[美]諾斯:《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發展》,路平,何瑋編譯,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年第5期。因此,單一的正式制度變遷不但是不完整的制度變遷,而且是很難帶來相應經濟績效的制度變遷。
二、滯后的非正式制度變遷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制約
學術界在討論我國當前的戶籍、土地制度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時,大都將其作為城市居民和農民重要的社會保障手段看待,在這樣一種新古典經濟學靜態資源配置分析框架下思考之后得出的結論只能是必須加快這些制度的改革。問題的關鍵在于,如果政府真的全面改革戶籍、土地制度,能夠有效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嗎?“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幾乎所有的農村城市化研究都會呼吁政府改革戶籍制度。然而,在許多中等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都放開了戶口之后,我們并沒有觀察到農民的大規模進城。”②柴洪輝,晉洪濤:《農村城市化研究:一個綜述》。其實,就長期、動態、持續的經濟發展來講,制度變遷理論比資源配置理論更有利于解釋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為什么正式制度變遷受阻從而影響整個變遷進程的原因。
(一)非正式制度變遷的主體缺失從根本上制約了我國城市化進程
當前農民如何市民化已經成為城市化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的難點之一,幾乎所有的文獻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都是站在政府的角度來討論的。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只要是有意識地推動或影響制度變遷的單位如政府、團體和個人等都是變遷的主體。理性地分析城市化的內涵,我們可以發現,城市化的本質是農民的城市化,農民應該是毫無爭議的城市化主體。因為“本質上來看,農村城市化是農民面對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推進所創造的機會的理性反應的結果,是農民的一種自我選擇”③柴洪輝,晉洪濤:《農村城市化研究:一個綜述》。。因此,忽視農民本身而僅將政府作為主體來研究城市化是欠妥的。因為把著眼點簡單地定位在政府身上,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農民這一非正式制度變遷的主體,城市化的推進自然而然就集中在了正式制度變遷的單一視角上。整個變遷活動必然被狹隘地理解為政府法律條文等正式制度的改變,不可避免地陷入“制度移植”的誤區,而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制度變遷。
我國當前的戶籍、土地制度是建國后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而其中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更是在非正式制度變遷驅動背景下形成的,是農民自主選擇的結果。這些正式制度在我國已經運行了幾十年的時間,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適應,農民已經形成并習慣了與之相對應的生產生活的思維方式和信念體系,非正式制度相對穩定并與正式制度一起組成了現有的一套實施機制。而城市化作為一種制度變遷活動,改革戶籍和土地制度本身不是什么困難的事情,甚至實行有些學者主張的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同的允許生產要素完全自由流動的制度也不困難,因為正式制度是很容易轉變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對于生活在中國廣大農業地區的農村居民來說,受封建社會長達數千年的影響,農耕文化作為傳統農業社會非正式制度的集中體現,目前僅僅是受到市場化傾向改革的沖擊和弱化,還未從根本上得到更新和替代,其主要特征和痕跡在廣大農民身上表現得依然明顯。因為“文化不僅扮演塑造正式規則的作用,而且也對作為制度構成部分的非正式制約起支持作用”④[美]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績效》,見[美]詹姆斯·A.道,[美]史迪夫·H.漢科,[英]阿蘭·A.瓦爾特斯主編:《發展經濟學的革命》,第119頁,黃祖輝、蔣文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而要想在一夜之間簡單地讓農民實現價值觀念的轉變是不可能的。猶如有機體脫離了母體的器官再也無法行使其原有功能那樣,強行移植正式制度必然受到非正式制度的排斥。因此,我們認為當前的戶籍和土地制度并非是城市化受阻的真正原因,忽略了農民作為非正式制度變遷這一重要的主體才是我國目前城市化存在的根本問題。
(二)非正式制度變遷的滯后降低了我國城市化制度變遷的經濟績效
為了更好地研究非正式制度,學術界通常將文化視其為在現實生活中的集中體現,①王理:《制度轉型與傳統農區工業化》,第13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因為“在所有的社會里,都有一種非正式框架構建人類的相互作用。這種框架是基本的‘資本存貨’,被定義為一個社會的文化。”②[美]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績效》,見[美]詹姆斯·A.道,[美]史迪夫·H.漢科,[英]阿蘭·A.瓦爾特斯主編:《發展經濟學的革命》,第119頁。在城市化這種制度變遷活動中,我們將農耕文化和市場精神分別界定為與傳統農業經濟和現代工業經濟相對應非正式制度的集中體現,所謂農耕文化,是指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人們價值觀和行為規則的總和,通常也被稱為“小農文化”或“小農意識”。而市場精神則是指建立在現代工業經濟基礎上人們價值觀和行為規則的總和。因此,城市化變遷中的非正式制度變遷可以理解為由農耕文化向市場精神的轉變。
由于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具有隱蔽性和獨立性,就像一只無形的手一樣指揮著人們的行為。因此,它的變遷具有時滯性。雖然我國的城市化速度很快,與傳統農業經濟相對應的農耕文化也受到了強大的沖擊和弱化,但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受封建社會長達數千年的影響,農耕文化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完全更新和替代,在生產與生活中的主要特征和痕跡表現得依然明顯:
第一,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的主導關系仍然體現在血緣與地緣的結合。產業離土不離鄉和農民離土不離家的現象說明數量眾多的非農產業市場拓展是以血緣為本位逐步進行的,絕大多數農民的根仍然牢固地扎在鄉土血緣的關系中是我國當前農村存在的不可回避的客觀事實。
第二,宗族權力對農村經濟和社會基礎的影響仍然明顯。雖然隨著農村中非農經濟的快速發展,中青年精英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傳統農業經濟的地位尚未得到徹底顛覆,在宗族權力與青年精英并存的時期,很多家庭的婚喪嫁娶與興修水利等地方事務仍需族人的權威。
第三,農村中禮治與法治并存的現象說明傳統禮教仍然在影響著目前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在當前我國許多農村和正在進行工業化建設的小城鎮,由于種種原因使法治在基層社會走樣,農民頭腦中的宗法關系仍然嚴重,人們普遍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現和存在,禮治制約法治、倫理與法客觀上在農村共同發生作用。
冷靜分析和思考我國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的狀況,不難發現,在目前廣大農民還深受傳統農耕文化影響的情況下,城市化變遷中的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并沒有同步進行轉變,非正式制度的變遷進程明顯滯后于正式制度,并直接干擾和影響了整個變遷活動的經濟績效。因為“經濟增長依賴于人們對工作、財富、節儉、生育子女、創造性、陌生人和冒險等等的態度,所有這些態度都是從人的頭腦深處產生的。”③[美]阿瑟·劉易斯:《經濟增長理論》,第11頁,周師銘、沈丙杰、沈伯根,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不適當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必將會干擾正式制度功能的發揮,加大社會運行的操作成本從而降低制度績效。
(三)滯后的非正式制度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制約作用
應當指出,文化作為非正式制度的集中體現,對制度變遷活動的制約作用十分顯著,主要體現在人們在選擇變遷路徑時仍然會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而降低制度安排和變遷的績效。因為當社會成員集體學習的內容長期不發生變化時,集體信念無法得到及時更新,認知性路徑依賴最終會導致制度的路徑依賴。農耕文化作為傳統農業社會非正式制度的集中體現,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人們的價值觀和行為規則的總和,通常也被稱為“小農文化”或“小農意識”。受路徑依賴的影響,農耕文化仍然在潛移默化地支配著廣大農業地區社會成員的行為,阻礙著多數農民擺脫傳統農業經濟的束縛、勇敢投身到非農經濟的城市化大潮中:
第一,“以農為本、以土地為本”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在維持著我國廣大農業地區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同時,也把數量眾多的農民固化在土地上并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內斂”保守傾向。這明顯與由工業化相伴而生的城市化所要求的專業化分工與競爭合作法則相背離,在農民缺乏向外擴散、開拓意識的前提下,短期內期望他們徹底擺脫土地束縛走向城市非農產業是不現實的。
第二,農耕文化群體本位的價值觀念在形成農村居民生產生活向心力的同時,也泯滅了個體成員自我生存與體現的價值,強化了人們頭腦中平均主義的思維方式。這顯然與工業化和城市化所要求的社會成員通過功利主義行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從而彰顯個人成就的信仰體系格格不入,客觀上既妨礙了生產要素受利益驅使而產生的正常流動,又排斥了市場經濟所倡導的通過自由競爭而得以實現社會效率的理想。
第三,農耕文化中與自給自足經濟相對應的封閉循環思維方式形成了農民對“安天樂土”的追求,社會成員極容易滿足于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狀況,缺乏擴大再生產的思想和能力。這種小富即安的信仰體系從本質上排斥了工業化和城市化所要求的社會成員必須具有敢于面對和承擔風險、大膽突破常規和尋求創新的價值理念。
張培剛在談到農耕文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時曾感嘆道:“在中國,資本主義為什么沒有發展起來?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歷史上探根溯源……中國封建制度的長期延續對中國整個經濟的發展造成的有害影響是很大的,使資本主義在中國雖有萌芽,但難以發展起來。”①張培剛:《懂得歷史,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發展》,載《江漢論壇》2001年第11期。
三、非正式制度變遷驅動下的中國城市化路徑
如何促使當前廣大農業地區的社會成員逐步擺脫小農意識的束縛、學習現代工業社會所要求的價值理念、真正實現由農民到市民的轉變既是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中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關鍵,同時也是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有效路徑。但這種非正式制度變遷驅動的城市化進程能否順利進行,還要取決于政府所驅動的與之相對應正式制度變遷的效率,因為制度是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二者的實施機制共同組成的,制度變遷活動不能忽視其中的任何一項內容。“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②[美]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20頁,陳郁、羅華平,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對于作為正式制度制定者和執行者的政府來講,有效利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間的互動過程對其制定適當的經濟政策十分重要。因此,我們認為要想順利推進城市化進程進而實現我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變遷,各級政府應根據本區域非正式制度變遷的進程來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正式規則以及實施機制,一定要完成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二者實施機制的制度變遷活動,有效地推進城市化進程,提高制度績效從而實現經濟發展。
(一)制定城市化制度變遷的整體規劃
從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的關系看,強約束力的正式制度能夠穩定社會成員的預期,減少經濟活動中的不確定性。“一個穩定的政府以及一些補充準則的建立是制度必不可少的特征。成功的政治或經濟體系就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中發展了此種特征。”③[美]諾斯:《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發展》。在我國逐步實施以非正制度演化為切入點的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的過程中,如果這種長期而緩慢的非正式制度自發演進活動得到正式制度的尊重和支持,政府就可以利用其自身特有的優勢有效地推動變遷的進程,對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發揮極其重要乃至決定性的作用。相反,如果這種非正式制度的演進活動無法得到正式制度強有力的支持,我國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的時間必將會大大延長,甚至有可能出現城市化進程中斷的現象,重蹈南美和印度等國家城市化進程中“貧民窟”遍地的覆轍。因此,各級政府在推進本區域的城市化進程時應該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擬定好制度變遷的整體規劃,通過正式制度的變遷來積極促進、推動變遷的整體進程。
首先,制定城市化變遷的目標。對于我國廣大的農業地區來講,城市化目標實現的表面形式雖然是農民轉化為市民,但政府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變遷的最終目標是由傳統農業社會進入到現代化工業社會,否則,只能會出現“偽城市化”的現象。當前現實可行的目標就是鼓勵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傳統種植業中解放出來投入到第二、三產業中去,用自己在工業化社會中的親身體驗去感知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價值理性,逐步擺脫傳統農耕文化的束縛。
其次,明確城市化變遷的主體。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只要是有意識地推動制度變遷或者對制度變遷施加影響的單位如政府、團體和私人等,都是制度變遷的主體。我們認為各級政府應該把區域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視為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的主體共同推動本區域的變遷進程,這樣既可以減少政府作為單一主體推動變遷的困難和壓力,同時也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城市化進程中因為忽視農民的需求而造成不必要的社會矛盾和突發問題。
此外,要做好城市化變遷長期性的準備。與新古典經濟學靜態資源配置思想不同,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變遷活動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并不能立即產生相應的經濟績效。發達國家城市化成功的經驗表明政府任何急功近利的思想都有可能帶來許多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使城市化進程的效率嚴重降低、甚至半途而廢。因此,在我國的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中,各級政府必須在非正式制度演化的過程中適時調整正式制度的變遷,使整個變遷活動的內容不斷豐富、方式不斷完善、實質不斷深入,逐漸使本區域由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現代工業社會,最終實現經濟發展。
(二)有效引導城市化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活動
非正式制度的演變雖然受路徑依賴的影響,是一個自發而緩慢的過程,但社會成員對此并非完全無能為力,制度變遷理論認為有效的正式制度是可以逐步引導非正式制度的變遷進程的。因此,各級政府在我國的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中可以提供一些富有效率的正式制度來改變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逐步引導非正式制度的變遷,以便加快整個城市化的進程。
由于恰當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可以對現行制度的合理性提供解釋,對于制度的穩定和制度變遷的成敗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采取大力宣傳的手段來強有力地影響和引導廣大農業地區的社會成員排除對我國當前戶籍和土地制度的陳舊認識,削減和淡化他們因傳統觀念而帶來走向市場的后顧之憂,在培育他們成為真正市場主體的過程中,鼓勵他們自發、主動地改變對現有戶籍和土地制度的認識,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像當初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成一樣,社會成員要在不斷糾錯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一套或幾套符合現階段農民需要的非正式制度驅動下的戶籍和土地的制度安排。這樣,政府的有效引導行為既可以營造出良好的制度變遷氛圍,又能使非正式制度變遷的要求得到正式制度的尊重和支持,為下一步較為關鍵和重要的戶籍和土地等正式制度的改變提供有利的強化機制,從而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順利推進。
(三)通過制度創新來增強政府的制度供給能力
制度變遷是一個無所不在、前進、累積的過程,當經濟發展遇到制度瓶頸時,制度創新能夠帶來較好的經濟績效。諾斯多次提到:“轉軌經濟國家有時為實現某種目標功能而建立制度,如果由此得出的結果不符合初衷,就要時刻準備修改制度。制度是在修正中慢慢演進的,任何制度都是如此。”①劉麗娟:《避免超越制度的力量左右制度——與道格拉斯·諾斯談轉軌國家制度缺口和制度的演進》,載《商務周刊》2004年第18期。
我們認為在城市化進程中,各級政府一定要根據廣大農業地區社會成員的動態需求進行制度創新,努力使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形成一個有效的實施機制,讓城市化制度變遷活動成為所有社會成員共同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只讓農民接受和適應政府制度供給的被動過程。如重慶市在2010年8月進行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戶籍和土地的制度創新活動:農民轉為城市戶口后,在3年的過渡期內仍享受各項土地的收益;過渡期結束后,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農房實行有償退出的方式;設立全國首個農村土地交易所,農民在土交所退宅基地,每畝可以拿到十多萬元人民幣,并且還可以申請公租房居住。②余靖靜、葉鋒:《我國城市化進程面臨考驗:外來務工者融入困難》,載新華網,2010-10-02。當然,政府在進行制度創新活動時,各地不可能有統一的操作模式,一定要根據當地農村居民的實際需求來提供制度供給,否則,極容易陷入制度移植的誤區。
林毅夫明確指出:“展望21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前景,讓生產力加速發展應該是我們的第一個優先選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變化,中國人的價值取向、行為準則也會改變。在變遷中,我們會揚棄一些過去的,建立一些新的,但決不會是簡單地照搬西方的準則。”③林毅夫:《經濟發展與中國文化》,載《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1期。因此,以非正式制度的變遷為突破口,引導我國廣大農業地區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由傳統農耕文化向現代市場經濟理念進行轉變,可以有效地構建出一條非正式制度變遷驅動下的城市化路徑,順利推進我國當前的城市化進程。
A Study on China's Urbanization Route in the Period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View of In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
(by WANG Li)
The original model for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its final model is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s also the process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change.As for the long,moving and lasting economy development,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can better explain the reason of the low qualit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han the theory of new classical economics.However,taking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s the starting poi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and thus leading all the social members'ideological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ulture to modern market culture in many agricultural areas in China,can construct its own urbanization route with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s a thrust and promote China's present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formal 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urbanization route
王理(1969—),男,河南汝南人,經濟學博士,廣東金融學院經貿系講師。
本文獲廣州市人文社會科學區域金融政策重點研究基地資助
2011-07-20
F29
A
1000-5455(2011)06-0094-06
【責任編輯:王建平;實習編輯:楊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