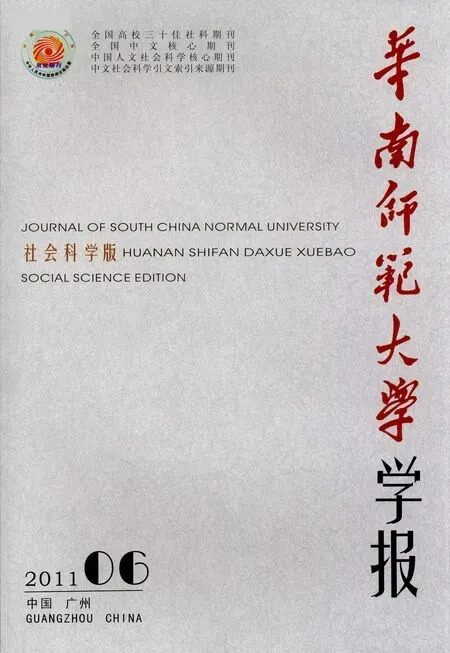“限知視角”與小說的翻譯創作——以《草原日出》和《喜福會》的翻譯為例
王心潔,陳 曦
(1.暨南大學 翻譯學院,廣東 珠海 519070;2.暨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限知視角”與小說的翻譯創作
——以《草原日出》和《喜福會》的翻譯為例
王心潔1,陳 曦2
(1.暨南大學 翻譯學院,廣東 珠海 519070;2.暨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2)
“限知視角”主要指讀者只能通過小說敘述者或人物的個人視角了解故事情節的發展。小說翻譯是一種再創作,難免會對小說的敘事進行操控性的重寫。由于不同的視角會傳達出不同的美學信息或主題意圖,引發不同的情感反應,因此譯者需要充分重視原小說中易于混淆的“限知視角”,盡量減少翻譯過程中的視角偏差。此文以《草原日出》和《喜福會》的譯文為例,探究譯者應如何把握第三人稱敘述中兩種不同的“限知視角”。
限知視角 小說翻譯 草原日出 喜福會
敘事學興盛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法國,重視探討文學作品內部的敘述結構,在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小說文本的建構由敘事完成,而敘事是由兩部分組成:故事和話語,即敘事的內容和敘事的方式。敘事學的代表人物之一熱奈特對敘事學中的重要概念進行了界定和區分。另一位領軍人物布斯則從修辭學切入,提出“隱含作者”的概念,對敘事學進行了更為直觀的探討。對小說進行敘事研究有利于對小說的審美價值與主題意圖進行更為深入的把握。因此譯者應重視敘事話語分析,否則在翻譯創作中難以避免遺漏或失誤。在小說敘事的形式技巧中,敘事視角的運用與變化是譯者應當關注的重點之一,因為文學作品中敘述視角的設置往往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能體現出敘述者的立場觀點。因此譯者除了要把握明顯的視角轉換,也要能夠辨析隱蔽的視角調節,并在譯文中再現。本文試結合小說《草原日出》與《喜福會》探討小說翻譯中敘述視角之一——限知視角與翻譯創作的緊密聯系。
一
讀者的闡釋過程是敘事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認知(建構)方法的代表人物A.紐寧在其創始者塔馬·雅克比的研究基礎上,提出在面對同一作品時,不同的讀者可能會建構出完全不同的作品“總體結構"(the structuralwhole)。[1]這一方法“聚焦于讀者的不同闡釋策略或闡釋框架之間的差異,并以讀者本身為衡量標準。既然以讀者本身為標準,讀者的闡釋也就無孰對孰錯之分”。[2]讀者的任何閱讀假設都可以被改變、歪曲,甚至被另一種假設所取代。[3]這就為譯者進行自由的翻譯創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譯者首先要作為讀者闡釋源語文本,然后在此基礎上重新敘述故事,繼而與譯入語讀者間形成闡釋循環。然而,如果完全將讀者的閱讀假設作為評論準繩,就極有可能會誤解甚至歪曲原小說的意義。這一缺憾已引起文學批評界的關注,在翻譯界則更應當得到重視和修正。
以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的短篇小說《草原日出》(A Sunrise on the Veld)①文中所引原文語句均出自 http://www.peninsula.wednet.edu/classroom/robisonp/Sunrise%20on%20the%20Veld.htm中的一個句子為例。這篇小說講述了一個充滿自信的小男孩在林中打獵時,目睹了一只雄鹿被群蟻吞食。在描述男孩看到殘酷場景后的反應時,文中有這樣一句話:
And at that moment he could not have performed the smallest action of mercy,knowing as he did,having lived on it all his life,the vast,unalterable,cruel veld,where at any moment one might stumble over a skull or crush the skeleton of some small creature.
譯文:他有生以來一直生活在這片廣闊的、無法改變的、殘酷的草原上,人們在這里隨時都會被一塊頭蓋骨絆倒,要不就會踏碎小動物的骷髏。所以,他很清楚,此刻他沒法采取絲毫行動來救這小動物。[4]
根據認知(建構)學派的觀點,這種譯法并無不妥。但譯者不是普通的讀者或評論家,他是“帶著鐐銬的舞者”,不能完全自由發揮,需要在小說原文的基礎上傳遞信息,因此還應考慮到“隱含作者”的規范。這一概念由韋恩·布思提出,他認為“作者在創作某一作品時特定的‘第二自我’就是該作品的‘隱含作者’……盡管布思一再強調作品意義的豐富性和闡釋的多元性,但受新批評有機統一論的影響,他認為作品是一個藝術整體(artistic whole),由各種因素組成的隱含作者的規范也就構成一個總體統一的衡量標準”,而這里的規范指的是“作品中事件、人物、文體、語氣、技巧等各種成分體現出來的作品的倫理、信念、情感、藝術等各方面的標準”。[2]譯者從讀者轉為再創作者時,不應太過偏離原文的作者規范。畢竟譯入語讀者還是希望能通過譯文更多地了解原文而不是看到面目全非的譯文。以此句為例,譯文對草原的表述與原文內容基本相符。但從語法角度分析可知,這句的正常語序應該是He did know having lived…creature,at that moment he could not…mercy。從know(知道,了解)這一明顯的線索可以判斷出整句都是人物對草原殘酷性的痛苦反思。也正是在這一頓悟后,男孩才承認他對眼前的狀況無計可施。但是譯文將這種帶有濃烈主觀色彩的人物感知變成了敘述者較為客觀冷靜的事實陳述,這就與男孩此刻對生活的新認識(即“這種時刻的無能為力”)失去了必然的因果聯系。可見此處譯者對視角的不當處理造成了邏輯漏洞。譯者在進行翻譯創作時,不妨打破原句的句式結構,結合漢語表述習慣,將后三個分句表述為男孩心理活動的一部分,以利于譯入語讀者深切感受到男孩的心理變化。例如:就在那時他意識到,此刻他的憐憫完全派不上用場,因為在他一直生活的這片土地,這片遼闊、殘酷、從未改變的草原上,人們隨時可能絆到頭骨或踩碎小動物的殘骸。
由此可見,譯者可以擁有充分的創作空間,但并非毫無顧忌,原文的作者規范應成為譯文創作的參照標尺之一。由于敘事類型是作者規范的重要構成要素,因此也應成為譯者需要重點關注的對象。“小說翻譯,審美效果的對應和作者的敘述意圖的再現主要體現在敘事類型上。”[5]“全譯(小說)如果置身于更大更廣的敘事類型語境,就能有效把握原文的敘事意圖,微觀層面的詞句乃至修辭的轉換,也有望得到根本性解決。”[6]而敘事類型中,敘述者和敘述視角尤為重要。視角指敘述時觀察故事的角度。[7]熱奈特(Genette)對其做出的三類劃分被廣泛使用。我國敘事學界頗具權威的申丹教授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更為全面的四大類視角:無限制型視角,即全知敘述;內視角;第一人稱外視角;及第三人稱外視角。[7]限知視角,即是與全知敘述相對的視角,包括后面三類。例句的翻譯其實就涉及了敘事學中的限知視角,也是本文將要重點論述的視角。由于視角的變化會傳達出不同的美學信息或主題意圖,引發不同的情感反應,因此譯者在進行翻譯創作時,應根據“限知視角”的不同,“分析它的形式特征并予以傳遞,使譯文符合原文的敘述特點和意圖性”[8],具體來說主要分為兩個層面:(一)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譯者在創作譯本時,不能滿足于字面含義的等值,應將敘述視角中展現的立場、語氣等在譯文中以適當的甚至創新的形式表現出來,令譯文與原文具有相似的藝術感染力。(二)對敘述文本主題的把握。譯者不應止步于直觀的故事情節復述,而要能夠把握原作品中視角選擇的獨具匠心之處,并在翻譯創作中選擇適當的方式,將視角間的微妙轉換及其中的深意傳達給讀者。
二
與戲劇不同,小說表達一般總是同時涉及“敘述者”和“感知者”,有時兩者合二為一,有時則相互分離。[7]清晰地判斷出兩者的關系是把握限知視角的關鍵。其中易令人迷惑的主要是內視角和第三人稱外視角中的限知視角。下面以《草原日出》和《喜福會》為例,論述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這類視角的必要性。
(一)翻譯創作中“限知視角”對內心刻畫的影響
《草原日出》中小男孩看到蟻群食鹿的場景,其中有這樣一句話:
He gripped the gun between his knees and felt in his own limbs the myriad swarming pain of the twitching animal that could no longer feel.
譯文:他用雙膝夾著獵槍,四肢感到無限劇烈的苦痛,而那抽搐的小動物已喪失這種感覺了。[4]
從表面上看,譯文與原文傳達的內容基本相似。但如果對原文進行視角分析,則會由felt(感到)推知后半句的描述是從男孩的視角切入,屬于第三人稱限知視角。從上下文可知男孩知道小動物已沒有知覺。但受到血腥吞食場面的刺激,他似乎親身感受到了被蟻群撕咬的痛苦。而譯文中三個分句的主語從“他”變成“四肢”最后變成“小動物”,實際是將感知者從視角有限的人物轉變成全知的敘述者,將人物的主觀感受轉變成敘述者的客觀評述。這樣就削弱了人物內心發展的戲劇性效果。其實譯者可以在進行翻譯創作時,增加一些突出感知者身份的詞語以更清晰地傳達原文的視角信息。例如:他用雙膝夾著獵槍。他很清楚那抽搐著的小動物已失去知覺,卻覺得那種被無數螞蟻吞噬的劇烈苦痛侵蝕著他的四肢。由此可見,敘述者和感知者分離時容易產生誤讀,需要譯者謹慎對待,并進行適當的翻譯創作。但兩者統一時,要想傳神地再現人物內心活動,有時也要費番心思。
華裔美國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最常采用的敘事策略之一是內視角。因為跨國的文化雜合是華裔文學的一個重要特性,而這類視角可以充分展現人物在雜合文化影響下的文化心態。在譚恩美《喜福會》中,作者通過對固定式內視角的嫻熟運用,將人物的心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主人公之一的羅絲是華裔的后代,和美國白人泰德相愛。在結婚伊始,羅絲就將自己想象成悲劇的女主角,而她的丈夫泰德是英雄,總能救她于危難。內心深處的自卑使其過度依賴于丈夫,不敢承擔生活中的責任,事事聽從丈夫,完全沒有主見。可是最終慘遭丈夫遺棄時,她無法再繼續逃避現實,但長期喪失自我的生活使她不知該如何應對,對未來深感迷茫:“Lately I had been feeling hulihudu.And everything around me seemed to be heimongmong…I suppose the closest in meaning would be‘confused’and‘dark fog’.”[9]這里采用了內視角。這句話本身并沒有艱澀的詞匯或復雜的語法,但是有一個很特別的語法現象,即引入了漢語拼音。此處的拼音其實大有深意。在離婚發生前,羅絲一直排斥自己文化身份中的中國性,推崇美國思維。然而婚姻的失敗迫使她反思自己的身份定位,開始接納母親不斷向她灌輸的中國文化和智慧。這里的hulihudu和heimongmong其實就是她母親勸說她時的用語。通過羅絲的視角,通過她自述時對漢語表達方式的接受,讀者可以感受到她對自身中國性的逐漸認可。因此在翻譯此句時,譯者如果直接將拼音譯回漢語,就無法將原句中這種內心情感的推進傳達出來。所以譯者應保持這兩個詞的拼音形式,再現它們在原文中與英文單詞的區別,突出她開始理性自我定位的重要時刻。這種看似簡單的處理其實也是譯者在對句子視角深刻理解的基礎上選擇的一種翻譯創作方式,與一般性的直譯有很大不同。
譯文:近來,我一直感到hulihudu“糊里糊涂”的,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是heimongmong“黑蒙蒙”的……我想在英語中和它們最接近的意思應該是“困惑”和“黑霧”吧。
在羅絲的反思中,她意識到自己喪失自我的罪魁禍首,正是一直影響她的美國思維:讓人有太多選擇,以至使人非常迷惑,最終做出錯誤的選擇。因此當她最終聽取母親的建議,重新變得自信時,就徹底地從他丈夫的陰影中解放出來,心中一片敞亮:All the questions:gone.There were no choices.I had an empty feeling ——and I felt free,wild.”[9]此刻羅絲已經重拾自我,不再困惑,原文通過羅絲的內視角充分展現出她愉悅的心情。如果譯者忽視了這里全部使用內視角的深意,誤將前兩句理解為評述性文字,并且僅僅按字面意思翻譯成“所有問題都不存在了。沒有選擇了。我感到一陣空虛——有一種自由、瘋狂的感覺”,就無法反映出她獲得新生的欣喜,反而有背道而馳之嫌。這里的no choices并非真的指她走投無路,沒有選擇,只是表明她已不再為過多的選擇糾葛,不再患得患失,無所適從。所以前兩句并非客觀描述,而是羅絲的主觀感受。這里的empty feeling也不是指她感到內心空虛,其實是想表現出她如釋重負的輕松。因此譯者此時要透過表層含義看到人物心態的逆轉,在翻譯創作時對關鍵詞句進行適當的闡釋,將人物內心經歷的巨大變化在譯文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避免干癟的、沒有感情色彩的直譯,否則有可能令讀者不知所云。
譯文:所有的問題都煙消云散了!再不用為選擇煩惱了!我一下子如釋重負——感到那么的自由,無拘無束。
(二)翻譯創作中“限知視角”對主題建構的影響
在對敘述視角的論述中,申丹特別提出,應區分第三人稱敘述中兩種不同的“限知視角”:“選擇性全知”和“人物有限視角”。前者指全知敘述者選擇僅僅透視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后者指全知敘述者通過人物的感知來聚焦。[10]這兩種模式在文學作品中十分常見,但有時交錯在一起,變得不易辨別。
《草原日出》整篇小說屬于選擇性全知敘述,“敘述者”即是“感知者”,或稱聚焦者,故事主人公的感知為聚焦對象;但有時這一限知視角會轉換為主人公的有限視角,即借用人物感知來聚焦,“感知者”不再是“敘述者”而是人物本身。《草原日出》中對螞蟻帶有主觀色彩的敘述主要有兩處:
第一處是當男孩剛剛發現涌向雄鹿的蟻群時:He looked wildly about,and then down.The ground was black with ants,great energetic ants that took no notice of him,but hurried and scurried towards the fighting shape,like glistening black water flowing through the grass.
第二處是在男孩在螞蟻吞鹿場景的刺激下轉變了人生觀后,敘述者告訴我們:
The boy looked at them,big black ugly insects.
兩處視角都是人物限知視角,都是在男孩看到蟻群吞食雄鹿這一場景下。但譯者可能會在兩句的邏輯語境信息中發現不協調之音。雖然剛看到蟻群時他的憤怒程度弱于思想轉變后,但他那時就已經為雄鹿的痛苦掙扎所震驚,也能看出螞蟻是罪魁禍首。因此從一開始他對螞蟻就沒有任何好感。但在第一處敘述中,居然出現了great energetic,glistening這些幾乎帶有贊嘆色彩的形容詞,和第二處飽含仇視的ugly insects形成較大反差。譯者對矛盾視角的處理也可以成為一種創作。在這個例子中,譯者可能會根據譯入國對非洲人民的態度,將前一處表述成略帶嘲諷甚至貶義的修飾語,或將后一種改為褒義詞,使前后保持一致。可是譯者應該感到疑惑的是,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為幾乎橫掃歐洲所有文學獎項的文學巨匠,萊辛為何會在這種小小的邏輯問題上失誤?是否這一矛盾敘述中隱含著作者的某種深意?譯者在創作中進行的變動是否會影響到文章的主題表達?此時譯者可從“隱含作者”入手,進一步探究此處視角的微妙之處。
“隱含作者”是由韋恩·布思在《小說修辭學》中最先提出。布思對這一概念的闡述涉及“編碼”和“解碼”兩個方面:小說作者是處于創作狀態的“正式作者”,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我們會讀到的內容”(編碼);同時也是讀者根據作者的文本內容建構出的一個“如此寫作的正式作者的形象”(解碼)[11]。由此可見,“在編碼過程中,作為文本生產者的“隱含作者”處于作品之外;但在解碼過程中,作為文本隱含的作者形象的“隱含作者”則處于作品之內。[12]“隱含作者”的提出并非要消解真實作者的地位,而是深刻地解構了作者在創作中所處的多個層面。作為譯者,不僅要以讀者的身份積極參與解碼,通過文本傳遞的信息勾勒出作品內隱含作者的面貌,還要重視形成作品的編碼過程中真實作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聯系,這樣才能更全面地把握作者創作時的思想傾向及對小說主題的建構。
申丹多次強調,一個人寫作時的立場與其個人經歷和社會環境密切相關。[12]《草原日出》的作者萊辛的早年生活都是在非洲度過的,她從不掩飾自己對那片土地和那里人民的熱愛,其著名的《非洲故事集》(1964)更是集中體現了其反對種族歧視的思想。《草原日出》就出自這個集子。雖然在這篇小說中只有一個人物,但依然可以在其中嗅到種族歧視的氣息。文中多次暗示男孩不是非洲本地人。當男孩發現雄鹿被困于蟻群是因為腿部受傷時,他絲毫未考慮可能是和他一樣喜歡狩獵的其他外來者所為,而是立刻聯想到一群向雄鹿擲石頭的非洲人。他此刻完全忘記了自己獵殺者的身份,忘記了草原生存法則中殘酷因素的必然性,而是以滿懷博愛之心的高姿態,鄙視狩獵的殘忍,而且本能地將非洲人而不是自己的族群納入這個捕殺的畫面中。這種鄙視正是他仇視黑螞蟻獵食的心理根源。因而黑螞蟻與非洲人影像疊加,合二為一,而男孩則代表了有種族歧視思想的外族。故事最后,男孩意識到自己才是公鹿遭遇不幸的始作俑者,非洲人與此無關。這一情節安排反襯出開始時男孩憎恨螞蟻(非洲人)的武斷,傳遞出隱含作者對種族主義者歧視非洲人的批判態度。至此譯者通過文本建構可以確認,隱含作者與真實作者在種族問題上立場相同。此時譯者可以推斷出,第二處具有污蔑性的敘述(insect除了“蟲”這一含義,還有“可鄙的人,渺小的人”這層含義)由于是小男孩的眼光在敘述層面上運作,因此導致了敘述話語的不可靠。“這種不可靠敘述的獨特之處在于人物的不可靠和敘述者的可靠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和由此產生的反諷效果可生動有力地刻畫人物特定的意識和知識結構”。[2]而第一處中小說人物的視角才是與隱含作者一致的視角,即對非洲人民團結一心時巨大力量的贊嘆。此處是可靠敘述。作者可能想借兩處視角的差異引發讀者好奇,使其進一步探究個中玄機,以更深刻地理解小說。此時譯者在翻譯時不應過度創作,致使掩蓋這里的邏輯矛盾,而應將其忠實再現,但這并不意味著譯者在創作中的無所作為。因為此處視角的變化十分微妙,讀者若非有心揣摩,恐怕難以體會其中奧妙,因此譯者可以將自己對原文的闡釋加在譯文的注釋中,幫助讀者更快地領會個中意趣。
小說翻譯創作中把握好限知視角,可以更好地傳達作品的感情色彩,再現人物隱秘的心理和體現小說的深刻主題。把握好限知視角進行小說翻譯創作的關鍵在于譯者要有豐富的語源國與譯入國兩種文化知識的儲備,對作者及其創作意圖的深刻了解,對文本的精準解讀以及嫻熟的翻譯技巧。
小說翻譯的過程是譯者全面解讀原作并讓其在譯文中再生的創造性寫作過程。在此過程中,“譯者的個性及主體性也被翻譯,在原文和譯文間留下文學空間”[13],為原小說注入新的生命力。原文對譯者的限制不僅不會阻礙譯者的創作發揮,反而能進一步激發譯者的創造性。但是這并不代表小說翻譯創作的空間可以任意拓展。譯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依然要受到各種制約,如“兩種語言的特點、習慣,語言轉換的客觀規律,原作的語言、文化和審美特征,譯者所處的時代語境,特定時代的翻譯觀,等等”。[14]因此譯者在對原作進行個性化翻譯創作時,仍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在譯作中再現原小說的核心思想與文本特色。“將敘事學運用于小說翻譯批評能避免小說翻譯中形式與內容的二元對立。”[7]譯者應對小說中易于混淆的限知視角給予足夠的重視,盡量減少小說翻譯過程中的視角偏差,這樣才能在翻譯創作中更好地傳遞小說語言形式中蘊涵的主要美學功能和文學意義。目前此類敘事學研究在我國翻譯界的聲音還很微弱,需要更多譯者的參與。
[1]Nünning,Ansgar.Deconstructing and Reconceptualizing the Implied author.Anglistik:Organ des Verbandes Deutscher Anglisten,1997(8):95-116.
[2]申丹.何為“不可靠敘述”.外國文學評論,2006(4):133-143.
[3]Yacobi,Tamar.Authorial Rhetoric,Narratorial(Un)Reliability,Divergent Readings:Tolstoy's Kreutzer Sonata∥In A Phelan and Rabinowitz edited.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2005.
[4]沈黎.草原日出//《外國文藝》編輯部.現當代英國短篇小說集.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
[5]鄭敏宇.敘事類型視角下的小說翻譯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6]黃忠廉.小說全譯的宏觀探索——《敘事類型視角下的小說翻譯研究》讀后.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2007(4).
[7]申丹.視角.外國文學,2004(3).
[8]張景華.敘事學對小說翻譯批評的適用性及其拓展.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
[9]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9:210 -217.
[10]申丹.選擇性全知、人物有限視角與潛藏文本——重讀曼斯菲爾德的《唱歌課》.外國文學,2005(6).
[11]Booth,Wayne.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U of Chicago P,1961.
[12]申丹.再論隱含作者.江西社會科學,2009(2).
[13]Loffredo,E.& Perteghella,M.(eds.).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Perspectives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London:Continuum,2006.
[14]謝世堅.論文學翻譯中的譯者主體性及其限度.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4).
王心潔(1953—),女,浙江麗水人,暨南大學翻譯學院教授。
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文學翻譯與創作空間”(08JA740020)
2010-10-26
H059
A
1000-5455(2011)06-0148-05
【責任編輯: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