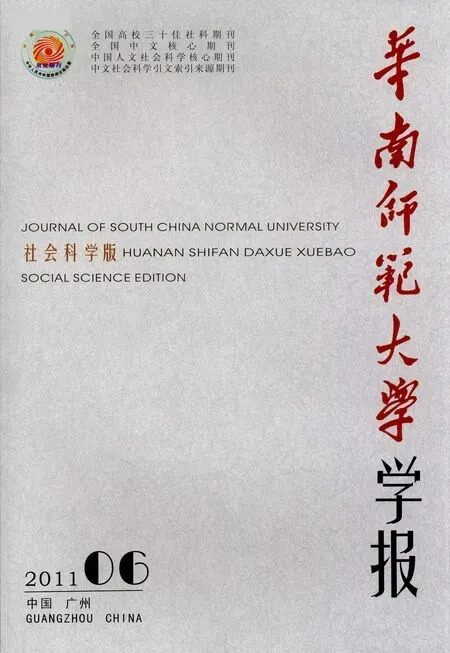異化的表達:《紅樓夢》詩詞英譯的互文性
朱 耕
(黃淮學院外語系,河南 駐馬店 463000)
異化的表達:《紅樓夢》詩詞英譯的互文性
朱 耕
(黃淮學院外語系,河南 駐馬店 463000)
《紅樓夢》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遣詞造句,無處不充滿豐富的互文性。翻譯過程中大量的互文指涉,無不蘊涵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譯者在翻譯實踐中借助異化策略,表現異域文化的互文性,達到了文化交流之目的。
互文性 《紅樓夢》詩詞 意象 異化翻譯
著名紅學家周汝昌認為《紅樓夢》是世界了解中國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據陳宏薇和江帆(2003)統計,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紅樓夢》的英譯本有9種之多。[1]47而《紅樓夢》英譯版本之多和翻譯之艱巨,又使得《紅樓夢》英譯成為翻譯研究的一個熱點。自從楊憲益及其夫人戴乃迭,戴維·霍克斯的譯本問世以后,出現了《紅樓夢》翻譯批評和研究的好形勢,研究文章散見于各種學術刊物,同時《紅樓夢》翻譯研究專著也相繼問世,如2001年南開大學王宏印教授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英譯比較研究》,2004年,范圣宙的《紅樓夢管窺——英譯、語言與文化》,2006年馮慶華主編《紅樓夢翻譯研究藝術研究》等。本文欲借助互文性理論,探討《紅樓夢》詩詞英譯問題,進而拓寬《紅樓夢》翻譯研究領域,為“紅學”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一
互文理論是當代西方哲學社會思潮的產物。互文(intertextuality theory)從其發端之日起,便廣受關注。互文性理念最早可追溯到俄國學者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e)有關復調理論和對話理論的思想。[2]6受巴赫金思想的啟發,法國符號學家朱麗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其《詞、對話、小說》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互文性”的概念,同時指出“一個詞(或一篇文本)是另一些詞(或文本)的再現,我們從中至少可以讀到另一個詞(或一篇文本),任何一篇文本的寫成都如同一幅語錄彩圖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轉換了別的文本。”[3]4即每一個文本中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每一個文本都不可能是一個與外界絕緣的封閉的語言體系,而是與其他文本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系。互文性涵義本身頗為復雜,并且隨著人們認識的變化而有所發展。大致看來,互文性有廣、狹兩層涵義:狹義觀點認為,互文性是指一個文本與存在于本身中的其他文本之間所構成一種有機聯系,其中的借鑒與模仿是可以通過文本語言本身驗證的。廣義觀點認為,互文性是指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所有文本符號之間的關系,它包括對該文本有啟發價值的歷史文本及圍繞該文本而存在的文化語境,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知識網絡,時刻影響著文本創作及文本意義闡釋。
二
《紅樓夢》無論是思想內容,還是遣詞造句,無處不充滿豐富的互文性,同時又是我國唯一一部真正“文備眾體”的小說。《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共計兩百多篇,其數量為中國章回小說之冠。以詩為論,有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排律、歌行 、騷體,有詠懷詩、詠物詩、懷古詩等等。正如羅蘭·巴特所言:“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個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本文,任何文本都是對過去的引文的重新組織。”[4]104這些詩歌或擬初唐《春江花月夜》之格的,有仿中晚唐《長恨歌》、《擊甌歌》之體的,有師楚人《離騷》、《招魂》等作而大膽創新的,五花八門,豐富多彩,也就是說大都留有對以前的文本借鑒、模仿抑或創新的痕跡。引用、用典、戲擬、糅雜這樣顯性的互文手法在《紅樓夢》詩歌中隨處可見。《紅樓夢》中關涉古人詩詞,涉及作者四十四人,從魏晉到元明都有,以唐宋為主,[5]同時這些詩詞又都融合在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命運當中,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比如,林黛玉的《桃花行》,寫的是“淚干春盡花憔悴”情景,就與前文的《葬花吟》互文,薄命桃花當然是她不幸夭亡命運的象征。
互文性會給翻譯帶來很多困難,但妥善處理互文性可以幫助克服不同語言的巨大障礙,促進源語信息和目的語信息之間的有效傳遞,盡量減少文化缺損,從而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掃清障礙。下面以《紅樓夢》的兩首詩歌及其英譯為例,探討詩歌的互文性翻譯問題。
例1:《詠菊》
無賴詩魔昏曉侵,繞籬欹石自沉音。
毫端運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
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
一從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風說到今。[6]278
在對文本的研究中,互文性理論關注文化傳統通過文本文學創作的影響。羅蘭·巴特曾指出,文本是作為文化的一種表意體系而存在的。自從屈原在《離騷》中借“夕餐秋菊之落英”抒發志向以來,菊花不僅與孤獨傲世的高人、隱士結下不解之緣,更成了文人學者們人格魅力的象征。因此在中國文學史上,描寫菊花的詩篇數不勝數,尤其以陶淵明和李清照的最為有名。
曹雪芹作為文學大師,對菊花文本,菊花的文化意象當然爛熟于心,他按頭制帽,詩即其人,[7]7以菊花的文化意蘊塑造了黛玉孤苦、高潔、隱逸的詩化形象。蔡義江指出,“曹雪芹慣于讓所詠之物的‘品質’去暗合吟詠它的人物。詠物抒情,恐怕沒有誰能比黛玉的身世和氣質更與菊相適合的了,她比別人能更充分、更真實、更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完全合乎情理的。”[7]247中國文學傳統自古悲秋、傷春,借助于“月”、“秋”、“菊”等意象隱喻,曹雪芹將黛玉的人生的悲劇感懷宣泄得淋漓盡致。黛玉說過(第四十八回)“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緊”,她在“詠菊”中的立意是顯而易見的— —以菊花的君子之風自比。林黛玉自比菊花之高潔,也暗合了《紅樓夢》的愛情主題:木石前盟——林黛玉是絳珠仙草下凡,以眼淚報答神瑛侍者的灌溉之情。[8]237
下面是Hawkes的譯文:
Celebrating the Chrysanthemums
by River Queen
Down garden walks,in search of inspiration,
A restless demon drives me all the time;
Then brush blooms into praises and the mouth
Grows acrid -sweet,hymning those scents sublime.
Yet easier'twere a world of grief to tell
Than to lock autumn's secret in one rhyme.
That miracle old Tao did once attain;
Since when a thousand bards have tried in vain.[9]251
霍的翻譯可謂音美、形美,意美,句式齊整、節奏感明確,突出了響亮的雙元音/ai/、/ei/,同時又用了time、sublime、rhyme;attain、vain來壓尾韻,屬于意譯,但詩歌當中所隱含的那種微妙的文化和美學互文意義,在譯文中基本沒有得到傳達,如,“詩魔”,“魔”來自于佛教,帶有很強的派生能力,佛教把人們有所欲求的念頭都說成是魔,宣揚修心養性用以降魔,所以,白居易的《閑吟》說:“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后遂以詩魔來說詩歌創作沖動所帶來的不得安寧的心情。霍用demon來翻譯此意義,隱性變為顯性,也造成了差額翻譯。素怨即秋怨,與下句“秋心”成互文,秋心,秋日的情懷,秋、心合成為愁字,是會意字,另吳文英《唐多令》詞:“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Hawkes的譯文翻譯過來就是“在詩歌中訴說憂傷要比鎖住秋天的秘密容易。”于原文意義相差較大,意蘊盡失,更是談不上互文性的翻譯。
另外,在霍的翻譯中一些具有互文意義的文化意象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省略。對于以意象為生命的詩歌語言,意象的缺損無疑會阻礙互文義的表達,尤其是詩的意境,沒有了意境,也就沒有讀者豐富的想象力。首先是“月亮”的文化意象。從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歐陽修的“月上柳稍頭,人約黃昏后”,它具有豐富的互文性,在中華文化里,月是生命的飛逝,是美的煙波,是人生悲歡離合的演繹……。“對月吟”一解為“明月”,意思是在月光下做詩,可是,查閱原文,我們知道,黛玉等人做詩是在日間,所以,詩人選擇此意象,是刻意借“月”的皎潔與高掛天空來烘托菊花的高潔與孤寒,可是這一重要的文化意象卻被霍丟掉了,根本沒翻譯出來。第二是陶淵明的文化意象。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獨樹一幟的。他的詩描寫田園風光,詩風恬淡清新,對后世山水田園詩的發展作出了開啟山林的作用。陶淵明當年不愿“為五斗米折腰”,隱耕田園,特愛菊花,菊花也因為他的品題而聲名鵲起。其《和郭主簿》中的“芳菊開林間,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心,卓為霜下杰”,便為菊花定下了高潔的基調。但霍只用了一個old Tao,沒加絲毫注釋,這會讓英語讀者不知所云。異文化中的一般讀者因缺少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而產生無法填充空位的文化缺省,這就對譯者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2
彩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6]245
這是林黛玉《題帕三絕》中的一首。湘江舊跡有著豐富的互文意義,是理解和翻譯的難點。《述異記》:“舜南巡,葬于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 、女英(都嫁于舜為妃),追之不及,相于慟哭,淚下沾竹,竹上文為之斑斑然。”湖南湘江一帶特產一種斑竹,上有天然的紫褐色斑點如血淚痕,相傳是二妃淚水染成,又稱湘妃竹。[7]218本詩“湘江舊跡”即指二位妃子所流的眼淚。另外,竹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因其節堅、中直、傲霜、寧折不彎而被稱為“君子”,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人格載體,晉代王子猷說“不可一日無此君”;蘇軾“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鄭板橋“唯有竹為君子伴,更卉許同載”。由此可以看出,以竹形容“孤標傲世偕誰隱”的林黛玉孤傲高潔、不甘流俗的品性是相當準確的。林黛玉愛哭,她來到人世是為了酬答知己而“還淚”的,斑竹所代表的文化意蘊著林黛玉的性格心態,可謂恰如其分[10]13。另秦觀有《踏莎行》詞:“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其中“杜鵑”與紫鵑之名互文暗合,且該詞凄婉憂傷,寫盡了青年兒女的離愁別緒。瀟湘妃子和瀟湘館也正來源于以上互文意義。這樣瀟湘館就帶有濃厚的中國文化互文意蘊,不但有淚痕斑斑的瀟竹,預示著林黛玉的性格秉性和凄慘的生命結局,而且可以看到優美的中國神話的影子。這一名稱所引發的思緒聯想和感情觸動,極大地提高和加強了林黛玉的藝術形象,就像肖像畫的背景一樣,瀟湘館成了林黛玉這個形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42同時也可看出,一個典故,往往包含了復雜的歷史人物故事,或是融化了前人作品的語言意境,接通并激活民族成員共同的歷史文化和文學記憶,既能使詩歌文本顯得典雅博奧,意蘊深厚,表情含蓄,又極大地增加了作品的知識容量和信息密度,提高了文本的解讀研究價值。下面看楊憲益和霍克斯對此難點的翻譯:
楊譯:
No silk thread can string these pearls;
Dim now the tearstains of those bygone years;
A thousand bamboos grow before my window——
Is each dappled and stained with tears?1[12]680
霍譯:
Yet silk preserves but ill the Naiad’s tears;
Each salty trace of them fast disappears.
Only the speckled bamboo stems that grow;
Outside the window still her tear marks show.[9]320
楊譯本后面附有注釋說明湘妃竹的傳說,楊譯為“年代久遠的淚痕”,盡管沒有直接指明是誰的眼淚,讀者借助注釋可以找到答案。而霍譯變成了希臘神話中水泉女神“那伊阿得斯的眼淚”(Naiad's tears),屬于典型的歸化翻譯,Naiad是希臘神話中的水泉女神,住在河流、湖泊和泉水中,是個美麗、快活和仁慈的人物。而在曹雪芹的筆下,林黛玉則是翠竹、詩書、苦戀、孤寂、淚水雕鑄成的。林黛玉變成了Naiad,“瀟湘館”只好成了 Naiad's House,既然對瀟湘館做了這樣的處理,就只好把林黛玉的綽號“瀟湘妃子”譯成River Queen,終日憂傷的瀟湘妃子變成了快活仁慈的水底女神,[8]p42這就對林黛玉的形象進行了徹底的顛覆,湘江舊跡的互文意義不僅沒得到傳達,而且進行了嚴重的歪曲。
三
《紅樓夢》詩歌中意象異彩紛呈,存在大量互文指涉,無不蘊涵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要把互文性翻譯出來,譯者必須對中國古典文藝美學理論有深刻的了解,在繪畫、音樂、美術等領域有深厚的藝術修養,譯者應該閱讀大量優秀的文學藝術著作,豐富自己的審美情趣,提高自己的審美趣味。同時刻苦磨練自己的翻譯技巧,在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上實行多樣化。
互文性在翻譯過程中具有雙重性。它首先是一種內互文性,這種內互文性對源語具有開放性,相對譯語文化卻具封閉性。內互文性翻譯至譯語文化時,已體現出不同文化間的參照關系,表現為一種超出其內互文性的外互文性。文化意象的內互文性轉化為外互文性時,譯者要考慮到這種外互文性將如何融合到譯語文本中去。因此,譯者既要考慮文化意象的內互文性,又要考慮譯語讀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在具體的翻譯過程中,譯者往往處于源語文化和譯語文化的張力之間,既要力求保留源語文化,又要讓譯語文化的解讀者接受源語文化。翻譯界經常討論的有關“歸化”和“異化”的問題,實際上是互文性上的一種選擇,體現了一種翻譯策略。譯者在采取“歸化”的策略時,更多的是注重譯語文本的內互文性,即考慮較多的是譯語文化讀者的接受能力。當譯語讀者的文化接受能力強時,源語互文性就能滲透到譯語中去,表現手段多體現為異化;當譯語讀者接受能力薄弱時,源語互文性就較難溶入譯語中,表現手段多體現為歸化。翻譯史上“歸化”或“異化”策略的使用此起彼伏就體現了這一點。
目前由于文化的多元化,譯界使用異化策略越來越多,譯者在翻譯時會有意保存譯文中的洋味,而讀者久而久之也接受了這種洋味。這種文化心態表明譯者和讀者都意識到了譯語文本外互文性的存在,并樂于接受這種外互文性,體驗一種新鮮的文化刺激,為文化互滲鋪墊基礎,反映了一種文化的相異性因素在另一種文化中的接受意向。[13]59
在這里尤其要強調詩歌異化翻譯的重要性,從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異化的翻譯可以為讀者了解并吸收外來文化創造機會,這也是翻譯的目的之一。沒有異化的翻譯,往往會使人看不到異域文化的真面目,更談不上文化交流中的融合吸收和加強,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會受挫。人類歷史證明,多元文化是有其優越性的。多種文化相互競爭與借鑒,共同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不同文化有相互沖突的一面,又有相互吸收的一面。吸收融合會產生“雜交優勢”。中國五千年的文化融合了無數異質文化,如佛教、少數民族文化、西方文化,“兼收并蓄”才使我們的文化生生不息,旺盛不衰,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們仍然是弱勢文化,我們都知道耶穌基督,但西方人中有幾人知道玉皇大帝,同時我們不應忘記過去西方殖民化的傳統,原殖民主義文化有著較強的排他性,其以往的翻譯常常傳播著殖民國家的文化,而對殖民地國家的文化則輕視甚至起著歪曲或肢解的作用。當前,全球各文化體系相互開放、相互交流與融合的廣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一點對處于“弱勢”地位的文化尤其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弱勢文化應該利用這種更為廣闊、更為寬容的多元化空間發展自己,傳播自己,壯大自己。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要盡可能多地采用異化翻譯,傳播中華文化,弘揚華夏文明,促進多極世界多元文化交流。
綜上所述,《紅樓夢》詩歌中充滿了豐富的互文性,楊憲益和霍克斯都充分發揮了譯者的主體性,綜合運用各種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但也只是譯出了其中的部分涵義。在理論上,譯文應當反映原文中所包含的一切互文關系,而且越充分越好。但實際上,由于翻譯中的“語義優先”原則的確定,以及由于文本所能容納的復雜成分的有限性,即可容性,在不影響正常語義表達的前提下,所有的互文手段都是很難翻譯的。[14]77就詩歌而言,由于英語是表音的,它講求邏輯性和實證性,很難理解漢字的象形、會意和形聲的特征,互文性更是很難傳達,但借助于異化的翻譯手段,一些漢語詩歌中的文化和美學互文意義已經成了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
[1]陳宏薇,江帆.難忘的歷程——《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寫性研究.中國翻譯2003(5).
[2]王洪濤.互相文性理論之于翻譯學研究:認識論價值與方法論意義.上海翻譯2010(3).
[3]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 in Toril Moi(ed.),The Kristeva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3.
[4]姜秋霞.文學翻譯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作用關系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104.
[5]www//hlmol.com/bbs.
[6]曹雪芹,高鄂.《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78、245.
[7]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北京:中華書局,2001:7、247、218.
[8]肖家燕,李恒威.詩歌隱喻與詩歌主題的異化翻譯——《紅樓夢》詩歌的認知語言學研究.紅樓夢學刊,2007(1).
[9]David Hawks,The Story Of The Stone.London:Penguin Books 1977/1973:251、320.
[10]張利玲.試論《紅樓夢》的鄉土想象及其文化意蘊.甘肅社會科學,2010(3).
[11]崔永祿.霍克斯翻譯《紅樓夢》中傾向性問題的思考.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5).
[12]Yang Xianyi and Yang Gladys.A Dream of Red Mansions.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94:680.
[13]舒奇志.文化意象的互文性與文化意象翻譯.外語與外語教學,2007(8).
[14]祖利軍.《紅樓夢》中俗諺語互相文性翻譯的哲學視角——以“引用”為例.外語與外語教學,2010(4).
朱耕(1970—),女,河南汝南人,黃淮學院外語系副教授。
2011-08-12
H059
A
1000-5455(2011)06-0153-04
【責任編輯: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