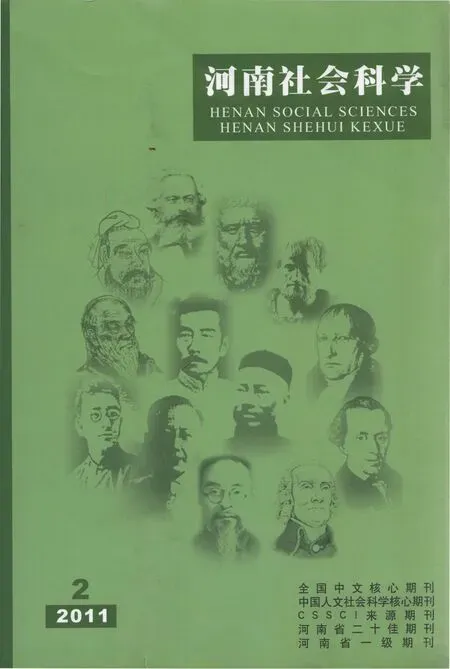鐘嶸《詩品》以“品”評詩淵源考
李天道,劉曉萍
(1.四川師范大學,四川 成都 610066;
2.四川大學,四川 成都 610064)
鐘嶸《詩品》以“品”評詩淵源考
李天道1,劉曉萍2
(1.四川師范大學,四川 成都 610066;
2.四川大學,四川 成都 610064)
有學者認為,《詩品》以“品”論詩的批評方法,其淵源應該是《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以品論賦”。筆者認為,這一說法,未免有失精準。應該說,鐘嶸的分“品”比較、以“品”評詩的方法的生成根源有多種,究其主要看,既根植于古代文化學術傳統,又是當時人物品藻方法與潮流影響的產物。
詩品;品;文化學術傳統;人物品藻
一
據《梁書·鐘嶸傳》、《南史·丘遲傳》的記載和隋劉善經《四聲論》(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引)、初唐盧照鄰《南陽公集序》、唐林寶《元和姓纂》等稱引,《詩品》又名《詩評》。如《隋書·經籍志》云:“《詩評》三卷,鐘嶸撰。或曰《詩品》。”唐、宋多用《詩評》,宋以后,往往正史藝文志系統稱《詩評》,目錄學系統和叢書系統稱《詩品》,詩話系統則二名混用。由于文化傳播方式和流傳系統的原因,以及目錄學和叢書文化的發展,后世學者遵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和《吟窗雜錄》、《山堂群書考索》的習慣,多稱《詩品》。《詩品》所論的范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把入選的一百二十二人分上、中、下三個等級,以“三品升降”顯現優劣。應該說,鐘嶸的《詩品》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后出現的第一部以“品”評詩的詩學專著。近有學者認為:“《詩品》以品論詩,實淵源于《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以品論賦。”[1]筆者認為,這一說法,未免有失精準。應該說,鐘嶸的分“品”比較、以“品”評詩的方法,既根植于古代文化學術傳統,又是當時人物品藻潮流影響的產物。為此,這里特就鐘嶸以“品”評詩方法的淵源作一考證。
二
在《詩品序》里,鐘嶸明言自己的分“品”比較、以“品”評詩方法,來源于“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所謂“九品論人”指班固的《漢書·古今人名表》九品論人法,而“七略裁士”則指劉歆的《七略》敘述歷代學術源流、追溯士人風格淵源法。
品,其原初義域為物品、物件。所以鐘嶸以“品”評詩方法來源之一的“九品論人”與中國古代以“品”論物的傳統分不開。在中國古代,很早就有“三品”之說,以分“品”論物。如《周易·巽》云:“六四:悔亡,田獲三品。”高亨注云:“品,種也。……行獵將得三種獵物。”又如《尚書·禹貢》云:“厥貢惟金三品。”孔安國傳云:“金、銀、銅也。”孔穎達疏云:“鄭玄以為銅三色也。”《太平廣記》卷四○一引宋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巴巫間,民多積黃金,每有聚會,即于席上列三品,以夸尚之。”這些地方所謂的“三品”,其義域為三種、三類。“品”又為等級、等第。《禮記·郊特牲》:“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尚書·舜典》孔穎達疏云:“品,謂品秩也,一家之內尊卑之差。”《漢書·匈奴傳上》顏師古注云:“品謂等差也。”《宋書·恩幸傳序》:“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這些地方的“品”為地位的尊卑貴賤等差。又如劉向《說苑·政理》云:“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后漢書·循吏傳》云:“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隋書·經籍志序》:“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這些地方所謂的“三品”,其義域則為三等級別,即將政績、田畝、書分為上、中、下三等品級,以“品”評物。顯然,這也應該是鐘嶸以“品”評詩方法的文化淵源之一。
對人物進行“品”評,有時稱為“品鑒”,有時稱為“品藻”。就文獻資料看,“品藻”一詞最早應該出現在《漢書·揚雄傳下》。其記載云:“仲尼之后,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對此,顏師古注云:“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表明所謂“品藻”多針對人的節、品、格而言,以是非長短優劣好惡議事。《顏氏家訓·涉務》云:“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其試用,多無所堪。”這些地方所謂的“品藻”,就是排列評價、分析鑒別的意思。正由于此,所以即如劉知幾在《史通·品藻篇》中指出:“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下愚等差有序,則懲惡揚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郁為不朽者矣。”應該說,“品藻”是“世中文學之士”的活動,其目的是辨君子小人。
在中國古代,分“品”論人的傳統由來已久。所謂辨小人、君子的以“品”評人在先秦就已經開始,如《詩經》即有“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之說。又如《國語·周語》中記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這里的“品”為當官的等級。“品”又為人品。據《逸周書·太子晉》記載,周靈王的太子王子晉,名晉,字子喬,也叫太子晉,王子喬。其時,師曠出使周,贊譽太子晉說:“溫恭敦敏,方德不改。”就稱贊子晉性情溫柔,人品厚道,不改常德[2]。又據《春秋左傳注·文公元年》記載,初,楚成王想立商臣為太子,于是征求令尹子上的意見,對此,子上說:“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楚國之舉,恒在小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這些材料雖然沒有出現“品評”、“品藻”、“品鑒”之類的辭藻,但應該也是一種“定其差品及文質”的以“品”評人行為。又如春秋時期的孔子,就是本著當時的審美訴求以及審美標準,從“仁”、“禮”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考察和評品人物的品格和才能的方法,如非常有名的“孔門四科”,就是從“文、行、忠、信”四個方面,即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來品評人物與人才的。同時,孔子還以人的天賦稟性來品評人物,把人劃為先天的、生來就“知之”和后天通過學習而“知之”,以及有了困惑而“學之”和有了困惑而“不學”等四類。應該說,這種根據先天稟性與后天習性將人劃分為不同類別并針對不同類別分別加以品評的方法對后世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從語義看,“品鑒”與“品藻”都是對人物的精神、氣質、風度、才學高下的評論,但兩者還有所不同,“品鑒”側重于才性方面的品評,而“品藻”則側重用綺麗、優美的辭藻對人的氣度風神進行評價。從歷史上看,真正意義上的人物品評始自漢代。其時,人物品評已經蔚然成風。漢代在人才選拔方面采用“征辟”和“察舉”兩種途徑。所謂察舉,就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轄區內進行考察,發現統治階級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異等”、“賢良方正”等名目,推薦給中央政府,經過一定的考核,任以相應的官職;所謂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長官直接進行征聘。這中間就涉及鄉間的鑒定和名士的品評。因為關系到士人的升遷提拔,所以這種選才途徑受到整個社會的高度重視。到漢末、三國時期這種制度轉變為盛行的諸子的談論。這種諸子型的談論帶有非常濃郁的戰國辯士之風,因此,無論是“品藻公卿”還是“激揚聲名”,已經和漢代流行的以“孝廉”、“茂才異等”、“賢良方正”為標準、以溫柔敦厚為行儀規范的人物品藻不同了。如劉劭《人物志》中對當時人物的品評標準就充斥了刑名法家思想,這應該是當時風氣的一種寫照。
對漢代人物品評記載得最為翔實的是班固《漢書》中的《古今人表》。班固在該《表》中把上古以來的歷史人物分別以上中下等級歸類,劃入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等所謂“九品”。到延康元年(220年),漢獻帝讓位于曹丕。班固的這種對人物進行不同品級劃分的方法得到朝廷的重視和進一步推廣。朝廷采納吏部尚書陳群所獻的人才選拔策略,承續班固的人物品評法,將士人分別評定為“九品”,以此為基礎,供朝廷選拔任用。為了更好地選拔人才,當時還在全國各地設專門進行人物品評的“中正”官。這就是中國人才選拔史上著名的“九品中正制”。這一制度沿襲和發展了東漢以來重觀察而不重考試的人才品評方法。不過,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將人才分為“九品”的“中正品第”制度只是流于形式而已,并不作為士大夫入仕的主要選拔標準。
到魏晉時期,自給自足的封建大地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各有其經濟力量和政治軍事力量的門閥世族的形成,東漢以來日趨僵化、煩瑣的儒學影響不斷削弱,使得統治階級士大夫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生活上和思想上獲得了過去所沒有的一個相對獨立自由的活動天地,文化不再只是朝廷進行倫理教化的工具了,而日益成為上層社會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先秦以來特別是漢代后期,對個人的才能風貌的講求以及對人生意義、價值的思索,都被不可分割地聯系起來,使人的個性、愛好、趣味等等在封建制度所能容許的范圍之內,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注意和重視。由此人物品藻也具有了全新的內容。這時的人物品評,逐漸發展為不僅僅是看人物的道德節操如何,而且十分重視才能、智慧、應變的本領等。到了晉代門閥世族大興之后,人物品藻更演變為對人物的個性氣質、風度才華的品評。從《世說新語》一書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種品評不只是政治倫理的,而且更是審美的,后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種情況深刻地影響到各門文藝和美學思想的發展,使得這一時期的美學思想經常從人的內在的個性、氣質、天賦以及獨特的心理感受等角度來觀察審美與藝術問題,注重于人物的風采神韻。即如宗白華所指出的,中國美學的精神及其整個思想體系的建構,都應該是建立在“人物品藻”的基礎之上的,所以中國美學乃是“出發于‘人物品藻’之美學”。中國美學有關“美”的概念、范疇、形容詞等,都發源于對人格美的評賞。在宗白華看來,中國人對于人格美的愛賞淵源非常深遠,而到魏晉時期,即“世說新語時代”,這種對人格美的愛賞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3]。
可以說,正是受“人物品藻”和對人格美追求的世風及其方法的影響,到六朝時期,人物品評和詩文思想的結合代替經學而成為生成詩文批評的主要途徑,對作為審美意識形態的詩文思想的建構發生了重大影響。漢代以來依經學而產生的詩學理論轉變為注重從創作者個體的才性出發的分“品”比較、以“品”評人的詩學批評。中國詩學批評的名著,鐘嶸《詩品》之前的陸機《文賦》,同時的劉勰《文心雕龍》,應該說,都受品藻人物風氣的影響。藝術批評方面,早于《詩品》的趙壹《非草書》、顧愷之《晉代勝流畫贊》、謝赫《古畫品錄》,分品評論書畫家;晚于《詩品》的梁庾肩吾《書品》,分三品評論書家,每品之中,又分三等,實際上是九品,與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正相吻合。此外梁阮孝緒的《高隱傳》也分三品評古今高隱之士。可以說,分“品”批評,已是當時評論家的共識,是一種帶有時代特征的批評方法。應該說,鐘嶸《詩品》以“品”評詩的方法受此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三
鐘嶸《詩品》這種分“品”比較的方法還受“七略裁士”,即劉歆的《七略》敘述歷代學術源流、追溯詩人的風格淵源方法的影響。劉歆與其父劉向是西漢后期著名的古典文獻專家和歷史學家。從中國學術史看,劉歆和劉向父子的治學態度是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即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古代學術流派及其文化淵源,注重文獻考據、輯佚辨偽,從紛繁復雜的文獻之中理清線索,做出明晰的判斷。他們注重全面地掌握文獻,一方面廣泛地收集遺書,一方面對存世典籍進行深入研究,因而其治學方法及其思想又具有學術規范的意義。其《七略》,特別是其中的《諸子略》,在學術思想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上的引領性與規范性意義。根據《漢書·劉向傳》的記載,漢成帝時,劉向受命負責校勘皇家館藏的經書;劉歆則接受朝廷的詔書,與其父一同領校秘書,講習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等,涉及其時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沒有他們不考究的。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漢武帝時,要求天下的士人獻書,到成帝時,朝廷又下詔,要求整個社會都搜尋“遺書”。并且下令,要劉向等人負責整理這些“遺書”。其時每一部書整理以后,劉向都要“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死后,劉歆繼承其父的遺業,總攬群書,并向朝廷進獻他所撰寫的《七略》,由此才“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由于歷史變亂,劉歆所撰寫的原本的《七略》已經散落,但其中的大部分則通過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承傳下來。其基本內容仍然突出地體現了劉向劉歆父子的學術史思想。
按照劉氏父子的說法,《七略》對先秦至漢的學術流派和重要著作,大體均有著錄,其著錄過程就是一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過程,“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本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劉氏父子秉承司馬遷父子的治史原則,從流派的角度來研究古代學術發展史,對古代的若干學術流派加以劃分,分為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十家。同時,在他們看來,這十家之中,小說只不過是一些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缺乏真實性,不足為據,所以“君子”,即士大夫是不會寫小說的,因此,“十家”之中只有九家是應該得到重視的。正由于此,才有所謂“諸子十家”其可以看的只不過“九家”之說。對此,班固特別在《漢書·敘傳》中加以評論,強調指出:“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已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也正因為此,后來則稱古代學術流派為“十家九流”。
在經書中,劉氏父子對《易》特別推崇。他們不但把《易》列為“群經之首”,而且在《六藝略》中特別表明他們的學術史思想,認為《易》為“五經之原”。他們強調指出:《六藝》之中,《樂》主“和”,以之“和神”,為“仁之表也”;《詩》是用來規范言論的,以之“正言”,為“義之用也”;《禮》是用來“明體”的,“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是用來“廣聽”的,為“知之術也”;《春秋》是用來“斷事”,為“信之符也”。這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其中,“《易》為之原”。所以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也就是說,《易》是與天地為終始的。根據《漢書·五行志》的記載,他們的這種觀點是有由來的,因為劉歆認為,遠古時期的伏羲氏是秉承了“天”的意志而王,接受《河圖》,以其為基礎而畫之,由此始有“八卦”;后來出現了洪災,大禹治理洪水,獲得《洛書》,法而陳之,由此才有《洪范》。劉歆指出:從前,“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也就是說,在他看來,五經以《易》為其本原,就是以“八卦”為《河圖》,以《洪范》為《洛書》。可以說,劉歆是把《周易》、《洪范》和《春秋》都看做是講天人之道等根本道理的經典著述。
正因為如此,劉氏在對諸子各家著述作評論時,喜歡引用《周易》“經文”與“傳文”,以其作為評判各家各派學術思想的標準和依據。如就《七略》來看,其中的《六藝略》和《諸子略》就引征了八條《周易》的“經文”與“傳文”,其余的引征了五條。比如:其中品評《易》引了《周易·系辭下》的“伏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評述《書》則引《周易》中的“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評論《禮》又引用了《周易》中所謂的“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評論道家學派則引用“《易》之謙謙”,評論法家學派又引用《周易》的“先王以明罰飭法”,評論天文者流則引《周易》所謂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評雜占者流則引《周易》的“占事知來”等等,不一而足。劉氏父子“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方法和思想顯然影響到鐘嶸,并成為其《詩品》以“品”評人、“裁士”方法的淵源之一。
按照鐘嶸自己的說法,他的批評方法主要是“致流別,辨清濁,掎摭病利,顯優劣”。所謂“致流別”,即追溯師承宗派、時代源流,實即區分詩歌的風格流派,追溯其淵源;“辨清濁”,在這里則指辨析不同流派及同一流派中風格的一致性和多樣性;“掎摭病利”,主要指陳詩歌作品的利病得失;“顯優劣”,則為評定詩人地位的優劣高低。幾種方法交叉運用,同時出現,又互相交融,形成其“三品升降法”或分“品”評述法。
總之,鐘嶸《詩品》以“品”評詩方法的淵源應該是多方面的,不應該簡單化。
[1]李士彪.三品論賦——《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前三種分類遺意新說[J].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112—114.
[2]盧文暉.古小說輯佚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責任編輯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
I2
A
1007-905X(2011)02-0173-04
2010-12-2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8BZX068)
1.李天道(1951— ),男,四川彭州人,四川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2.劉曉萍(1981— ),女,四川彭山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